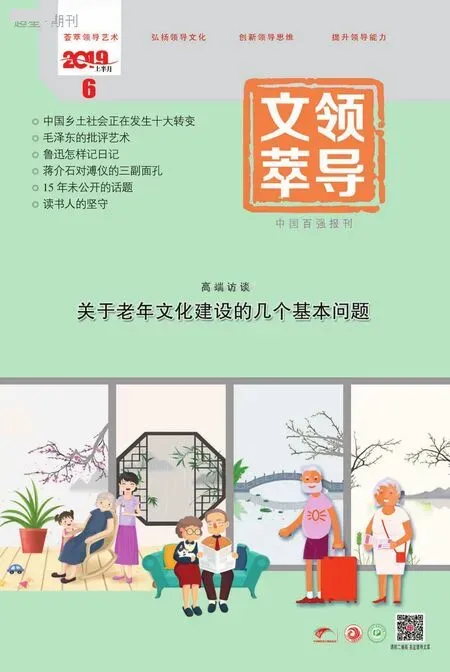在開封為趙佶一嘆
周大新

身為一個(gè)河南人,開封是我常去的城市。每次去開封,只要看到龍亭,看到北宋王朝留下來的遺跡,都免不了在心里為趙佶一嘆。唉,趙佶,你該去精研你的書畫藝術(shù),而不該去當(dāng)皇帝呀!
趙佶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廟號徽宗。趙佶在接過哥哥趙煦的皇位時(shí),大宋王朝的局面還很不錯(cuò)。汴京當(dāng)時(shí)是擁有150萬人口的世界性大都市,工商業(yè)異常繁榮。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里描繪了汴京的繁華市景。這幅畫繪成后,張擇端便把它獻(xiàn)給了趙佶,趙佶是這幅畫的第一個(gè)收藏者,這表明畫中的圖景就是對當(dāng)時(shí)盛況的真實(shí)描繪。但當(dāng)趙佶繼位25年之后,大宋王朝竟然就呼啦一聲亡掉了,朝廷被迫南遷,北宋的歷史戛然而止。
《靖康稗史箋證》附錄諸跋其九寫:自古亡國之恥辱,未有如趙宋者。這就是趙佶帶來的。
這就是趙佶的悲劇命運(yùn)。
多少年來,人們一直在追尋趙佶悲劇命運(yùn)的起因。無數(shù)的歷史研究者得出了無數(shù)的結(jié)論。而我這個(gè)不懂歷史的人認(rèn)為,起因就是他當(dāng)了皇帝。
他的哥哥宋哲宗趙煦去世時(shí),他是端王,這一年他18虛歲17周歲。此時(shí)的他已有了對事情做出選擇的能力。
他的哥哥是在23歲的盛年去世的,盡管去世前已病了一段時(shí)間,但事發(fā)還是有些出人意料。17周歲的趙佶并沒有要當(dāng)皇帝的準(zhǔn)備,包括精神準(zhǔn)備和素質(zhì)準(zhǔn)備。
當(dāng)時(shí),因哲宗趙煦沒有留下子嗣,按照規(guī)制,只能從他的兄弟中選擇繼位者。哲宗此時(shí)在世的兄弟有五位,包括趙佶,但趙佶并非哲宗的嫡親兄弟,按照宗法制度,他并無資格繼承皇位。當(dāng)時(shí)的宰相章惇提出,按照嫡庶禮法,該立哲宗同母弟弟簡王趙似為君。不料遭到向太后反對。章惇退而提出,若論長幼,那么當(dāng)立年長的申王趙佖為帝。可向太后以趙佖眼有疾病為借口又給予拒絕。因?qū)w佶印象好,向太后堅(jiān)持立他為君。章惇認(rèn)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宰相和太后為此僵持不下,其他大臣附和了向太后之議;章惇?jiǎng)輪瘟Ρ。辉贍庌q。據(jù)說,當(dāng)端王趙佶被傳來宮中時(shí),并不知道他同父異母的哥哥哲宗已經(jīng)去世,他來到向太后所坐的簾前,被向太后告知:皇帝已棄天下,無子,端王當(dāng)立。
如果他堅(jiān)辭不受,那對他和大宋王朝無疑是一件好事。可惜他沒能堅(jiān)持到底,他最終領(lǐng)受了向太后的美意,登基做了皇帝。畢竟,當(dāng)皇帝的好處太多,當(dāng)了皇帝就是天下老大,說句話就是圣旨,這些對人的誘惑力太大。17歲的趙佶沒有堅(jiān)辭到底是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原諒的。
可我們?nèi)糇鰝€(gè)假設(shè),假設(shè)趙佶有一點(diǎn)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興趣根本不在掌握權(quán)力上,他要辭去皇位是完全可以的。他只要再在向太后面前堅(jiān)決一點(diǎn),加上有章惇的反對,向太后是有可能改變主意的。
差不多可以斷定,趙佶在這個(gè)重大的人生選擇面前,依從了自己的本能而不是自己的理智。
17歲的趙佶明知道自己喜歡的是書法、是繪畫、是藝術(shù)收藏、是蹴鞠、是騎馬游玩,而不是端坐在朝堂上去一本正經(jīng)地思慮和處置政事,可他還是做了違背自己內(nèi)心的選擇。
我想,當(dāng)他被囚在金國之后,他回想起自己當(dāng)初做的當(dāng)皇帝的選擇,大約是會心生后悔的!會在心里念叨:當(dāng)初要不做皇帝多好……
對此,多少年后,我也想為他一嘆:選錯(cuò)了呀,趙佶!
當(dāng)然,我這樣嘆說,是很容易遭到反駁的:當(dāng)今美國兩個(gè)70多歲的男人為當(dāng)總統(tǒng)都爭得不可開交,你竟想讓幾百年前一個(gè)17歲的中國男人把到手的皇位推掉,這不是白日說夢嗎?誰能做到?就是你自己,真要遇到讓你繼承皇位的機(jī)會,你能拒絕?
我承認(rèn)這反駁很有力,也讓我心中一驚:假如真讓我有了這樣的選擇機(jī)會,那對我肯定也是一場嚴(yán)峻的考驗(yàn),我真能理智地選擇拒絕?不過,還是有前人給我們做出了榜樣——
那就是伯夷和叔齊。這兩位都是商朝時(shí)期孤竹國國君之子,伯夷是老大,叔齊是老三。孤竹國國君非常疼愛老三,常說,在我死了之后,真希望能由老三叔齊來繼承我的王位。可按當(dāng)時(shí)的制度,王位是應(yīng)該由長子來繼承的,伯夷才是合法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后來,孤竹國國君死了,伯夷想起父王的話,想父王準(zhǔn)是看到叔齊有治理國家的才能才這樣說的,于是便推讓本屬于他的王位給叔齊,沒想到叔齊也不貪戀權(quán)位,堅(jiān)決拒絕了大哥的好意,說,按禮法應(yīng)該是大哥繼位。二人都不肯登基,相持不下,竟成僵局。伯夷想,只有我走了,叔齊才好繼位,于是便在一個(gè)深夜,留下要叔齊繼位的書簡,悄悄離開了王官。叔齊也想,大哥賢德仁厚,一定能把國家治理得比我好,但只要我留在這兒,大哥就不會違背父命登基,干脆,我走。叔齊于是半夜里從王宮后門走了。二人雙雙逃走后,孤竹國的人只好讓老二繼承了王位。
我們這些后來者,包括我自己,是不是該向這兩位學(xué)習(xí)?
宋徽宗自選的命運(yùn)再也無法更改,但幾百年之后的我,倒可以有個(gè)假想。假想趙佶做了另外的選擇:堅(jiān)辭皇位,仍做端王,潛心于他喜歡的書畫創(chuàng)作。
那他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命運(yùn)?
答案是肯定的!
趙佶的悲劇命運(yùn)昭示我們,當(dāng)我們?nèi)ミx擇一生要做的事情時(shí),一定要三思而行,不能只憑本能;一定要注意拒絕誘惑,不要被一些職業(yè)表面的光鮮所吸引;一定要爭取不被外力左右,自己做出決定;一定要量力而行,去做自己喜歡做的、愿意做的、有可能做成的事!
我想,在這個(gè)世界上,因?yàn)橹鳂I(yè)選擇錯(cuò)誤而毀掉短短人生的,絕不止趙佶一人。
(摘自《中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