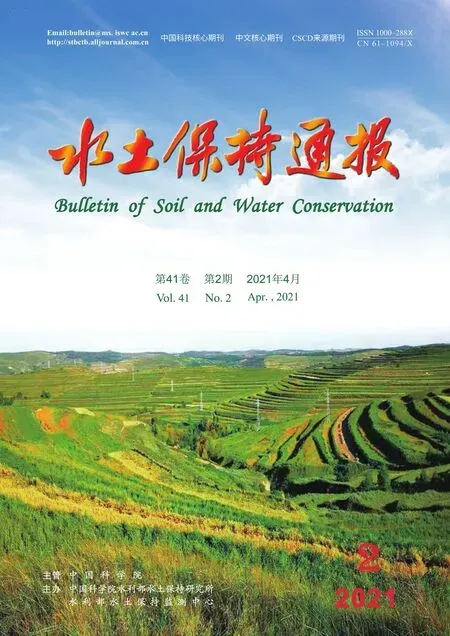土壤水鹽因子對鹽湖防護林體系植被群落分布的影響
馮亞亞, 汪 季,2, 黨曉宏,2, 魏亞娟, 管雪薇, 李 鐲
(1.內蒙古農業大學 沙漠治理學院, 內蒙古 呼和浩特010018; 2.內蒙古杭錦荒漠生態定位觀測研究站, 內蒙古 鄂爾多斯 017400)
長期以來,植被群落分布及其影響因子一直是生態學領域重點研究內容之一[1]。特別是在干旱區荒漠綠洲過渡帶,脆弱的生態系統決定了其抗干擾和恢復能力低,自維持和自調控功能弱的特點[2],生態系統管理面臨著諸多難點。荒漠植被作為荒漠生態系統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改善荒漠生態環境、維持生態系統穩定性和保障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干旱荒漠區,氣候[3]、地形[4]和土壤[5-6]、地下水環境[7-8]和人為干擾等因素限制著植物生長和分布,決定了植物群落的演替速度和方向。其中,土壤環境是影響植被生長和分布的主要因子。研究表明,土壤含水量決定了植物的斑塊分布,進而促進灌叢下肥島效應的形成;同時,土壤水鹽及其他土壤因子也通過調節草本植物種類及其多度來想荒漠植被群落結構。因此,了解植物與土壤因子的關系對荒漠綠洲過渡帶植被恢復和管理非常重要。
吉蘭泰鹽湖地處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境內,氣候干旱少雨,風沙活動頻繁,風沙危害十分嚴重。自1983年開始,吉蘭泰鹽湖建立由半固定沙壟、防護林帶、湖濱鹽堿灘地等多種下墊面構成的防風固沙林體系,有效的阻止了風沙侵湖現象[14-16]。但隨著營建年限的增加和植被的演替,導致防護林體系人工植被大面積死亡,自然植被逐漸退化,不同下墊面植被分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嚴重影響了防沙治沙工作。因此,防護林體系撫育工作迫在眉睫。土壤水鹽作為影響荒漠植被生長和分布的重要環境因子,明晰防護林體系植被分布與表層土壤水鹽含量的內在聯系,對進行人工—天然植被群落撫育和管理具有重要作用。鑒于此,本文以吉蘭泰鹽湖防護林體系為研究對象,對防護林體系植被進行調查,并運用數量分析和排序方法,探究不同下墊面植被與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溶性鹽離子間的相關關系,探究影響植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旨在揭示防護林體系植被群落分布格局與土壤水鹽因子等的關系,為吉蘭泰鹽湖防護林撫育和管理提供理論依據。
1 試驗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屬于典型大陸性干旱氣候,具有干旱少雨,日年溫差大,蒸發量大的氣候特點[14]。最高氣溫40.9 ℃,最低氣溫-31.2 ℃;該區風沙活動頻繁,年平均揚沙日數為82.5 d,年風沙流出現頻率為112.9次,風力一般在4—5級,平均風速3.6 m/s[15,17]。鹽湖土壤種類以灰漠土、風沙土為主,并伴有鹽堿土出現。研究區防護林體系始建于1983年,在鹽湖西北部建立起了東西長18 km,南北寬1 km的由半固定沙壟、植物防護林網、湖濱鹽堿灘地等多種下墊面構成的,喬、灌、草相結合人工防風固沙林體系[16]。防護林體系建立之初,人工植被在宏觀上根據與主害風垂直方向進行布置,植物種主要以梭梭、花棒、沙拐棗和沙棗為主。其中沙棗主要采用2 m×2 m和3 m×3 m株行距,梭梭、花棒和沙拐棗主要采用2 m×2 m株行距[16]。自防護林體系建立36 a以來,林帶不同下墊面景觀發上了巨大的變化,沙棗大面積死亡,鹽斑裸露現象,逐漸形成人工—天然植被群落(表1)。研究區植被結構簡單,植物種類稀少,主要以白刺(Nitrariatangutorum)、梭梭(Haloxylonammodendron)、花棒(Hedysarumscoparium)、沙蓬(Agriophyllumsquarrosum)、豬毛菜(Salsolacollina)的等耐旱,耐鹽堿的灌木、草本植物為主[19]。

表1 樣方分布及植被特征
1.2 樣地選擇與樣品采集
試驗于2019年8月進行,試驗期間無降水事件。在吉蘭泰鹽湖防護林體系內設置4條樣線,每條樣線均經過半固定沙壟、防護林帶和灘地共3種防護林類型[20]。樣線長3 000 m,樣線間間隔250 m,在樣線上每隔200 m設置一個30 m×30 m固定樣方,共計64個樣方,去除人為干擾的樣方,共計有55個固定樣方(表1)。植被群落采用五點樣方法,分別在每個固定樣方內設置5個10 m×10 m灌木樣方,調查樣地內灌木的種類、數量、株高、冠幅和蓋度等。每個灌木樣方設置5個1 m×1 m草本樣方,調查樣方內草本植被的種類、數量、株高和蓋度等指標。采用重要值作為各種植物在群落中的優勢度指標,計算公式為[16]:
重要值Ⅳ=(相對密度+相對頻度+
相對蓋度+相對高度)/4
(1)

1.3 數據處理與分析
依據張金屯[22]和曹靜等[23]人的研究結果,選取研究區分布頻度大于5%的植物種,應用雙向指示種分析(TWINSPAN)對防護林體系植物群落進行數量分類,依據樣地—植物種的重要值數據矩陣,將研究區植被劃分為不同群落類型[23-24],分類軟件采用PC-ORD生態學軟件[25]。運用典范對應分析(CCA)探討植被群落與環境因子相關關系[26],分析采用國際標準生態學軟件Canoco 5。分析方法如下,首先,對物種重要值—樣方環境因子數據進行趨勢對應分析(DCA),若DCA排序軸的梯度長度<3,則采用線性模型排序;若梯度長度>4時,則采用單峰模型排序;梯度長度位于3,4,兩種模型都適合[22,26]。
2 結果與分析
2.1 吉蘭泰鹽湖防護林植物種類與群落類型劃分
2.1.1 吉蘭泰鹽湖防護林植物種類 由表2可知,在研究區55個樣方中,篩選出分布頻率大于5%的植物種,其中有喬木1種,灌木、半灌木5種,草本10種,包括藜科、禾本科、豆科和檉柳科等共計8科16屬。其中,草本植物優勢種以一年生沙蓬、霧冰藜和豬毛菜為主,占樣方總數的74.55%,65.45%和65.45%;灌木植物中白刺出現頻率最高,為72.73%,這與白刺具有固沙阻沙,耐旱耐鹽堿的生態適應性密切相關。其次是沙拐棗和梭梭,分別為36.36%和34.55%,是吉蘭泰鹽湖防風固沙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整體來看,防護林體系物種組成相對貧乏,優勢植物主要以耐旱耐鹽堿的灌木、小灌木和草本植物為主,這與研究區干旱少雨,蒸發量大的大陸性干旱氣候相適應。

表2 鹽湖防護林植物群落物種組成
2.1.2 TWINSPAN群落分類分析 運用TWINSPAN分類法,依據樣方—植物種重要值數據,對研究區主要植物種進行分類,分類時依據中國植被分類原則,并結合實際樣地調查結果,將防護林體系植被劃分為6個群落類型,依據各群落優勢種和指示種命名群落類型。分類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雙向指示種分類(TWINSPAN)的樹狀圖
① 群落Ⅰ。沙棗+蛛絲蓬+霧冰藜+豬毛菜群落。該類型群落包括樣地5,7,11共3個,樣方于分布防護林帶,優勢種為沙棗,樣方內沙棗均為人工種植,株高最高可達3.2 m,群落結構物簡單;優勢種為沙棗,伴生種花棒、沙拐棗、豬毛菜、沙蓬等。②群落Ⅱ:沙拐棗+白刺—豬毛菜群落。包括4,16,25,26,36~39,41共9個樣地,樣地分布于半固定沙壟。優勢種為沙拐棗,伴生種包括沙蓬、霧冰藜、花棒等。 ③群落Ⅲ。梭梭—沙蓬+霧冰藜—沙蓬—豬毛菜群落。包括6,9,12,13,22~24,27~29,35,42,46,47共14個樣地。樣方于分布防護林帶和半固定沙壟,優勢種為梭梭,伴生種包括沙拐棗、沙蒿等。 ④群落Ⅳ。花棒—白刺—霧冰藜—沙蓬群落。包括8,10,14,15,19,40,44共7個樣地。樣方主要分布于防護林帶,優勢種為花棒,伴生種沙蒿、豬毛菜等。 ⑤群落Ⅴ。白刺+沙蓬—沙蒿群落。包括樣地18,20,21,30,31,33,34,43,45,48,49,50~55共17個樣地,樣地分布于灘地和防護林帶,優勢種為白刺,伴生種有苦豆子、砂藍刺頭等。 ⑥群落Ⅵ。白刺—檉柳群落。包括樣地1,2,3,17,32共5個樣地。樣方主要分布于灘地,優勢種為白刺,伴生種有堿蓬和沙蒿。通過對樣方分類發現,除了群落Ⅴ和群落Ⅵ優勢種為白刺外,其余群落優勢種均為人工種植灌木,群落Ⅰ、群落Ⅱ、群落Ⅲ和群落Ⅳ草本植物種數明顯高度其他群落,且由于受到人工林的影響,草本植物平均高度較低,長勢較差。
2.2 不同群落類型下土壤水鹽特征分析


表3 不同植物群落類型下土壤水鹽因子特征分析
2.3 防護林植被群落與土壤水鹽因子的CCA排序分析
防護林體系植物重要值—樣方土壤水鹽因子矩陣的DCA排序結果表明,所有軸的梯度長度最大為4.5,且研究證明,CCA排序法更適合用于干旱區沙地植物分布及其環境解釋[25-26],故選用CCA分析植物群落分布與土壤水鹽因子的關系。從CCA排序匯總表可知(表4),CCA第1軸特征值為0.381,第2軸特征值為0.176,占所有排序軸特征值總和的68.8%,Gauch研究表明,如果前3個主要特征向量的方差占總方差的40%以上,則排序結果是有效的[27],因此,本研究只保留前兩軸的數據來研究防護林體系植物群落分布特征與土壤水鹽因子的關系。

表4 植被群落分布特征的CCA排序
進一步分析得到防護林體系植物種與土壤水鹽因子二維排序圖(圖2)。圖中箭頭連線長短代表植物種分布與該環境因子相關性的大小,連線越長,代表相關性越大,而箭頭所處象限代表土壤因子與排序軸間的正負相關性;環境因子與植物種之間關系可以做某一植物種與環境因子連線的垂直線來表示,若垂直線與環境因子連線相交點在箭頭正方向,表示該植物種與環境因子為正相關關系,相交點在箭頭負方向,表示該植物種與環境因子為負相關。


圖2 不同植物種與環境因子的CCA排序圖

表5 土壤水鹽因子與排序軸相關關系
由不同植被類型與環境因子的CCA排序圖可知(圖3),由于Cl-與土壤總含鹽量的共線性,因此分析過程中將Cl-將排除在外。研究發現,雙向指示種分類(TWINSPAN)結果與CCA植被樣方—土壤水鹽因子排序圖分類結果較為吻合。在排序圖中,除群落Ⅰ外,群落Ⅳ到群落Ⅱ分布隨土壤水鹽含量降低方向依次排開,群落Ⅵ(白刺—檉柳群落)生境土壤表現出具有較高的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含鹽量,主要分布于離鹽湖湖心較近、土壤水鹽含量均較高的灘地。群落Ⅴ(白刺+沙蓬—沙蒿群落)生境條件與群落Ⅵ相似,而以人工灌木為優勢種植物群落分布較為集中。整體來看,不同植被群落類型樣方分布存在一定程度重疊。土壤水鹽因子與植物群落樣方CCA排序圖直觀的反映出防護林體系不同植物分布的相關關系。

圖3 不同植被類型與環境因子的CCA排序圖


表6 環境因子顯著性檢驗結果
3 討 論
植被是反映某一地區生態環境特征的重要指標[28],研究表明,在該研究區自然條件惡劣的條件下,植物物種少,群落結果簡單,生活型單一的特點[16]。由于草本植物作為生態恢復的先鋒植物,具有適應力強,生活史短暫,生態位較寬等特點[29],造成研究區植物種主要以草本植物為主(占植物種總數的62.5%),促進了研究區植被的正向演替。TWINSPAN分類將防護林體系植被劃分為6個群落類型,6個群叢類型的分布代表了生境梯度的變化,同時也是防護林人工植被與天然植物群落在特定生境條件下演替的結果。
研究表明,不同植被類型在CCA排序圖上從第一排序軸正方向到負方向,即沿土壤水鹽含量降低的方向有序分布,較好的反映了雙向指示種分類結果的有效性。其中以人工植物(梭梭、花棒和沙拐棗)為優勢種的植被群落分布較為集中,且分布范圍有一定的重疊,表明防護林體系下土壤水鹽因子和人工植被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植物中的分布[30]。

除土壤Mg2+,Na+含量外,從排序圖中可以看出,表層土壤含水量也對防護林體系植被分布起到重要作用。在干旱半干旱區,土壤水分是制約植被分布格局的重要因子,特別是草本植物,張佳等人研究發現,土壤含水量對草本植物的生長、分布、組成和生態系統功能產生直接影響[36];土壤pH作為反映土壤理化性質的重要指標,其大小直接影響到土壤肥力狀況和有效性[37],進而影響植物生長發育。Schuster[38]研究發現,在堿性土壤中,植被分布與土壤pH值不存在顯著性關系。尹德潔[39]對山東濱海鹽漬區植被群落特征與土壤化學因子關系研究發現,山東濱海鹽漬區土壤pH均值為8.09,土壤pH值與植被分布不存在相關性。在本研究中,不同植被類型下土壤pH值均大于8,且排序結果表明,研究區不同植被群落分布與土壤pH不存在顯著相關性,這與何明珠對阿拉善高原植被分布與環境因子關系研究相一致[32],并驗證了Schuster研究結論。
在干旱半干旱區,影響荒漠植被分布格局的因素包括地下水、土壤含水量和土壤鹽分等環境因子,在小尺度下,土壤環境是影響植被分布的主要因素[3-6]。研究結果表明,表層土壤含水量、白刺土壤水溶性鹽對于植物群落分布僅能解釋25.2%,未解釋部分占74.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植被與表層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溶性鹽的關系。這與趙鵬[18]、賀強等[40]人研究結果相一致。但本研究僅從土壤水鹽出發討論荒漠植被類型及其空間分布與環境的關系。而各類環境因子對植物群落分布的相對作用并不絕對。其余未解釋部分可能包括土壤養分和風沙活動對荒漠植被分布的影響。
4 結 論
(1) 通過對吉蘭泰鹽湖防護林體系進行植被群落調查發現,研究區分布頻率>5%的植物隸屬于8科16屬。植物群落結構簡單,物種組成稀少。優勢植物主要以耐旱的灌木、小灌木和草本植物為主。
(2) 雙向指示種分類(TWINSPAN)將防護林體系內植被分為沙棗+蛛絲蓬+霧冰藜+豬毛菜群落、沙拐棗+豬毛菜群落、梭梭—沙蓬+霧冰藜—沙蓬—豬毛菜群落、花棒—白刺—霧冰藜—沙蓬群落、白刺+沙蓬—沙蒿群落和白刺—檉柳群落共6個類型。不同群落類型間植被數量特征存在顯著差異,白刺+沙蓬—沙蒿群落和白刺—檉柳群落下土壤水鹽含量與其他群落類型存在顯著差異,且研究區土壤鹽害類型主要以氯化物—硫酸鹽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