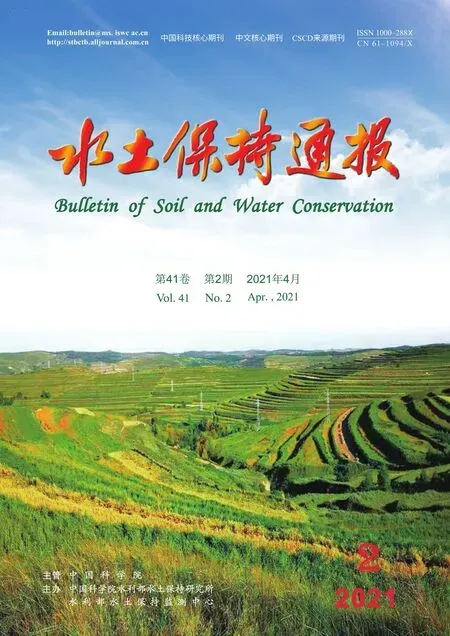在騰格里沙漠東南緣應用沙漠造林器栽植檸條的試驗研究
唐希明, 李敏嵐, 屈建軍, 宋乃平, 孟 晨
(1.中衛市自然資源局中衛市治沙林場, 寧夏 中衛 7550001; 2.寧夏大學西北土地退化與生態恢復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 寧夏 銀川 750021; 3.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 敦煌戈壁荒漠生態與環境研究站/沙漠與沙漠化重點實驗室, 甘肅 蘭州 730000)
沙漠化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其危害程度從最初的地表植被逐漸破壞到小面積流沙出現,最后可發展成地表粗化,土壤含水量降低,風蝕嚴重,進而造成可利用土地資源減少、土地生產力嚴重衰退、自然災害加劇等系列問題,對農業、牧業和人民造成嚴重損失[1]。隨著我國在防沙治沙過程中多年的經驗累積,目前可將防沙治沙造林技術分為飛播造林、容器苗固沙造林、大苗深植、“六位一體”栽植、扦插倒坑、高桿造林、沙地直播、設立沙障等技術[1]。根據各沙區的立地條件可自由選擇,本研究區主要采用設立沙障技術。該技術原理是通過機械沙障對下墊面粗糙程度的改變,從而降低底層風速,減弱輸沙強度,最后使流沙表面達到穩定的效果[2-5]從而為苗木根部創造生根條件,使大量根系萌生深入沙層促進水分吸收。由于研究區沙障材料為麥草,其有效使用年限僅4 a[6],故后期灌木的栽植及成活尤為重要,是該區域防沙治沙成功的關鍵所在[2]。現今,在造林過程中對于灌木的栽植主要有種子撒播和苗木栽植兩種方式[8-9]。因沙漠環境嚴酷惡劣,降水稀少,灌木種子萌發率較低,故造林時多采用苗木栽植的方式。干旱、半干旱地區沙漠造林多為無灌溉造林,水分是沙漠植物成活及生長的主要限制因素[10],而該地區植物所需水分主要靠土壤水分供給,所以要在無灌溉區的沙漠進行成片灌木種植,就必須避免原土壤中不必要的水分散失。如今,造林常用栽植方式為傳統栽植(即鐵鍬)——挖坑種樹。其實施過程為先用鐵鍬挖坑,待每條行帶的樹坑全部挖完后領取苗木再進行栽植填埋。該過程中鐵鍬的挖坑動作,會使原先土層結構破壞,將深層土壤翻動至表層,并且由于作業順序所出現的晾曬行為會使深層濕沙土壤水分蒸發,造成嚴重的水分喪失,最終可能導致苗木成活率下降。針對這一問題,有專家發明了新型栽植工具——沙漠造林器,此工具采用直插式栽植原理,可最大限度保證土壤土層結構完整性,在允許范圍內避免部分土壤水分喪失,由此提高苗木成活率。理論上確實如此,但具體兩種栽植方式的差距還沒有一個量的定論。本次試驗則是通過測定兩種栽植方式不同土層土壤水分,并將其進行數據處理分析,探究哪種栽植方式的保水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苗木的成活,為將來大批量高效率栽植提供數據支持。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地點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境內的騰格里沙漠東南緣世行貸款項目區(37.32—37.26N,105.03—104.4E)。騰格里沙漠東南緣地處阿拉善高原荒漠與荒漠草原的過渡地帶,屬于草原化荒漠。因受內蒙古高氣壓的影響,冬春季節寒冷、干燥、多西北風,但也有短暫時間受東南季風的影響。夏秋季節降雨集中,東北風和偏南風轉盛,故兼有大陸性氣候和季風降雨的特點。年平均氣溫9.6 ℃,極低溫為-25.1 ℃,極高溫為38.1 ℃,晝夜溫差大;年平均降水量為186.2 mm,主要集中在5—9月;年蒸發量是2 300~2 500 mm,空氣平均相對濕度為40%,最低為10%;年平均風速2.8 m/s,大于5 m/s的沙風天氣約200 d左右。土壤基質為風沙土,地下水埋深達80 m。地貌形態以格狀沙丘為主,主梁呈東北—西南走向,副梁呈西北—東南走向,主梁是連續的,副梁往往被主梁隔斷。迎風坡向西北,坡度5°~10°,背風坡向東南,坡度30°~32°。其間栽植植被主要有:灌木檸條(Caraganakorshinkill)、半灌木油蒿(Artemisiaordosica)。草本植物主要有霧冰藜(Bassiadasyphylla)、小畫眉草(Eragrostispoaeoides)、蟲實(Corispermumhyssopifolium)、虎尾草(Chlorisvirgata)、砂藍刺頭(Echinopsgmelinii)、沙米(Agriophyllumsquarrosum)。
1.2 研究方法
研究樣地選擇在中衛“世行貸款”項目區2017年所扎設的草方格片區內。其原因是,與2018年所扎草方格片區相比,該區沙面條件穩定,可降低部分環境因素對次此試驗的干擾。并且該區物種豐富度低,尤其沒有多年生草本植物沙蒿,排除了其他灌木物種以及沙蒿對本次栽植物種的影響。試驗時間為2019年9月22日至2019年10月7日,試驗時間和每年實際栽植苗木時間相一致。所選苗木也是“世行貸款”項目區的主要灌木物種——檸條,具體參數詳見表1。苗木栽植規格以世行項目統一規格為準,是1 m×3 m。采用2種栽植方式:一是傳統方式即鐵鍬栽植;二是新型方式即沙漠造林器栽植。為達到試驗效果,完成試驗目的,特在該片區無植被的草方格中設置1組對照(CK:對照組全程不栽植植物),共計3種處理。

表1 所栽苗木的基本特征
根據試驗目的要求,試驗栽植操作過程及養護管理措施與實際栽植完全一致。具體操作如下:鐵鍬組先挖苗木栽植坑,大小約為35 cm×35 cm×25 cm,然后使栽植坑暴露陽光下晾曬30 min,最后將檸條植入坑中并完成填坑;沙漠造林器組栽植時主要利用植苗鏟末端叉住樹苗根部,雙手握住手柄,一腳踩住腳蹬順勢將苗木向下直插,進入草方格中央土壤,最后向上提起沙漠造林器,栽植完成。
兩組栽植同時進行,試驗期間也未對其進行澆水、施肥等養護管理。此次共栽植檸條48棵,每組24棵,栽植完成后使用鋁盒對3種處理下的土壤水分進行分層取樣,然后用烘干法(105 ℃,24 h)測定土壤含水量。因鐵鍬挖掘深度為30—38 cm,沙漠造林器深度為50 cm,所以取樣深度設置為0—5,5—10,10—15,15—20,20—25,25—30,30—35,35—40,40—50 cm。取樣間分別為0,1,3,5,7和10 d。為降低試驗誤差,每次取樣均在距檸條5 cm處取樣,且重復2次。
1.3 數據分析方法
1.3.1 土壤含水量 土壤含水量(土壤含水率)是指土壤中絕對含水量,該試驗所測定的是土壤重量含水量,計算公式為:
土壤含水量(重量/%)=
(1)
1.3.2 土壤有效含水量 利用土壤有效含水量測定土壤中可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水分含量,其計算公式為:
土壤有效含水量=土壤含水量-凋萎濕度
(2)
1.3.3 單個樣地不同土層土壤水分虧缺程度評價 利用土壤水分相對虧缺指數(compared soil water deficit index, CSWDI),評價單個樣地不同土層土壤水分相對虧缺程度[11]。
(3)
式中:i為第i土層; CPi為對照樣地第i土層土壤濕度; SMi為樣地第i土層土壤濕度; WM為凋萎濕度。
1.3.4 變異系數Cv利用變異系數Cv[12]對土壤水分垂直變化層次進行劃分,表示各層次土壤水分的穩定性。
(4)
(5)
式中:x為觀測樣本(土壤重量含水量)平均值;n為樣本總個數;xi為樣本的第i個觀測值。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完成數據處理后,使用SPSS 22.0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Surfer 13.0繪制土壤水分垂直分布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處理下土壤水分垂直變化規律
數據經統計處理,在采用兩種不同方式栽植檸條后,其土壤水分整體表現為,鐵鍬、造林器0—50 cm土層中土壤平均含水量分別是0.87%,1.08%。與CK土壤含水量相比,鐵鍬減少了0.14%,造林器增加了0.07%,并且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3者并無顯著性差異(p>0.05)。將3種處理下土壤含水量分層展示,結果如圖1所示。3者的土壤水分垂直動態均表現出,土壤含水量隨土層深度的增加呈先增大—后減小—再增大的波動型變化,其波動范圍為:CK(0.4%~1.45%)、鐵鍬(0.38%~1.32%),造林器(0.43%~1.48%)。且鐵鍬和造林器的土壤含水量變化趨勢相一致,2者都在10—15 cm土層到達第一個峰值,土壤含水量分別是1.08%,1.48%,然后下降,直到25—30 cm土層到達最小值(0.66%,0.83%)開始上升。整個過程中,造林器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鐵鍬,最高達1.42倍,最低是1.04倍。

圖1 3種處理下各土層土壤含水量
2.2 不同處理下土壤有效含水量垂直變化規律
沙漠地區土壤含水量一般都相對較低,可被植物吸收利用的土壤水較少,通常該區域土壤凋萎濕度為0.6%[13],使用土壤有效含水量公式進行計算,結果為沒有檸條栽植的CK組在試驗期間0—5 cm土層土壤有效含水量-0.2%,即土壤中含水量不滿足植物的吸收與利用;而在10—15 cm土層中土壤有效含水量最大是0.85%;在0—50 cm土層中土壤有效含水量范圍在0.16%~0.85%(圖2)。鐵鍬組在試驗期間0—5 cm土層土壤有效含水量-0.22%,同樣無法滿足該土層中植物對土壤水的吸收及利用;并且10—15 cm土層中土壤有效含水量0.48%并非是最大有效含水,其最大值出現在40—50 cm土層,值為0.72%;整個土層(0—50 cm)土壤有效含水量范圍在0.06%~0.72%。造林器組在試驗期間0—5 cm土層土壤有效含水量-0.17%,也無法滿足植物需求;但10—15 cm土層中土壤有效含水量0.88%,是3種處理下土壤有效含水量最高值;在0—50 cm土層中土壤有效含水量范圍是0.23%~0.88%。總體而言,通過對比3種處理下的土壤有效含水量可以得出CK、鐵鍬及造林器0—5 cm土層的土壤含水量皆是無效含水,都無法供給植物正常生長生理所需,并且無效程度大小排序:鐵鍬>CK>造林器。在整個土層(0—50 cm)中土壤有效含水量范圍大小順序為:造林器>CK>鐵鍬。3種處理的土壤有效含水量不僅最大值與最小值不同,其出現的土層也不盡相同。CK最小值出現在20—25 cm土層,而鐵鍬和造林器都出現在25—30 cm土層中;CK和造林器最大值表現在10—15 cm土層,鐵鍬則是在40—50 cm土層。

圖2 3種處理下各土層土壤有效含水量
2.3 不同處理下各土層土壤水分相對虧缺特征
土壤水分相對虧缺指數(CSWDI)是具體評價土壤水分是否缺失的一個衡量指標,可以清楚的評估出土壤剖面上不同層次土壤水分相對虧缺的程度,一般CSWDI值越大,表明土壤水分虧缺越嚴重,若值小于0,表示土壤水分沒有虧缺[8,14]。圖3是兩種栽植方式作用下各土層土壤水分的相對虧缺指數,CK作為參照樣地,鐵鍬組的CSWDI值波動較大,且土壤水分虧缺土層較多。其中虧缺嚴重的是20—25 cm土層,CSWDI值達到5.64;10—15,25—30,30—35,35—40 cm土層屬于輕微虧缺,CSWDI值分別是0.2,0.34,0.43,0.48;40—50 cm土層CSWDI值為0,土壤水分沒有虧缺也沒有補充,處于臨界狀態;0—5,5—10,15—20 cm土層土壤水分得到輕微補充,CSWDI值分別是-0.04,-0.54,-0.02。相較鐵鍬組的土壤水分相對虧缺指數而言,造林器的波動幅度較小,并且土壤水分虧缺土層相對較少。CSWDI最大出現在5—10 cm土層,值為2.15,土壤水分虧缺程度較為嚴重;10—15,25—30,30—35 cm土層土壤水分屬輕微虧缺,CSWDI值分別為0.21,0.18,0.07;0—5,15—20,20—25,35—40,40—50 cm土層土壤水分均不同程度得到水分補充,CSWDI值為-0.23,-0.37,-0.44,-1.24和-0.62,其中35—40 cm土層土壤水分補充量相對最高。整體來看,鐵鍬組土壤水分得到補充的土層大多出現在表層,如0—5,5—10,15—20 cm土層,而隨著土層深度的增加土壤水分反而出現虧缺。造林器組的土壤水分相對虧缺指數變化規律不明顯,其土壤水分的虧缺與補充隨土層深度的增加呈交替嵌套式存在。

圖3 2種栽植方式下各土層土壤水分相對虧缺指數
2.4 不同處理下各土層土壤水分變異系數變化
由表2可見,試驗期間CK樣地中土壤含水量最大值在5—10 cm土層,為2.2%;最小值在0—5 cm土層,為0.08%。鐵鍬樣地土壤含水量最大值在5—10 cm土層,為2.58%;最小值在0—5 cm土層,為0.08%(表3)。造林器樣地土壤含水量最大值在10—15 cm土層,為2.66%;最小值在0—5 cm土層,為0.04%(表4)。3種處理下土壤含水量最低值均出現在0—5 cm土層,而CK與鐵鍬的最大值都出現在5—10 cm土層,造林器則出現在10—15 cm土層。根據剖面(0—50 cm)土壤水分垂直變化變異系數劃分:速變層(Cv≥30%)、活躍層(Cv:20%~30%)、次活躍層(Cv:10%~20%)以及相對穩定層(Cv≤10%)[15-16]因而,對CK樣地,鐵鍬樣地以及造林器樣地土壤含水量垂直變異分層分別為:0—5,20—25 cm為變速層,5—10,15—20 cm為活躍層,10—15,25—50 cm為次活躍層;0—10,15—30 cm為變速層,10—15,30—40 cm為活躍層,40—50 cm為相對穩定層;0—5,10—15,30—35 cm為變速層,25—30,35—40 cm為活躍層,5—10,15—25,40—50 cm為次活躍層。由于在沙漠環境下0—50 cm土層土壤含水量相對穩定性較差,加之人為擾動因素影響,所以試驗中經3種處理所得到的不同土層土壤含水量變異系數差別較大,其劃分結果規律性不強。

表3 鐵鍬處理土壤水分的統計特征

表4 造林器處理土壤水分的統計特征
2.5 不同處理下各土層土壤含水量隨時間的變化
為進一步探究兩種栽植方式對土壤含水量的具體影響,本試驗將連續測定的各土層土壤含水量按時間順序將整理,繪制出圖4。由圖4可知,在栽植當天CK土壤表層含水量在1%以上的土層為0—15 cm,隨著時間的推移表層土壤含水量下降,15—20 cm土層土壤含水量增加,到了試驗第7天CK組5—50 cm土層土壤含水量明顯增加,均大于1.1%并一直持續到試驗第10 d。相比CK組,試驗初期鐵鍬組表層土壤水分大于1.1%的土層在0—25 cm,而25—50 cm土層土壤水分不足1%,最小為0.27%,在試驗第5 d時所有土層土壤含水量都低于1%,除20—25 cm土層外,其他土層土壤含水量都不足0.5%,直到試驗第7 d各土層土壤含水量有所回升,僅35—50 cm土層土壤含水量超過1.4%。使用造林器栽植當天土壤表層含水量在1%以上的土層同樣出現在0—15 cm,由于人為擾動較小整個土層在試驗第3 d土壤含水量明顯增加,隨時間推移從試驗第8 d開始各土層土壤含水量略有下降,并一直到試驗結束。

圖4 3種處理下各土層土壤含水量時間變化
3 討 論
根據氣象數據顯示,研究區在試驗前3 d有降雨事件發生,降雨量約為13 mm,對于騰格里沙漠流動沙丘土壤入滲而言,屬于有效降雨量(>6.4 mm)[17]。所以第一次取樣時,土表0—15 cm土層土壤含水量均相對較高。但由于鐵鍬組在苗木栽植過程中的挖掘及晾曬操作,致使25—40 cm土層土壤水分蒸發、流失,土壤含水量降低。在后期完成栽植填坑后,含水量較高的土壤大多堆積在0—20 cm土層中,使其含水量較其他土層略高一些。根據劉新平等[18]對流動沙丘的研究發現,0—20 cm屬于沙丘的干沙層范圍,因此在植被尚未穩定建立時,該土層變異系數較大,隨著時間推移,土壤水分受蒸發量的影響而降低[19]。這與試驗后續的試驗結果相吻合。沙漠造林器組栽植方式以直插式為主,操作簡單,擾動小,大大降低了各土層土壤水分的損耗風險,故該組作用下的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鐵鍬組,最高達1.42倍,最低是1.04倍。而鐵鍬組栽植時因其作業特點使部分土壤水分喪失以致其各土層土壤含水量均低于CK組,最大減少26.36%。以CK為對照,3種處理下的土壤水分垂直動態規律總體表現為,土壤含水量隨土層深度的增加呈先增大—后減小—再增大的波動型變化,但變化土層不同。這主要和試驗處理方法有關。
干旱、半干旱沙漠地區環境嚴酷惡劣,光熱資源豐富,水資源卻嚴重匱乏。對于該地區生活的植物,水是限制其生長的主要因素[20-21],合理有效利用有限水資源已成為植被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基礎[22]。據研究表明,不同植物類型在其各生長階段的水分利用策略不同[23-24]。對于檸條而言,賈志清等[25]認為5 a生植株主要利用20—50 cm土層的土壤水,而9 a和25 a生的植株則主要利用30—50 cm土層的土壤水。結合試驗所用檸條參數及栽植深度確定,鐵鍬組檸條主要利用15—40 cm土層土壤水,造林器組檸條主要利用20—50 cm土層土壤水。經過數據統計分析發現,鐵鍬組15—40 cm土層,平均土壤含水量為0.96%;造林器組20—50 cm土層,平均土壤含水量為1.18%。二者對比后可知,造林器組可為植物多提供1.2倍的土壤水。從土壤水分虧缺方面來看,以CK為準,鐵鍬組CSWDI值波動較大,土壤水分虧缺土層較多,特別是20—25 cm土層虧缺嚴重,10—15,25—30,30—35,35—40 cm土層屬輕微虧缺;造林器組CSWDI值波動幅度較小,土壤水分虧缺土層較少,虧缺程度較為嚴重的是5—10 cm土層,10—15,25—30,30—35 cm土層屬輕微虧缺,對檸條生長影響較小。
通過各土層土壤水分連續監測結果可知,在試驗中除表層土壤含水量隨時間推移一直降低外,其他土層土壤含水量均有增加情況出現,但因栽植方式不同,其增加時間、持續時間以及增加的土層都有所不同,以致對土壤水分影響程度不同,進而栽植苗木成活率也不相同。據統計,對同年不同栽植方式的檸條林進行多次抽檢,其結果為鐵鍬栽植苗木成活率為45%~55%;沙漠造林器栽植苗木成活率為70%~75%,提高了25%左右。
4 結 論
(1) 在草方格內進行人工栽植,采用沙漠造林器栽植會大大降低各土層土壤水分的損耗風險。造林器作用下的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鐵鍬,最高達1.42倍,最低是1.04倍。
(2) 兩種栽植方式深度不同,以致檸條根系所在土層不同,進而對水分的利用策略不同。鐵鍬組檸條主要利用15—40 cm土層土壤水,造林器組檸條主要利用20—50 cm土層土壤水。經分析得出造林器組所對應的土層土壤水分虧缺程度較輕,更有利于檸條的初期生長。
(3) 在栽植苗木成活率方面,鐵鍬栽植苗木成活率為45%~55%;沙漠造林器栽植苗木成活率為70%~75%,提高了25%左右。沙漠造林器栽植苗木成活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