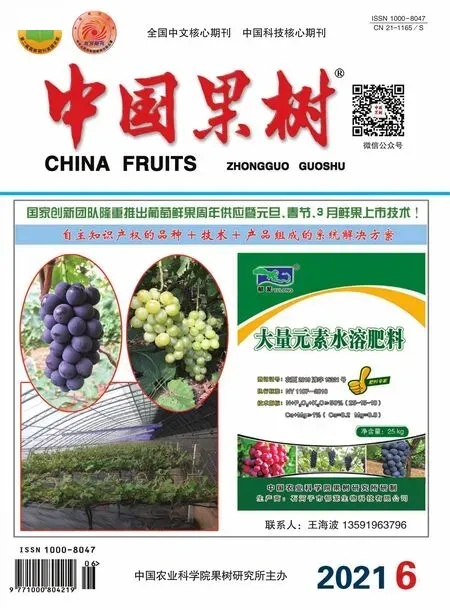不同地區蘋果黃蚜對3 種常用藥劑的敏感性*
封云濤,李 婭,郭曉君,庾 琴,張潤祥
(山西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農業有害生物綜合治理山西省重點實驗室,太原 030031)
蘋果黃蚜(Aphis citricola von der Goot)又名繡線菊蚜,是我國北方果園的重要害蟲。蘋果黃蚜以成蟲及若蟲群集在寄主植物蘋果、梨、海棠等薔薇科果樹的嫩葉背面和新梢嫩芽上刺吸汁液,使被害葉片彎曲或卷縮,影響光合作用,嚴重時導致早期落葉、樹勢衰弱及誘發霉污病[1-2]。蘋果黃蚜1 年發生10 余代,以卵在寄主枝杈、芽旁及皮縫處越冬;第2 年寄主萌動后越冬卵開始孵化為干母,4 月下旬開始為害,5—6 月為發生盛期,為害一直持續到9 月。山西省、山東省和陜西省是我國北方重要的蘋果優勢產區,蘋果黃蚜發生普遍,為害嚴重[3-6]。近年來,蘋果黃蚜除了在嫩枝廣泛發生,在大發生期時也常為害幼果,嚴重影響果實品質。
多年來,對蘋果黃蚜的防治一直以化學防治方法為主,長期頻繁地使用同一類藥劑,使蘋果黃蚜在20 世紀90 年代已經對溴氰菊酯、氰戊菊酯、氧化樂果、甲氰菊酯等多種藥劑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7-10],給防治帶來了很大難度。目前,登記用于防治蚜蟲的藥劑主要有啶蟲脒、吡蟲啉、溴氰菊酯、噻蟲嗪、阿維菌素、呋蟲胺、礦物油等,復配產品以擬除蟲菊酯和有機磷或新煙堿類殺蟲劑為主[11]。據筆者近年來的調查,蘋果園使用最多或高頻次使用的藥劑,啶蟲脒、吡蟲啉、高效氯氟氰菊酯等位居前列,1 個生長季用藥6~7 次,有的地區已出現防效明顯下降、用量大幅增加等問題。為明確蘋果黃蚜對最常用農藥的敏感性水平現狀,我們連續3年比較了山西省、山東省和陜西省蘋果園蘋果黃蚜對3 種主要防治藥劑的敏感性,以期為田間合理使用及防治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供試藥劑
供試藥劑均為原藥,97.3% 吡蟲啉(imidacloprid)和97.6%啶蟲脒(acetamiprid),江蘇農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產;96.1%高效氯氟氰菊酯(lambda-cyhalothrin),江蘇皇馬農化有限公司生產。
1.2 供試蘋果黃蚜種群
(1)田間種群。2017—2019 年每年5—7 月分別采自山西省運城市臨猗縣猗氏鎮翟村、山東省棲霞市臧家莊鎮大欒家村、陜西省咸陽市禮泉縣烽火鎮高家村,寄主蘋果品種分別為‘紅富士’‘嘎拉’‘紅富士’。
(2)相對敏感種群。蘋果黃蚜相對敏感種群2020 年采自山西省農業科學院玻璃溫室蘋果樹上,現采現用。蘋果樹2015 年種植,品種為‘紅富士’,至今未曾施過藥。
1.3 室內毒力測定
采用浸葉法[12]。在預備試驗的基礎上,用丙酮將原藥溶解并配制成母液,用蒸餾水將藥劑依次配成5~7個濃度梯度。其中高效氯氟氰菊酯配制成5、10、20、40、80、160、320、480 mg/L 藥液,吡蟲啉配制成5、10、20、40、80、160、320 mg/L 藥液,啶蟲脒配制成2.5、5、10、20、40、80、160、240 mg/L藥液。采摘蘋果幼葉,在藥液中浸泡5 s,用吸水紙吸取多余藥液后放入培養皿中,接入個體大小一致的健康無翅成蚜,24 h 后檢查死蟲數,用毛筆輕觸蟲體,以不能正常爬行為死亡,每個處理重復4 次,每次重復20~25 頭蟲。對照處理死亡率在10%以下為有效試驗。
敏感基線測定中高效氯氟氰菊酯配制成0.5、1、2、4、8、16 mg/L;啶蟲脒和吡蟲啉的敏感基線,參考封云濤等[13]研究結果。
1.4 數據分析
試驗數據用Probit 幾率值分析法計算毒力回歸方程、致死中濃度及95%置信限等。以各殺蟲劑LC50與相對敏感種群毒力基線致死中濃度進行比較,計算抗性倍數(RR)。
抗性水平按照沈晉良等[14]方法進行劃分,RR<3為敏感,3≤RR<5 為敏感性下降,5≤RR<10 為低水平抗性,10≤RR<40 為中等水平抗性,40≤RR<160 為高水平抗性,RR≥160 為極高水平抗性。
2 結果與分析
2.1 敏感基線
測定了高效氯氟氰菊酯對蘋果黃蚜相對敏感種群的毒力,其致死中濃度為1.74 mg/L(表1)。蘋果黃蚜對啶蟲脒和吡蟲啉的敏感基線,參考封云濤等[13]報道的數據。

表1 蘋果黃蚜對3 種殺蟲劑敏感基線
2.2 不同地區蘋果黃蚜田間種群對3 種藥劑敏感性
以2.1 敏感基線為基礎,連續3 年測定了山西、山東和陜西三地蘋果黃蚜田間種群對3 種殺蟲劑的敏感性(表2)。結果表明,2017—2019 年采自三地的蘋果黃蚜種群對啶蟲脒敏感性下降,產生了低水平至中等水平抗藥性,抗性倍數為7.9~19.3,致死中濃度為22.30~54.29 mg/L,且各地不同年份間抗性水平沒有差異。
不同地區蘋果黃蚜種群對吡蟲啉敏感性處于下降及低水平抗性階段。山西種群敏感性下降,抗性倍數為2.3~4.1;陜西種群在2017 年和2019 年均為敏感性下降,2018 年達到低水平抗性,抗性倍數為6.2,與山東種群無明顯差異;山東和山西種群3 年間對吡蟲啉的敏感性變化不大(表2)。

表2 不同地區2017—2019 年蘋果黃蚜對3 種殺蟲劑的敏感性
不同地區蘋果黃蚜種群對高效氯氟氰菊酯敏感性下降程度較高,均產生了中、高水平抗性,抗性倍數為12.5~44.6。其中,2017 年山西和山東兩地蘋果黃蚜種群對高效氯氟氰菊酯表現為高水平抗性。同一年度不同地區蘋果黃蚜種群對高效氯氟氰菊酯抗性之間無明顯差異。
3 結論與討論
害蟲對藥劑的敏感水平與諸多因素有關,其中農藥的使用是最重要因素之一。農藥的不合理使用,如長期使用單一藥劑或生長季節內多次使用同一藥劑,都會導致害蟲對藥劑的敏感性下降。及時了解和掌握害蟲對藥劑的敏感水平及其分布,可以為農藥的合理使用和延長重點保護的藥劑類別及品種使用年限提供指導和依據[15]。
我們于2010—2011 年測定了山西省運城地區蘋果黃蚜的敏感性,測定的3 類殺蟲劑中,煙堿類的啶蟲脒和吡蟲啉毒力最高[13]。與之相比,本研究中吡蟲啉處于敏感性下降階段,啶蟲脒處于低水平抗性階段,表明了運城地區蘋果黃蚜種群與8 年前相比,敏感性呈逐年下降趨勢,這與運城地區果農在防治時不斷加大用藥劑量和濃度情況相一致[5]。張存環等[16]報道,禮泉蘋果黃蚜種群對吡蟲啉較為敏感,致死中濃度為20.95 mg/L;武榮祥[17]研究表明,2015 年采集的陜西禮泉黃蚜種群對吡蟲啉和啶蟲脒均處于敏感水平,其致死中濃度分別為30.660、51.085 mg/L;本研究表明,2017—2019 年陜西禮泉黃蚜種群對啶蟲脒和吡蟲啉的敏感性均已下降。彭波等[18]2010 年研究表明,山東省主要蘋果產區的蘋果黃蚜對吡蟲啉產生了較高水平的抗性,對啶蟲脒的敏感性比吡蟲啉要高一些,本研究中則是啶蟲脒的抗性高于吡蟲啉,由于其采用點滴法測定,因而不能與本研究致死中濃度進行比較。有較多的田間防治試驗表明,吡蟲啉和啶蟲脒防治蘋果黃蚜仍然有效[11,19-20],但該類藥劑防治時的施藥濃度卻一直在提高,說明了害蟲對這類藥劑敏感性在逐年降低,抗性水平隨著用藥時間和用藥量的不斷增加而升高,因此,在山西、山東和陜西蘋果產區需要嚴格控制煙堿類殺蟲劑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數。三地蘋果黃蚜對高效氯氟氰菊酯均為中高水平抗性,宮慶濤等[11]研究發現,當高效氯氟氰菊酯用量為8.3~12.5 mg/L 時,整個試驗期間對蘋果黃蚜防治效果均在55.1%以下,基本失去防治作用,故今后不宜推薦使用。
目前,蘋果黃蚜防治藥劑類型比較單一,為了延長殺蟲劑使用壽命,延緩抗性產生,可以將不同作用機制的藥劑聯合使用,如氟啶蟲胺腈與阿維菌素、吡蟲啉等混配作為替代藥劑防治蘋果黃蚜[21],以及使用一些功能性助劑來減少藥劑的施藥量[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