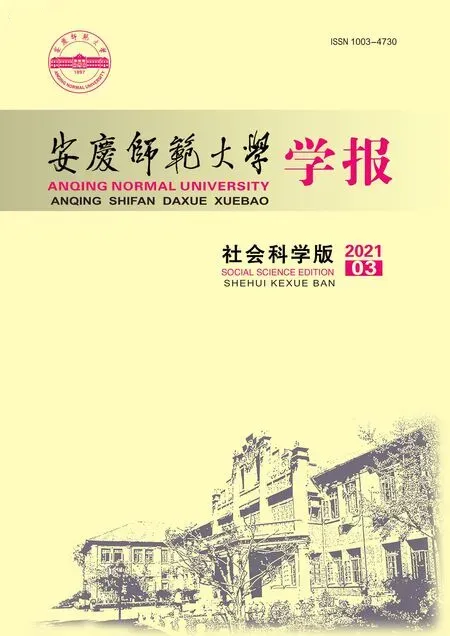姚鼐書法藝術的韻質美
尹忠俊
(安慶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安徽安慶246133)
一、韻的美學意涵
“韻”這一具有審美意味的概念與音樂相關,曹植《白鶴賦》:“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1]韻在此處是指體現琴聲“和”特征的韻律。魏晉時期,本來只同音樂之美有關的韻這一美學概念逐漸地運用于人物品藻領域,《魏故博陵太守邢偉府君墓志》在描述墓主邢偉其人時使用了猶如繪畫中意象性的修辭手法,這種意象性評價語匯需要讀者加入想象力才能建構墓主人的人物形象,其墓志銘記載:“展如君子,實邦之俊。如淵之清,如樂之韻。振藻春華,摛文玉潤。孝睦家庭,朋友以信。”[2]79韻在此種語境中具有雙重意味,一層意為音樂的韻律,另一層則表示墓主人邢偉人物形象和精神氣質具有如音樂般悠揚綿遠、優雅標致之美。墓志撰寫者把墓主這種可以直觀感受到的內在精神氣質之美與樂音訴諸于聽者所產生的類似于優雅、美妙意象性畫面或情境相比擬,一方面暗示撰文者駕馭華麗辭藻和修辭手段的卓越能力,另一方面則豐富和加深對墓主人神采風度的認知。如果說這種人物評價還和音樂領域中的韻(或與韻相關聯的想象)有比附的成分,那么南朝宋時期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品藻則是直接以韻去評價和把握人物內在的精神之美。
《世說新語·品藻》評衛永:“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游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3]280又載:“冀州刺史楊準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準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3]301品題阮渾一則說:“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3]449此三則品題之中分別使用了“風韻”“高韻”“韻度”三個詞來品目人物,大致是指人物由表及里所呈現出來的風姿韻度、高邁深韻,偏向于人物內在的精神氣質和情狀。此外,在三國魏時期的一些墓志中,也出現了以“韻”直觀描述人物風度的例子。《鄭道忠墓志》記載墓主人:“君氣韻恬和,姿望溫雅,不以臧否滑心,榮辱改慮,徘徊周孔之門,放暢老莊之域,澹然簡退,弗競當涂。”[2]130《元愔墓志》也有相似的表述:“君風神清舉,氣韻高暢,孝友天至,學藝通敏。”[2]232此二則墓志之中的‘氣韻’指的是墓主人的風神韻度。以上引文中分別出現了高韻、風韻、韻度、氣韻四個詞,是直接由韻字組合而來的,用來品鑒人物內在的神韻和風度。可見,在魏晉時期的墓志銘文和人物品藻一類的文學作品中,既有對人物的自然風貌、個性特征,即容貌的品議,又有對人物的精神才情、神韻風度的品鑒,但最終則是由外及里、由形到神,重點突出人的神韻和風采。
上引人物品藻中所使用的詞匯——高韻、風韻、韻度、氣韻等,這些詞匯可以訴諸直觀、想象和情感體驗,因此這種人物品藻不僅僅是一種品鑒活動,更帶有審美性質,它與一般美感和藝術是相通一致的,這種品評詞匯自然可以用于書法品鑒領域。魏晉時期審美性人物品藻的發展,使得魏晉名士們對美的細膩的感受能力和表達能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種對人物的品題和審美欣賞漸而擴展到自然和藝術領域。李澤厚先生認為“對‘人物之美’的‘品題’和自然美、藝術美的‘品題’,三者常常是互相溝通的”[4]90。徐復觀先生則說得更加具體:“魏晉時代對于美的自覺,和古希臘時代有相似之點,即是由人自身形象之美開始,然后再延展到文學及書法、繪畫等方面去。當時的繪畫,是以人物為主。而這種人物畫,正是要把上面所述的,由人倫鑒識轉換后所追求的形象之美,亦即是在人倫鑒識中所追求的形象中的神,在技巧上把它表現出來。”[5]
可見,這種用來評價人物精神內涵和氣質的韻自然也可以用于藝術評論中,人物主體的情性、氣質、風神自然也會體現于其藝術作品之上。
二、書法語境中的“韻”質美
在書法品評領域,也常常出現帶有審美性質的“韻”或“韻”的復合性概念,只不過韻的內涵和審美意象發生了變動。魏晉六朝時期的書法品評詞匯和語意還沒有完全脫離音樂中關于韻的本體意味,表現出審美主體借助于已有的對于音樂審美的經驗——審美意象或意境遷移到對書法藝術的審美之上,從而獲得兼具音樂和書法二者共性且融通時空的審美體驗。
南朝王僧虔《書賦》一文在描述書法這種情感性藝術時說道:“爾其隸明敏婉,蠖絢蒨趨,將蒨文篚縟,托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云郁,輕若蟬揚。”[6]20“蒨文篚縟”意為書法藝術語言(線條、造型、章法等)表現為視覺的猶如繁麗紋錦般精美;而“托韻笙簧”意謂書法中所寄托的情韻或表現的意象如笙簧之樂音婉轉悠揚、清幽泠泠,具有綿遠悠邈、含蓄不盡之美。南朝袁昂《古今書評》品鑒殷鈞書法所用韻則與王僧虔有所不同,因為袁昂所使用的“韻”已經跨越了音樂領域中韻的特征和意涵:“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7]74意味著殷鈞書法具有粗獷豪放,意氣勃發的審美意象,卻缺乏優雅含蓄的韻味,此處的韻純粹是書寫主體在其書法中由精神品質所折射出來的韻味和情態。
王僧虔和袁昂的書法品評之中所用“韻”這一概念,均說明了“韻”的特質(類似于音樂的韻律和人物品評中的精神內涵之美)在書法作品或書法審美活動中得以某種程度的表現。一方面,優秀的書法作品應具備音樂般和諧的美的律動,這種律動亦是主體有節奏的生命活動;另一方面,書法作品應具有“韻”的美感,有韻即有美,無韻則不美。因此,“韻”與高雅潔凈、優美精致、瀟灑飄逸的審美意象相呼應。“韻”更是創作主體的才情、智慧、精神美的表現,是一種難于言傳的內在的精神性的美。李澤厚說:“‘氣韻’的概念,歸根到底是要求從主體生命的有節奏、合規律的運動中表現出主體精神的美,使主體的個性、氣質、才情之美獲得一種具有音樂性的美的表現。”[4]791
姚鼐在其題跋作品中所主張的韻與上述韻的意味和特質基本相仿,同時又把體現在韻內涵深處的精神之美加以延伸了,從而擴大了韻的意涵范疇。姚鼐《跋王子敬辭令帖》:“是帖未見古摹,此乃明嘉靖中吳章杰摹本,多姿媚而少古韻,乃有唐李北海等筆法,竊疑非子敬跡也。”[8]217姚鼐首先判斷此貼為唐書家李北海或與李氏風格相似的書家所為,這種判斷主要是依據書法風格,后人普遍認同的李北海書風為“奇崛倜儻、險峭爽朗”,特別是學李氏風格的書家較為容易產生“姿媚”類型的作品。恰恰這種“姿媚”成為姚鼐存疑的有力依據。姚鼐在此跋中透露出更為重要的觀點即為此帖姿媚有余而乏古典(抑或高古)的韻味意趣。可見,姚鼐比較看重富有“古韻”的書法作品。當我們考察姚鼐的詩文思想時,這種重“古韻”的觀念也能得到印證。如姚鼐為既是其叔父亦為其門徒的姚興澩撰寫詩稿序言時就使用了“清韻”這一評價語匯:“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為淺俗之言。其才于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解,為之皆有法度,而尤長者在詩。”[8]38我們從姚鼐的評述中獲知姚興澩所為詩篇具有“清韻”之境,且這種清韻之中內含高古、古風、古典之意,因為姚興澩“不為淺俗之言”,與古為徒,浸淫于古文經籍和駢體之文,為詩文有法度。
姚鼐在為其友人方澤撰寫的墓志銘中也肯定了這種帶有古風的“潔韻”:“先生為文,高言潔韻,遠出塵壒之外,場屋主文俗士,不能鑒也。其守頟頟,以古為則,不為俗惑,英英高云,以壯其文。”[8]158這種“潔韻”的獲得,姚鼐的描述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即以古為則,恪守古道,不與俗尚為伍,更不為世俗所迷惑。因此,這種韻和詩境與姚興澩所創造的詩境和韻味有相似之處,即韻而有古味,韻而不俗。
姚鼐在書法上重“古韻”的觀念與其在詩文方面看重“清韻”是一致的,也透露出姚鼐所看重的這種韻——排斥俗、贊賞古韻、修煉和提升自我修養,正如趙建軍所說“智慧多于交感,超俗多于應世——韻在超俗”[9]。韻所要求的自我修養與主體的學問積累和文化內涵是分不開的。宋代書家黃庭堅就明確說明了這一點,其跋蘇軾書法:“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痩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于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10]從黃庭堅的題跋可見黃氏對蘇軾書法面貌的姿媚之趣、天然痩勁之象、類似于李邕奇崛雄放之風十分肯定和贊賞,當最終得出帶有評論性和主觀性的結論——蘇軾書法筆力圓健遒拔,以情韻勝,“本朝第一”——則把這種贊賞推向了頂峰。這種韻與其厚重的學問修養和忠義品性是有內在聯系的,書韻蘊含著學養和品格。
考察姚鼐《惜抱軒法帖題跋》,我們基本上可以推測,姚鼐對超越時俗、極具個性的書法十分欣賞。姚鼐跋《冠軍帖》:“長史固有筆力,然只是塵埃之雄俊。此大令書,如化人飛行空中,長史何由望及哉!”[8]491張旭和王獻之均為書法史上造詣高深、特立獨行的書家。無論其書法,還是其人物才情,都給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姚鼐認為二人之間仍然有高下之分:張旭書法為塵俗之“雄俊”,獻之書則為仙界之“化人”,由于獻之書法具有“化人飛行空中”般輕盈靈動、飄逸灑落、如仙人若隱若顯的書境和情味,姚鼐對獻之書法更加欣賞,這種書境和超俗之味也對應了獻之其人無一點塵埃氣、高尚其志的情性,姚鼐在此也是間接地贊賞王獻之高謝風塵、內在修性并超越自我的精神之美。
姚鼐對這種拔俗之韻的肯定和贊賞在他另一則題跋中再一次得到證實。姚鼐跋王獻之《桓江州帖》:“論二王書,譬之論李杜之詩。太白作五言詩,固為妙矣。然必至其歌行,瑰詭縱蕩,窮態極變,乃所以為大家而與杜并也。大令草書,能變右軍之法,極其筆力,雄奇怪偉,超絕古今。《桓江州》及《委曲前書》等帖,皆古今絕出之奇筆,如祖師禪,如佛入魔,無不可者。”[8]510我們可以從姚鼐的跋語中體會到姚鼐在評價獻之書法時使用了一些意象性的修辭,這些修辭體現了獻之書法和李杜之詩所共有的或相似的帶有某種神秘感、不可名狀的審美意象或作品意境——雄奇詭譎、超絕古今、即佛即魔、神出鬼沒、變幻莫測,這些修辭手法或評價策略正體現了書寫者強烈奔放的生命活動和特立獨行的個性和趣味追求,書寫過程亦即書家生命活動的表現和人格魅力的綻放。
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中國的書法,是節奏化了的自然,表達著深一層的對生命形象的構思,成為反映生命的藝術。”[11]392宗白華先生又說:“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乃是自始至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構成為一個有骨有肉有筋有血的字體,表現一個生命單位,成功一個藝術境界。”[11]146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取韻其實質為追求生命的強度和生命的趣味,韻體現著書法藝術中的生命和律動。
“韻”這種審美特征體現于書法作品之中便表現為和諧而有節奏變化,整體上具有音韻之美,同時又富有情趣和意味。綜觀姚鼐行草書法作品,這種“韻”的審美表征,不僅體現于富有音韻之美的書法線條以及起伏跌宕、節奏分明的書法體勢之中,亦體現在書寫時表現于時間因素之上的墨色變化——濃淡、潤燥、輕重、虛實之上,更是書家自身內在生命律動、風神才藻、才情個性的自然流露,正如韓德林先生所說:“審美對象的內在生命顯現出來的具有韻律美的形態。”[12]——即書家的風神才情、精神氣質內化于書法作品中所形成的書法藝術生命力和藝術感染力。
三、韻在姚鼐書法藝術中的體現
書法藝術中,由線條構成的審美意象是抽象的,這種抽象和意境在書法筆墨語言之中又可以被感知。一方面,作為創作主體的生命之“氣”轉化為書法作品美學性質的“氣韻”;另一方面,書法作品在整體上呈現出節奏感、流動感——“韻”的審美意象。這種“韻”的特征在姚鼐的某些書法藝術中得以具體地呈現,表現出相應的筆法、結構與章法。
節奏感可以分為點畫節奏、結體節奏和章法節奏。點畫節奏是由筆跡(筆鋒)的順逆、藏露、干濕、潤燥、徐疾、提按、轉折、纖秾、斷連、輕重等時空美學形式要素構成。(如右圖姚鼐《程魚門編修》手札)第一行“正茲有”三字與其下“瀚已捐”形成了潤燥、秾纖、重輕、徐疾等用筆方面的節奏對比;而第一行“程魚門”、第三行“亦未”、第四行“愍其孤”、第五行“進退”等字組,呈現出“連”的關系和“疾”的節奏,與通篇其余各字的“斷”和“徐”又形成一種對比關系。結體節奏主要由欹正、疏密、大小、寬窄、避就、向背、穿插、朝揖、偃仰等對比要素構成。如第一行“程、編、捐”,第二行“縣、機”,第四行“愍”等字,各單字左右兩部分形成一種“背”的勢態;而第一行“修”、第二行“欲”、第四行“誼”和“孤”、第五行“進”等字,則構成了“向”勢。在通篇平和優雅的基調中偶然間也出現了幾個特立獨行之字,如第一行“魚”字、第四行“年”字,一寬扁橫勢一拉長縱態,一寬舒一縱揚,具備動蕩飄揚之情態,與其余各字平正端和的結構特征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關系,這種不同的結體是對整體平和風格的一種調節并改變了書寫節奏。

章法布局則“窮變態與毫端,合情調于紙上”[7]131,氣脈連貫,一氣呵成,有“一筆書”之意趣和氣勢。(如右圖姚鼐《歸無錫》信札)各行長短不一,錯落有致,行首處于書寫節奏和情感醞釀之始,因此,情感基調平穩,表現為厚重的筆墨語言和漢字造型。行末則處于情感表現巔峰階段,尤其是最后兩行中“珍重不具”和“姚鼐頓首”,一筆完成,情感表現澎湃而淋漓,形式處理方面則更表現出書者的精思巧構,大起大落又歸于和諧統一之中,顯得巧妙多姿,自然生動。墨色隨著書寫時間的推移而呈現出由濃到淡、由潤到燥、由粗到細的節律變化。隨著情感的波動,每行并非平鋪直下,而是表現出微妙的搖曳動勢,通篇書寫流露出勃勃生機和生命的律動。

整體上審美觀照姚鼐書法藝術,我們會從中體味出一種濃郁的書卷氣息和意境,清新脫俗,高逸超拔,氣清而質實。這種自然流露的氣息和意境與姚鼐的人品與學品是內在一致的。姚鼐畢其一生著書立說、傳道授業,棄別仕途與功名,與古為徒,力學古人,涵養胸趣。姚鼐自我內修的學者氣質和溫文儒雅的書卷氣息表現于其書寫活動之中,則體現出一定意味的“韻”的意象。對此,黃庭堅說得比較明確:“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6]60黃庭堅指出,王著書法筆法精熟,所臨習《蘭亭序》《樂毅論》《千文》等作品,妙絕不凡,然而遺憾的是其書缺乏韻味。黃庭堅也道出了書法富于韻味的有效途徑在于“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因此,“讀萬卷書”對于韻的體現則顯得十分重要。董其昌在其《畫禪室隨筆》中也有相似的觀點:“畫家六法,一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13]黃庭堅所言“不隨世碌碌”,亦道明韻與平庸俗氣相抵牾。書家宜滌除胸中塵埃之氣,寄至味于淡泊,雅意于林壑,升華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清明澄澈之境界。蔡襄在《論書》中說:“書法惟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6]51可見,晉時士大夫所追求的是一種清新簡澹、虛懷曠達的生存狀態和思想境界,這種人格追求和自由精神反映在晉人書法之上則表現為脫俗、“風流蘊藉”的審美意境。姚鼐中年棄別官場,雖然他本人沒有直接明說棄官的原因,其做法似乎與晉人追求“以韻相勝”的風格相似——從意適便,順從本意,追求本真,崇尚自由和自然無為,擺脫“官場體制”的牢籠。而姚鼐晚年周游名山大川,著書講學,不求名逐利,不同流俗,似乎也正暗合此旨趣。因此,韻與“法”(或流俗,或羈絆)不相容,有法的約束,反而使其情韻和意味消失殆盡。正如梁巘所說:“晉書神韻瀟灑,而流弊則輕散。唐賢矯之以法,整齊嚴謹,而流弊則拘苦。”[7]581所以,姚鼐這種遠榮辱、超拔達觀的君子式的理想人格和精神追求,也正是其書法遠離俗氣、表現“韻”味、體現書卷氣所需要的。
姚鼐以自己的審美觀念、意趣追求和筆墨語言踐行著“韻”之美、“韻”之趣、“韻”之質。藝術作品中韻的內涵既反映著猶如音樂般的韻律和美,又是主體精神氣質、才情品性和人格魅力的體現。姚鼐所支持和肯定的書韻,實際上需要學問修養和自我修為來支撐,更少不了主體不與俗尚為伍、與古為徒、高尚其志的趣味追求。這種韻也可在書寫過程中一定程度地表現為豐富而變化的筆法墨法、字型結構、整體布局和情緒狀態的節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