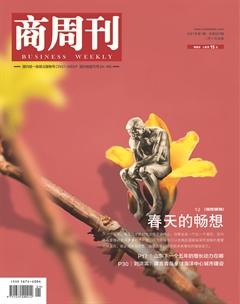劉洪濱:建言青島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
張雅喬



青島港吞吐量現在排在全國第5-7位之間,在全球也是第7-9位的樣子,地位是有了,但是青島要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必須在生產性服務業上下功夫,加快由傳統的裝卸港、目的地港向貿易港、樞紐港轉型。
2020年12月31日公布的《中共青島市委關于制定青島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列為“十四五”期間青島12個具體方面的重點任務之一。
與青島同場參與競逐的是深圳、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大連等城市。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指的是以海洋資源為基礎,擁有領先的海洋核心競爭力,在一定區域內起著樞紐作用且對全球經濟社會活動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城市。
顯然,與以上海為代表的對手相比,青島任重道遠。
在“十四五”開局之際,《商周刊》專訪了青島太平洋學會會長劉洪濱,為青島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幾點思考。
問:為什么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成為了深圳、上海、天津、寧波、舟山、青島、大連等城市紛紛競逐的目標?
劉洪濱:這個概念起源于2012年挪威海事展和奧斯陸海運聯合發布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報告》,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秘書長張春宇團隊將這個概念介紹進中國,將The Leading Maritime Capitals of the World翻譯成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2017年發布的《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提出,推進深圳、上海等城市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這是這個概念首次出現在國內的政策語境當中。而當這兩個城市提出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時候,包括青島在內的其他一些傳統海洋型城市坐不住了,紛紛提出目標,希望能爭得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這頂帽子,其實就是希望能爭取到一些政策和資金支持。但實際上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到底怎么建,大家的方向還不是特別明確。
問:參照國際上的經驗,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需要具備什么要素?
劉洪濱: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應該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國際航運貿易中心,港口與物流服務中心,海事法律中心,海洋教育與科技創新中心,海洋治理與服務中心,海洋生態保護中心,海洋產業基地等。
如此多的桂冠戴在一個城市的頭上,在我看來,沒有一個城市能達到所有的這些標準,有一些比較符合條件的城市,比如倫敦、紐約、新加坡、香港、東京,但也不是方方面面的條件都具備。
我曾在英國待了四五年,對倫敦的情況比較熟悉。倫敦是大家公認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現在倫敦港的貨物吞吐量多年來保持在5000萬噸左右,相比歷史數據,其吞吐量不是在上升反而在下降。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倫敦港的腹地較小,另一個原因則在于老倫敦港地處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沿岸,相當于我們國家的南京港或武漢港,過去航運靠的是幾百噸、幾千噸的帆船,而現在發展到了萬噸、十萬噸級的大船,船越來越大,航道水深不夠,承載大船越來越困難,港口就慢慢地向泰晤士河下游轉移,最后轉移到了泰晤士河河口的蒂爾伯里港區。
從貨物吞吐量來看,倫敦港早已不在全球十大港口之列,但倫敦卻一直是公認的海洋中心城市。它靠的不是貨運量,而是與之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比如航運、保險、金融等等。倫敦有涉海咨詢、中介、代理機構500多家,海事技術人員14000多人,中介機構從業人員4000多人,銀行和保險業從業人員3760多人,仲裁和律師2700多人。超9成的國際海事爭端都選擇在倫敦處理,僅處理海事爭端每年就給英國帶來300億英鎊的收入。此外,作為老牌航運中心,世界20%的船級管理機構常駐倫敦,50%的油輪租船業務、40%的散貨船業務、18%的船舶融資業務和20%的航運保險業務都在倫敦進行。
由此可見,吞吐量已不再是衡量一個港口航運地位的唯一標準。前些年我到日照港和廣西的防城港港,這兩個港口每天忙忙碌碌,但吞吐的都是些散雜貨——煤炭、鐵礦石,都是低附加值的東西,這就相當于裝卸工、搬運工,是藍領。現在統計一個港口的吞吐量有兩個數據,一個是整個吞吐量,另一個是集裝箱吞吐量,如果集裝箱的吞吐量高了,那就是個白領。而像倫敦港這樣從事生產型服務業的,則是高級白領。
后起之秀是新加坡。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由歐美向東亞轉移,新加坡扼守馬六甲海峽航運要道這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抓住了機遇,采取了有效的國策,大力發展航運、臨港產業、貿易、金融等高端服務業,成為新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問:國內幾個城市當中,誰最有競爭優勢?
劉洪濱:深圳在海洋方面起步比較晚,它的優勢在于金融和營商環境方面,除此之外它不具備其他海洋方面的優勢,但是作為后起之秀,胃口很大,來勢兇猛,要辦海洋大學、頂尖海洋研究機構等十大工程,奮起追趕。國內最具優勢的是上海,上海不但是我們國家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人才中心,也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人才中心,營商環境好,也有豐厚的歷史文化,其中也包括海洋文化。
問:與這些城市相比,青島的優勢何在?
劉洪濱:主要有兩個優勢。在國際航運界,凡是注冊總噸在100噸以上的海運船舶,必須在某船級社或船舶檢驗機構監督之下進行監造,船級社就是一個建立和維護船舶和離岸設施的建造和操作的相關技術標準的機構。世界十大船級社,其中9家入駐了上海,1家入駐了深圳。青島則入駐了6家,分別是挪威船級社、美國船級社、日本船級社、英國勞氏船級社、中國船級社和韓國船級社,這是青島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另一個優勢是海洋科研,青島擁有海洋試點國家實驗室、國家深海基地等“國”字號創新平臺,涉海科研機構數量,部級以上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數量,全職在青涉海院士數量三個指標均排名全國第一。
雖然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青島擁有這么多國家級的海洋創新平臺,這體現了青島在海洋基礎科研方面的地位,是青島的面子。但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面子和里子要兼顧,里子就是海洋產業發展、稅收和GDP,具體看對地方產業的拉動、對地方經濟的拉動,這方面的作用不明顯。
青島的涉海人才當中99%從事的是基礎科學研究,基礎科學研究當中又有60%以上人員從事生物方面的研究,這些基礎研究到應用有一段距離。在海洋生產性服務業方面的人才,青島還是比較欠缺,可以說整個國內在這方面的人才培養能力都比較弱,國內有兩所海事大學,分別是上海海事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培養的人才有限,并且有一部分還去了國外。
這幾年人才結構稍微有了改變,為什么?十多年前青島市科技局找到我為市里科技成果轉化提建議,我當時建議要引進“7”字頭的大院大所,即裝備制造領域的工科院所。這些院所,多在內地,我們不求整建制引進,可以引進研究室、分院等團隊。這些院所有很多國家項目,應用性很強,且以工為主。再就是引進大的企業。后來青島西海岸引進了多家“7”字頭的院所,出了不少成果。
問:在您看來,青島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方向和重點應該怎么定位?
劉洪濱:要從加強海洋文化科技交流,提高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做大海洋產業,建立海洋科教體系,建設海洋公共服務中心,加強海洋中心城市研究這六個方面努力。
問:作為傳統的海洋型城市,青島如何加強海洋文化科技交流?
劉洪濱:我們最近在討論海水浴場的提升改造工程,希望能在海邊建一些有海味的雕塑,體量不一定大,但是要有標志性。現在很多外地人去海水浴場,已經到海水浴場了卻不知道這就是海水浴場,開著車往旁邊走一下子就開過了。
更重要的是涉海的文化科技交流。青島在這方面基礎比較好,可是動作慢,體量小。青島有兩個大的節慶,一個是啤酒節,另一個是海洋節。海洋節的其中一個重頭戲是海洋科技論壇,舉辦了十來屆,主辦部門一直在換,論壇名字也不停地換,后來就銷聲匿跡了。前些年外交部和國家海洋局有在我國召開東亞海洋合作論壇的想法,山東和青島把這個平臺爭取過來,落地西海岸。這個論壇辦了幾屆,但不是我想象中的樣子。我認為雖然這個論壇由青島來辦,但代表的是國家,應該站在國家的高度辦論壇,現在搞成了本地自己的活動,站位不高,沒站在國家的角度,甚至連省里的角度都沒站上。另外,一個海洋合作平臺不能開完會就結束了,需要一個常設機構,起到協調、通聯的作用。東亞海洋合作平臺論壇也不一定每年都在青島舉辦,可以今年在青島,明年在韓國釜山之類的地方輪流召開,形成一些社會、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
問: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主要特征是航運服務能力,青島表現如何?
劉洪濱:青島是具備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區位優勢和港口、貿易條件的。2020年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顯示,全球國際航運中心排名中,上海、香港、東京都位于前10位,是東亞國際航運中心的代表城市。舟山、廣州、釜山、青島分別位于第11、13、14和15位,是第二梯隊的代表城市。青島港吞吐量現在排在全國第5-7位之間,在全球也是第7-9位的樣子,地位是有了,但是青島要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必須在生產性服務業上下功夫,加快由傳統的裝卸港、目的地港向貿易港、樞紐港轉型。
具體來看,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要積極與行業協會溝通,引進國際海事組織。第二,強化青島的金融中心功能,引進跨國涉海金融、保險機構。第三,建立航運信息咨詢體系,做好航運中介與代理。這三方面青島目前還有一定的差距,以金融為例,2020年國際金融中心排名當中,前6位分別為紐約、倫敦、東京、上海、新加坡和香港,青島在這一榜單上排名第47位;另外,倫敦有大約600家航運銀行、20多家涉及航運業務的世界大型保險公司,而青島卻沒有幾家,引進涉海金融、航運銀行、頂級保險公司是當務之急。
問:青島的海洋產業目前面臨什么問題?
劉洪濱:青島的海洋產業發展到現在,卻一直沒有大的龍頭產業,也沒有千億級的企業,我們需要在這方面做大,不然要當半島城市群的龍頭,就比較難實現。
問:這是什么原因?
劉洪濱:原因可能在于發展海洋經濟幾十年,但是方向有些偏了,注重了面子,忽視了里子,一些投入比較大的項目,海洋成果轉化不多,產值不高,并沒有達成較為理想的效益。
青島在海洋產業方面缺少大企業、領軍企業,領軍企業不是天生就有的,應該對高端科技小微企業進行扶持發展,目前青島的涉海小微企業不夠多,也不夠活躍。青島早在十幾年前就搞孵化器,一夜之間房子全起來了,卻沒有像樣的企業入駐。某個孵化器給某位院士準備了一處辦公地方,光院士自己的辦公室就有一百多平方米,無非是希望能借他的名聲把孵化器做大。真正需要這些支持的是院士嗎?真正需要辦公室、實驗室的是那些拿不起租金的小微企業。
問:請分析一下青島目前的海洋經濟結構所存在的問題。
劉洪濱:主要是漁業、旅游業和海工裝備三大方面,海洋藥物、海水利用、海洋生物、海洋能源這幾個方面占比都很小。
海水利用是重要的待開發的產業,其中我們最常提的就是海水淡化。
解決供水矛盾,本地的水源肯定是不夠的,特別到了旱季,缺水問題格外嚴重,這就需要增加水源。我們國家目前有幾個重大的調水工程,比如南水北調、引黃濟青,但調水工程只是把甲地的水搬運到乙地,沒有增加新的水源。我國整個北方地區都是貧水區,如果是一個沒有淡化水條件的內陸城市,給它送水過去,這是可以的,但像我們青島守著這么多可利用的海水卻沒有充分利用,這是對資源的一種浪費。
關于調水和海水淡化的成本,有人做過研究:輸水距離超過40公里,淡化就更具有優勢。我們現在的引黃濟青等調水工程,輸水距離平均都在二三百公里左右。有人還具體計算過,南水北調工程輸水到北京,一噸原水的成本是10元,水經過處理到了用戶家里,一噸是12元;現在成規模地進行海水淡化,一噸水的成本在4-6元之間,如果規模再大,成本還會降低。
然而我國的海水淡化做得不盡如人意。我們國家目前的海水淡化規模在千噸級、萬噸級,最多到達十萬噸級別,國外則是在萬噸級到百萬噸級,差距很大。我們除了自己研發之外,還應該積極引進國外技術,把產業做大。青島目前海水淡化的規模是20余萬噸/日,處于國內領先地位,青島是有條件做到日產淡水百萬噸的,但是需要更多政策和扶持。
問:青島海洋旅游面臨什么問題?
劉洪濱:海洋旅游,青島現在的統計指標就是濱海旅游,真正的海洋旅游,喊了30年,但可以說是還沒破題。
海洋旅游包括濱海旅游、遠洋旅游、海島旅游。遠洋旅游目前因為疫情受到了不小的影響,而發展海島旅游,青島應該說是比較有條件的,但是諸如靈山島、田橫島之類的島嶼目前基本都處于沒有被開發、自生自滅的狀態,島上有些村民自發搞的漁家樂,沒有理想的旅游設施和居住條件。搞旅游固然需要大眾化的個體經營戶,但是真正要做大,需要的是大項目。
最近我在幫長島做規劃,長島其實做好兩件事就夠了,一件事是做好長島海洋生態文明綜合試驗區,保護好長島的生態;另一件事是適度發展海洋產業——漁業和旅游業。長島雖然做了30年的旅游,但主要是低端旅游。把海島旅游做好,就要學習馬耳他,做“一島一品”,一個島交給一家有實力的企業,進行適度開發。這個理念是馬爾代夫的理念,馬爾代夫作為千島之國,開發了不到一百個島,一個島交給一家財團來經營,從四星級酒店到五星級再到六星級,不同的島上有不同的酒店、不同的風格,注重生態保護,做得很成功。我的這個理念在珠海被接受了,并在萬山群島得到了實踐,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