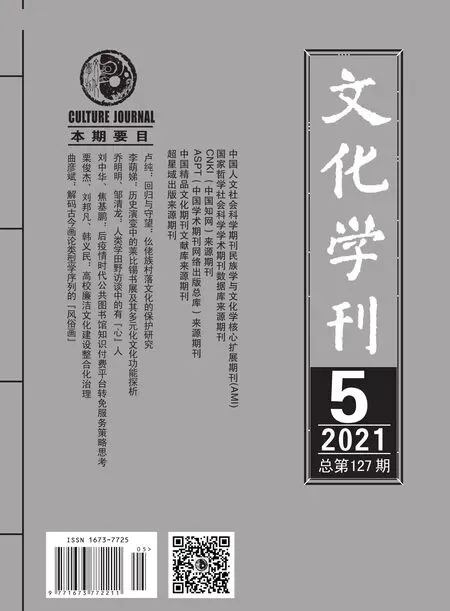論秦國用人與秦文化
潘 婷
從秦穆公任用由余“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到秦孝公啟用商鞅“變法修刑,獎勵耕戰”,重用異國人才一直是秦國用人的傳統。宋朝史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談到秦國用人時曾說:“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1]正如史學家洪邁所說,秦國最終能夠兼并六國,實現天下一統,很大程度上與其用人政策和制度有關。
一、秦用異國人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而始封為諸侯,開始建國,與諸侯各國互通聘享之禮。由于立國較晚,且地處西隅,深受戎狄文化影響,秦國缺乏嚴格的宗法制度,貴賤等級、親疏差別也不似山東諸國嚴格。因此,秦國在用人方面更為容易突破宗法制的束縛,重用他國的賢人良將。秦穆公虛心招攬賢才,“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2]2542;秦孝公為了獲得人才頒布了求才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3]202,商鞅遂聞令入秦,在孝公的支持下積極變法;秦王政時更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3]223,吸引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軍事、外交才能的人才,最終得以一統天下。
戰國后期秦國逐步形成的客卿制度即是秦較早突破宗法制的藩籬,重用外人傳統特點的繼續和發展,也是秦國統治者轉變用人標準,完善官僚政治的必然結果。戰國時期的“客”僅為賓客之意,即使是位尊者,也只能稱之為“上客”,客卿則是客當中入仕居客卿官位的一部分人。客卿制度就是拜“客”為“客卿”的制度,是以客出仕的規范化發展。由客而拜為客卿相對來說較為容易,與國君交談一次獲得認可便可。但拜為客卿之后,還需率兵征戰獲得軍功,才能拜為正卿或相。如張儀、范雎等都是由客拜為客卿后獲得軍功直接升遷為相的。客卿制度將以客出仕和軍功出仕完美結合在一起,“客”始終是底色,軍功才是關鍵,最終實現了用人傳統的制度化。秦自惠文王十年(前328)任魏人張儀為相后,出現了以客出仕的高潮,山東六國之人紛紛入秦。根據史料記載,從惠文王十年到始皇時期,共計22人擔任過秦相,其中籍貫明確為秦國的僅1人,籍貫沒有明確記載的有6人,并且這6人是秦國人的可能性也不大,剩下15人的籍貫均不屬于秦國。雖然始皇時曾因“鄭國疲秦”計劃泄露和秦國宗室的反對,下令“大索,逐客”,但最終因李斯上書《諫逐客書》分析用人利弊,而廢止逐客令。逐客令的廢止也反映了秦“重客”始終是主流,逐客令只是失勢貴族的一次無奈反抗。
二、秦文化的特點
(一)功利性
秦國地處西隅,長期的戰爭環境使得秦人無暇思考倫理道德這些形而上的東西,對他們來說,生存和發展才是最重要的。不論是物質方面還是精神方面,只要有利于秦國發展,統統被吸收和利用。林劍鳴曾就秦人價值觀說道:“在秦人的價值評價中,沒有給道德倫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為標準。”[4]商鞅三次求見秦孝公,分別說以帝道、王道、霸道,但最終以法家理論和霸道學說獲得孝公的青睞并委以行之,充分體現了秦人這一價值取向。同時,在集中反映秦人宗教觀念的《日書》中也很難找到類似周人那樣的道德化的鬼神觀,其中更多的是與實際生活相接近的宗教迷信。秦人崇拜的諸神中不僅有至高無上的“天”和“上帝”,而且有雞、牛、石、書等世間普通的事物。“重功利、尚實際”的價值取向使得秦人更為容易突破宗法制的束縛,任用宗族和本國以外的賢能之人。
(二)尚武性
秦國以武力建國,每一次的國土擴張都伴隨著武力征服,每一次的稱霸都以軍事實力為基礎,國人具有濃厚的戰爭意識。加之商鞅變法后的秦國獎勵耕戰、按功授爵,使得國人形成好戰、重戰、樂戰的觀念。商鞅變法之后,秦國的經濟、軍事實力迅速增強,為了恢復昔日的霸業實現一統天下的政治理想,秦國開始了兼并六國的戰爭。長期而頻繁的戰爭成為秦人生活的重要內容,由此也形成了秦人尚武的傳統。如《詩經·秦風》共收錄了十首詩,其中和戰爭有關的有兩首:《小戎》描寫的是妻子通過回憶出征時的壯觀場面來表現對出征西戎丈夫的思念,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建功立業,平安歸來;《無衣》則是一首慷慨激昂的從軍曲,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等詞直接表現了秦人互相鼓勵、同仇敵愾,共同抵抗西戎的英勇精神。再如《韓非子·初見秦》中描述秦人說:“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皆是也。”[5]在長期的兼并戰爭中,秦國的政治、軍事、外交人才根本不足以滿足其需求,使其不得不廣開門路,大量引進異國的優秀人才。同時,商鞅變法后秦國確立的軍功爵制剝奪了貴族爵位世襲的權利,改變了“任人唯親”的用人標準,為異國謀士良將進入權力機構提供了機會。
(三)開放性
秦建國后,在青銅器、文字以及制度等方面受周文化的影響較大,不過影響范圍僅僅局限于物質方面,思想和價值觀念卻并未改變。秦墓的發掘也表明,秦用的青銅器基本上仿效的是西周風格。戰國時期,秦在李斯、韓非子的影響下逐步接受法家思想,為秦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力量。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有“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2]2544之語,雖多溢美之詞,但也確實反映了秦吸收中原文化的事實。《史記》也說:“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3]239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常常將當地的作坊主和手工業作坊全部占為己有,并遷入秦地,這些同樣是吸收異文化的表現。秦統一后,秦始皇采用了齊人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宣稱秦是以水德王天下,并崇尚黑色,又吸收了神仙家的理論,晚年更是沉迷于“東海求仙”“長生之藥”。從秦開國到一統天下,秦國統治者始終以開放的心態對待外來事物,不管是有才能的異國人士,還是迥異的異族文化,只要是有助于提升秦國綜合實力的事物,都被秦人拿了過去,成了秦國的一部分。
三、秦用人與秦文化
縱觀秦國歷史,大量任用異國的謀臣勇將在其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秦國最終兼并六國、實現統一提供了人才保障。但究其原因,秦國能夠重用他國人與秦國的文化有很大關系。秦國“尚武”的思想觀念使得秦國不斷進行軍事擴張,需要從別國引進大量優秀人才,“重功利”的價值取向又使秦國較易突破宗法束縛,能夠任用異國的良臣猛將,而“兼容并包”的心態使較多的異國人才可以進入秦國的權力中樞。秦國統治者對這些進入官僚隊伍的他國人才不排斥、不猜忌、不生疑,并都能委之以重任。秦穆公時期的由余是西戎之人、百里奚是晉國媵臣,但皆被“授之國政”,使秦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3]194;秦孝公時期的商鞅雖來自衛國,卻被授以變法的大權,最終使秦“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2]2542。由余、百里奚、商鞅、張儀、韓非子、李斯等這些來自他國的政治家、軍事家、改革家、外交家為秦國的崛起和強大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功利、尚武、開放的秦文化影響下,重用他國人的用人觀念深入人心,并將其制度化為客卿制度,而這恰恰也體現了秦國國家權力系統和官僚政治組織的開放性。

秦 云紋 淳化縣涼武帝村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