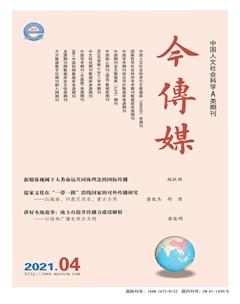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融入”傳播策略
王佳煒
摘 要:國際社交媒體給國際傳播帶來了深度滲透和沖擊,也為陜西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嶄新空間與契機。本文以構建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機制為依托,提出增強陜西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國際社交融入”傳播策略,包括創建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內容資源庫、創設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內容遴選機制、挖掘日常生活維度的陜西故事的國際社交表達、搭建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媒體多源動態監測體系、培育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協同內容生產體系。
關鍵詞:陜西文化;對外傳播;社交媒體;“國際社交融入”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1)04-0114-03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陜西軟實力的重要來源,陜西文化快速走向世界正是積極適應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在文化對外傳播能力視角下,文化對外傳播力是包含在傳播過程之內的研究,文化傳播力指文化通過傳播方式的組合而得到彰顯的能力,簡言之,即文化的對外傳播能力。媒介屬于文化對外傳播力的主要構成要素之一,文化如果要轉化為軟實力就必須借助媒介傳播至國際社會中[1]。
以Facebook、YouTube、Twitter為代表的國際社交媒體給國際傳播帶來深度滲透和沖擊的同時,也給中國文化,甚至于陜西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嶄新空間和契機,如何解決陜西文化對外傳播的“國際社交融入”問題,成為新時期陜西文化對外傳播的新課題。本文以建立基于日常實踐的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機制為依托,提出以下幾點關于增強陜西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國際社交融入”傳播策略,試圖為陜西文化融入全球社交傳播體系探尋長效路徑。
一、創建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內容資源庫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頂層制度設計和具體策略規劃[1],同時還缺乏整合營銷傳播理論IMC指導下的戰略制定和戰術運用,在對外傳播內容導向、傳播內容的選取和形式等維度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問題[2],這些問題也是陜西文化在對外傳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內容是陜西文化對外傳播的承載和起點,特別是社交媒體時代對傳播內容的需求量呈暴增趨勢,根據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發布的全球數字報告顯示,全球42億社交用戶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占上網時間的1/3以上[3],這種7×24在線的溝通常態決定了迫切需要創建一個豐富、全面、立體的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內容資源庫,為陜西文化對外社交傳播提供動力原料庫。
文化是相較于政治、經濟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活動產品,“文化”這一概念本身具有復雜性,不同學者從多個角度給出過多種定義。參照首都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播工程研究院于2015年對法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英國五國的國際受眾進行中國文化認知程度調研時,對中國文化元素的分類方式[4]。可以將陜西文化分為陜西人物、陜西哲學觀念、陜西藝術形態、陜西自然資源、陜西生活方式、陜西人文資源,并在每個類別中另行設定若干個具體文化符號,通過六大類別及其子符號體系構建陜西文化社交傳播內容資源庫。增強陜西文化多層面的立體質感和結構的豐富性,調整和改變在陜西文化的對外傳播中過于依賴歷史文化、傳統文化資源的狀況,從“供給側”加大陜西文化對外傳播中的現當代文化比重。
二、創設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內容遴選機制在社交媒體傳播場域下,關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文化外交、文化的國際傳播等相關領域頗受重視。社交媒體的參與性、復向傳播性、對話性和圈子性有助于提升對外國際傳播的認同感、覆蓋率、親和性和黏合度,這也決定了國際社交媒體成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場域。傳播內容的類型和特點直接影響著社交用戶是否愿意參與社交互動,然而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力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傳播內容的選擇問題。楊澤喜研究發現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內容單一缺乏吸引力,對外文化傳播報道過于集中“高層政治”,導致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內容很難引起國外受眾的關注興趣;于丹、楊越明通過對國外受眾進行在線調查研究后發現,國外受眾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程度整體偏低,同時還存在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內容供給與國外受眾興趣點脫節的現象。此外,缺乏對當代中國生活方式、社會議題和價值觀的討論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內容層面的另一問題。
就陜西文化對外傳播而言,在創建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內容資源庫的基礎上,更需要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創建一套標準化的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內容遴選機制。一方面,這套內容遴選機制是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陜西文化對外傳播內容過濾系統;另一方面,這套內容遴選機制也是基于“他國”受眾視角的,即基于“他國”受眾需求判斷篩選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的內容,因為只有具備能夠滿足“他國”受眾需求的陜西文化對外傳播內容,才可能使陜西文化具有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
三、挖掘日常生活維度的陜西故事的國際社交表達傳播內容的包裝形式欠缺吸引力也是導致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有學者研究發現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方式過于公式化,偏向于集中式正面報道,這種公式化表達與國際傳播語境的不匹配,造成中國文化在國外受眾中傳播效果不佳的狀況[5]。徐翔通過網絡文本挖掘國際社交媒體中的中國文化形象的呈現特征后,發現中國對外文化傳播需要關注生活化和民眾化視角[6],以日常文化形成對精英文化和經典文化的有益補充,優化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內容,讓中國文化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和“他國”受眾中更易被接納與傳播。辛靜、葉倩倩提出,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積極的情感表達亦要通過日常生活的視閾,以基于人類共通情感和價值理念基礎之上的方式完成表述。
對照陜西文化的對外傳播實踐情況而言,一方面,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傳播需要強化陜西文化的日常化內容挖掘,避免傳播內容的刻板化和單一化,積極探索基于日常生活維度的“陜西故事”內容,以親近國際社交用戶的日常化內容激發社交用戶的高喚醒情緒;另一方面,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表達需要充分尊重國際社交用戶的選擇偏好,深挖國際社交用戶感興趣的視角和表達方式,厘清國際社交媒體語法,尋找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的表達范式,將基于日常生活視閾的陜西文化傳播內容以符合國際社交媒體語法的方式進行表達。借助社交媒體的交往實踐實現陜西文化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上對“他國”受眾的日常化融入,以此實現陜西文化在國際社交媒體場域的傳播流轉與價值擴散。
四、搭建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媒體多源動態傳播監測體系5G萬物互聯時代,大規模的跨維度數據(包括網絡用戶行為數據、地理位置數據等)會在人與物、人與人以及物與物相聯的過程中井噴式產生。對傳播而言,數據成為內容生產和內容分發的重要依據,是傳播活動的生產要素,也是人工智能傳播的動力與燃料。面對5G、物聯網、AI等技術應用的持續落地,陜西文化的對外傳播活動需要深化數據驅動意識,即搭建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媒體多源動態傳播監測體系。
一方面,基于大數據,在傳播過程中對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內容進行實時動態監測并維護社交互動的活躍性,為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媒體傳播的每個環節賦能,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實施。1.基于多源信息數據對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目標受眾展開供給側洞察、篩選傳播策略,使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傳播決策建立在客觀全面感知、洞察他國目標受眾的基礎上;2.進行以“個人”為單位的自動化社交傳播內容生產,生產出能夠匹配差異化傳播受眾、個性化場景的定制式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媒體傳播內容;3.在了解國際社交媒體用戶的媒體偏好和深入理解其所在場景的前提下,以自動規劃和精準定向等方式實現高效的流量配置,由此實現在各類場景中細微處理陜西文化對外社交傳播與目標受眾個體的互動關系。
另一方面,通過融合國際主流社交媒體多源信息,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媒體多源動態傳播監測體系圍繞網絡重點目標群體及熱點話題展開深度洞察與多維度分析,對國際社交媒體中與陜西文化相關的態度、觀點或傾向進行實時判斷,助力政府相關機構在海量國際社交媒體數據中第一時間發現陜西文化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傳播熱點和最新動態,追蹤重點目標、對預估的風險可能進行識別并及時預警。
五、培育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協同內容生產體系美國美利堅大學Robert Albro在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案例的研究中發現,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還缺少來自非政府組織、企業和民間傳播渠道的聲音[7]。一方面,在以受者為中心的時代,內容生產權力被不斷分流,曼紐爾·卡斯特爾認為大眾自傳播的演進是傳播轉型中最重要的一類,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信息制造是自我生產的、信息流動是自我定位的、數字傳播網絡內容的接收與融合是自我選擇的[8]。被技術賦權后強勢崛起的UGC和OGC不斷沖擊著傳統PGC的內容生產核心地位,與此同時,基于大數據和算法技術而產生的海量MGC(機器生產的內容)也開始進入線上內容矩陣。傳播內容生產權力的碎片化決定了陜西文化對外社交傳播的內容生產格局勢必發生改變,趨于形成以PGC、UGC、OGC以及MGC并存的在線協同內容生產系統。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傳播需要有效整合PGC、UGC、OGC以及MGC的內容生產力,發揮各自內容生產的優勢,構建陜西文化全球社交傳播協同內容生產體系。
另一方面,陜西文化對外傳播不僅是政府作為主體的傳播,移動社交時代大眾自傳播呈現出向平民化、多維化表達讓渡的趨勢。在強調傳播共振的大眾自傳播時代,激活民間傳播活力是實現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產生“共振”的路徑之一,這就需要構建多元化的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主體,即在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上,鼓勵企業、高校、智庫、網民等作為傳播主體,以公共文化交流的形式,參與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實踐。通過商業文化傳播、教育傳播、國內外文化交流活動、美食等基于日常生活視閾的對外社交傳播融入,激活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傳播的民間活力,傳遞更多平民化和多維化的“陜西聲音”。
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傳播是一個系統工程,既需要建立起集合地域宣傳、文旅歷史、對外文化交流等相關版塊的聯動機制;也需要構建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形成包括地方政府部門、文化部門、企業、民眾,以及對外媒體、文化傳播機構等在內的陜西文化國際社交媒體對外傳播聯動機制。由此打造一套貫通頂層設計至日常運營的陜西文化國際社交整合傳播體系,形塑出被“他國”受眾接納的、值得信任、充滿活力且富有吸引力的陜西文化形象,有效提升陜西文化的國際社交媒體傳播力。
參考文獻:
[1] 李智.對文化軟權力化的一種傳播學解讀[J].當代傳播,2008(3):13-15.
[2] 初廣志.中國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整合營銷傳播的視角[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0(4):101-106.
[3] We Are Social&Hootsuite:DIGITAL 2021-GLOBAL DIGITAL OVERVIEW[EB/OL].https://www.thes table.com.au/wearesocialhootsuitereportonasocialdigitalboomworldwide,2021-01-28.
[4] 于丹,楊越明.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核心命題“供給”與“需求”雙輪驅動——基于六國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度調查[J].人民論壇,2015(24):72-75.
[5] 楊澤喜.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力現狀審視與提升路徑[J].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35(3):58-63.
[6] 徐翔.中國文化在國際社交媒體傳播的類型分析——基于共詞聚類的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37(10):38-45.
[7] Robert Albro (2015) . The disjunction of image and word in US and Chinese soft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4, 382-399.
[8] (美)曼紐爾·卡斯特爾著.湯景泰,星辰譯.傳播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23.
[責任編輯: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