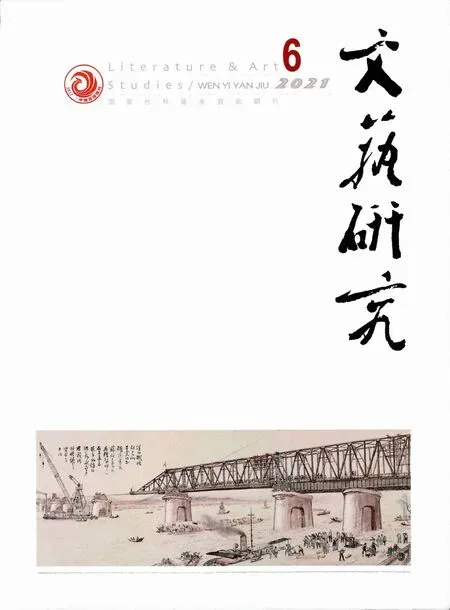形象的旅行
——評(píng)W. J. T. 米歇爾《圖像學(xué): 形象, 文本, 意識(shí)形態(tài)》
陳永國(guó)
《 圖像學(xué): 形象, 文本, 意識(shí)形態(tài)》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中譯本由陳永國(guó)譯出,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出版。 以下引文凡出自該書(shū)中譯本者, 均只隨文標(biāo)注頁(yè)碼) 是W.J.T. 米歇爾“ 圖像三部曲” 的第一部, 原書(shū)1987年面世, 其他兩部為1995年出版的《 圖像理論》 和2005年出版的《 圖像何求: 形象的生命與愛(ài)》 。 該書(shū)是一本闡述圖像及其研究的專(zhuān)著。 本文僅就該書(shū)的主要內(nèi)容——形象的相似性、 形象的文本性和形象的意識(shí)形態(tài)性——進(jìn)行概括性介紹和述評(píng), 以便于讀者深入了解米歇爾圖像學(xué)的任務(wù)、 圖像與文字( 畫(huà)與詩(shī)) 的關(guān)系、 圖像如何傳達(dá)思想和感情以及形象如何建構(gòu)觀念等問(wèn)題。 在介、 評(píng)過(guò)程中, 本文將涉及藝術(shù)史、 藝術(shù)批評(píng)、 語(yǔ)言研究以及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家和思想家, 如馬克思、 萊辛、 維特根斯坦、 貢布里希、 潘諾夫斯基、 古德曼等, 分析各家就形象( 藝術(shù)) 提出的重要思想和觀點(diǎn), 以凸顯當(dāng)下文學(xué)批評(píng)、 藝術(shù)批評(píng)與視覺(jué)文化研究中“ 圖像轉(zhuǎn)向” 的重要意義。

W.J.T. 米歇爾是美國(guó)芝加哥大學(xué)藝術(shù)史系和英語(yǔ)語(yǔ)言文學(xué)系教授, 長(zhǎng)期從事藝術(shù)和文學(xué)批評(píng)。 他將形象、 文本和意識(shí)形態(tài)有機(jī)聯(lián)系起來(lái), 建構(gòu)了一種有關(guān)形象或意象的別開(kāi)生面的圖像詩(shī)學(xué)。 他的《 圖像學(xué): 形象, 文本, 意識(shí)形態(tài)》 主要討論形象這一觀念, 以及相關(guān)的畫(huà)、 想象、 感知、 比擬和模仿等觀念。 該書(shū)力求回答兩個(gè)問(wèn)題: 什么是形象? 形象與詞有何不同? 由此把圖像學(xué)界定為一門(mén)研究用以標(biāo)識(shí)詞、 思想、 話語(yǔ)或科學(xué)的圖像的學(xué)問(wèn)。 這里的“ 圖像” 包括兩個(gè)方面: 就形象之所說(shuō); 形象本身之所說(shuō)。 前者指對(duì)視覺(jué)藝術(shù)的描述和闡釋?zhuān)?后者指形象本身的言說(shuō)。 關(guān)于圖像的這種研究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gè)傳統(tǒng), 就狹義而言, 它開(kāi)始于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切薩雷·里帕的《 圖像》(1593) , 終結(jié)于20世紀(jì)上半葉潘諾夫斯基的《 圖像學(xué)研究》 (1939) ; 就廣義而言, 這個(gè)傳統(tǒng)開(kāi)始于基督教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觀念, 終結(jié)于20世紀(jì)現(xiàn)代科學(xué)的形象制造。 就其所涉的研究問(wèn)題而言也有狹義與廣義之分, 狹義的形象指繪畫(huà)、 雕塑、 肖像等藝術(shù)品, 廣義的形象則包括精神形象、 文學(xué)形象、 詞語(yǔ)中的形象等。 所有這些構(gòu)成了圖像學(xué)研究的核心內(nèi)容(第6—7頁(yè))。
為了進(jìn)一步澄清《 圖像學(xué): 形象, 文本, 意識(shí)形態(tài)》 和《 圖像理論》 中涉及的一系列相關(guān)概念, 米歇爾撰寫(xiě)并出版了論文集《 圖像何求: 形象的生命與愛(ài)》 , 并在該書(shū)中譯本出版之際給中國(guó)讀者寫(xiě)了一篇說(shuō)明, 澄清了四個(gè)基本概念: 圖像轉(zhuǎn)向、 形象/圖像、 元圖像和生命圖像。 在區(qū)別圖像與形象時(shí), 他舉例說(shuō): “ 你可以掛一幅圖畫(huà), 但你不能掛一個(gè)形象。”①畫(huà)是物質(zhì)性的, 可以掛在墻上、 擺在桌上或燒掉, 而畫(huà)留下的印象、 在觀者頭腦中產(chǎn)生的形象, 卻依然存在, “ 在記憶中, 敘事中, 在其他媒介的拷貝和蹤跡中”②。 正如作為實(shí)存之物的金犢消失后, 金犢依然作為形象活在各種故事和無(wú)數(shù)描畫(huà)中。 金犢先以塑像( 肖像) 的形式出現(xiàn), 塑像消失后便留下了它的形象。塑像是金犢形象的載體或媒介, 是其實(shí)質(zhì)性的物的支撐, 在這個(gè)意義上, 金犢的塑像便是它的圖像。 但圖像不止于物的層面, 它還介入精神層面, 作為“ 精神圖像” 或形象跨越媒介, 經(jīng)拷貝、 模仿或改造, 呈現(xiàn)為雕塑、 繪畫(huà)、 語(yǔ)言敘事、 攝影等其他不同表現(xiàn)形式。 因此可以說(shuō), 一個(gè)形象可以有兩種表達(dá), 一種是物質(zhì)性的表達(dá), 如塑像、畫(huà)像、 建筑、 詞語(yǔ)等, 另一種是非物質(zhì)性實(shí)體的、 高度抽象的表達(dá), 它進(jìn)入人的認(rèn)知或記憶之中, 一旦與相應(yīng)的物質(zhì)支撐相遇, 便會(huì)重獲精神圖像③。
質(zhì)言之, 形象就是對(duì)一種相似或相像關(guān)系的認(rèn)知, 它是一種隱喻關(guān)系, 即把兩種視覺(jué)認(rèn)知相互“ 克隆” 或相互轉(zhuǎn)換的關(guān)系, 或把某一形象“ 視為” 另一形象的關(guān)系。最終, 形象必然會(huì)以圖畫(huà)的形式出現(xiàn), 無(wú)論是石板上書(shū)寫(xiě)的“ 十誡” ( 最終被視為基督教教義的權(quán)威) , 還是柏拉圖的“ 洞穴寓言” ( 被視為哲學(xué)的元圖像) , 都體現(xiàn)了形象在認(rèn)知和記憶中的核心作用。 一個(gè)形象是一個(gè)思想的形象。 這種“ 轉(zhuǎn)義” 或向圖像的“ 轉(zhuǎn)向” 并不是現(xiàn)代才有的。 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透視法及其后的架上繪畫(huà)和照相術(shù),都可說(shuō)是歷史上重要的向圖像的“ 轉(zhuǎn)向”, 并且每一次都是從“ 詞” 到“ 象” 的轉(zhuǎn)向。在這個(gè)意義上, 米歇爾在其“ 三部曲” 中所描述的“ 圖像轉(zhuǎn)向” 主要針對(duì)的是理查德·羅蒂的“ 語(yǔ)言轉(zhuǎn)向”, 后者認(rèn)為20世紀(jì)的西方哲學(xué)將原本對(duì)物自身的關(guān)注轉(zhuǎn)向了對(duì)觀念和概念的關(guān)注, 因此把一切問(wèn)題都?xì)w結(jié)為語(yǔ)言。 而在米歇爾看來(lái), 語(yǔ)言也許不是根本,20世紀(jì)中期至今的圖像和視覺(jué)文化研究已經(jīng)從特殊的藝術(shù)史轉(zhuǎn)向了一個(gè)“ 擴(kuò)展的領(lǐng)域”, 一種新的“ 形象的形而上學(xué)”, 因此可以說(shuō)是又一次“ 圖像轉(zhuǎn)向”④。
一、形象的相似性
歷史上, 形象經(jīng)歷了從“ 偶像崇拜” 到“ 偶像破壞” 的歷次宗教、 社會(huì)和政治運(yùn)動(dòng), 又經(jīng)過(guò)索緒爾、 維特根斯坦、 喬姆斯基、 潘諾夫斯基和貢布里希等語(yǔ)言學(xué)家和藝術(shù)史家的符號(hào)化、 理論化和體系化, 已經(jīng)不再是用于認(rèn)識(shí)世界的透明窗口, 不再單純是“ 一種特殊符號(hào), 而頗像是歷史舞臺(tái)上的一個(gè)演員, 被賦予傳奇地位的一個(gè)在場(chǎng)或人物, 參與我們所講的進(jìn)化故事并與之相并行的一種歷史, 即我們自己的‘ 依照造物主的形象’ 被創(chuàng)造, 又依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自己和世界的進(jìn)化故事” ( 第5頁(yè)) 。 形象具有了歷史性, 因而不同程度地具有了虛擬性, 成為文學(xué)批評(píng)、 藝術(shù)史、 神學(xué)和哲學(xué)等領(lǐng)域中意識(shí)形態(tài)化和神秘化的一個(gè)再現(xiàn)機(jī)制。 如果按照“ 相似、 相像、 類(lèi)似” 的特征,形象便可以依據(jù)維特根斯坦的“ 家族相似性” 理論, 進(jìn)入圖像、 視覺(jué)、 感知、 精神和詞語(yǔ)諸范疇, 進(jìn)而涉及心理學(xué)、 物理學(xué)、 生理學(xué)、 神經(jīng)學(xué)等生命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 而一旦從福柯的“ 物的秩序” 這一普遍原則來(lái)思考形象所內(nèi)含的和諧、 模仿、 類(lèi)比、 共鳴諸關(guān)系, 就不可避免地從“ 精神圖像” 的視角進(jìn)入詩(shī)歌、 繪畫(huà)、 建筑、 雕像、 音樂(lè)、舞蹈等藝術(shù)。 最終, 形象必然會(huì)作為一個(gè)無(wú)意識(shí)深層結(jié)構(gòu)從語(yǔ)言中浮現(xiàn), 成為一種融合精神形象與物質(zhì)形象的“ 語(yǔ)言形象”, 它是語(yǔ)言中蘊(yùn)含的形象, 而不是語(yǔ)言本身。
語(yǔ)言中蘊(yùn)含著形象。 語(yǔ)言是思與詩(shī)對(duì)話的場(chǎng)所。 詩(shī)的本質(zhì)不是對(duì)仗或音韻的和諧,而是對(duì)行為的模仿和形象的再現(xiàn); 詩(shī)不是一種語(yǔ)言形式, 而是一個(gè)故事, 其成敗在于故事的虛構(gòu)。 “ 如果詩(shī)歌和繪畫(huà)可以相互比較, 并不是因?yàn)槔L畫(huà)是一種語(yǔ)言, 或繪畫(huà)的色彩與詩(shī)歌的單詞有相似性; 而是因?yàn)槎叨荚谥v述一個(gè)故事, 這個(gè)故事為普遍的、基本的準(zhǔn)則帶來(lái)了選題和布局。”⑤這就是米歇爾所說(shuō)的人“ 依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自己和世界的進(jìn)化故事”。 在這個(gè)故事中, “ 詞是思的形象, 而思是物的形象” ( 第23頁(yè)) 。作為實(shí)存的人經(jīng)過(guò)“ 物的形象” ( 原始印象) 和“ 思的形象” ( 精神圖像) 而變成了故事中的詞語(yǔ), 也就是從“ 流自物體自身的形象” 變成了“ 來(lái)自語(yǔ)言表達(dá)的形象”( 第24頁(yè)) 。 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 詩(shī)人以更有力的筆觸讓后者占了上風(fēng), 使描摹的美超過(guò)了自然的美, 語(yǔ)言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lái): 雨果的浪漫主義圖景并不是由教堂的石塊而是由“ 物質(zhì)性的” 詞語(yǔ)構(gòu)筑的, 福樓拜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并非是由實(shí)證性的生活數(shù)據(jù)而是由“ 華而不實(shí)” 的言辭組成的, 馬拉美的象征主義詩(shī)歌也并非是由隱喻性的詞語(yǔ)而是由“ 沉默的言語(yǔ)” 構(gòu)成的。 這些物質(zhì)性的詞語(yǔ)、 華而不實(shí)的言辭和沉默的言語(yǔ), 不是情感于瞬間的自然宣泄( 華茲華斯) , 不是于瞬間呈現(xiàn)思想和情感的綜合體( 龐德) , 也不是沒(méi)有思想而只有物的“ 流自物體本身的形象” ( 艾迪生) , 而是“ 由某一命題投射出來(lái)的‘ 邏輯空間’ 里的‘ 圖畫(huà)’” ( 維特根斯坦) , 是現(xiàn)實(shí)經(jīng)過(guò)“ 思” 之中介在語(yǔ)言中形成的“ 圖畫(huà)” ( 第24—27頁(yè)) , 也是既使用語(yǔ)言又使用圖畫(huà)的一種符號(hào)性認(rèn)知活動(dòng)。它便于我們深入理解傳統(tǒng)認(rèn)識(shí)論中詞、 思、 形象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這種關(guān)聯(lián)便是相似性。
從根本上說(shuō), 相似性不但是西方創(chuàng)世傳統(tǒng)的根基( 造物主依自己的形象造人) , 也是西方美學(xué)的思想基礎(chǔ)( 藝術(shù)首先依據(jù)相似性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模仿) 。 相似性指的不是外形或形狀的相似, 而是靈魂的相似。 偶像崇拜者所犯的錯(cuò)誤在于把外形或物質(zhì)形狀當(dāng)成與靈魂的相似, 甚至當(dāng)成靈魂自身, 偶像破壞者也正是基于這個(gè)理由去破壞偶像的。作為靈魂或精神相似性的形象究竟是什么呢? 一棵樹(shù)與另一棵樹(shù)相似, 但二者之間的相似性絕不構(gòu)成形象。 “‘ 形象’ 一詞只有在我們?cè)噲D建構(gòu)我們?nèi)绾握J(rèn)識(shí)一棵樹(shù)與另一棵樹(shù)的相似性的理論時(shí)才與這種相似性有關(guān)。” ( 第37頁(yè)) 這涉及形象可見(jiàn)的圖畫(huà)意義與不可見(jiàn)的精神意義, 也就是說(shuō), 一幅畫(huà)在可見(jiàn)的畫(huà)框內(nèi)描畫(huà)了一個(gè)可見(jiàn)的世界, 一個(gè)美或丑的世界, 但這個(gè)可見(jiàn)的世界同時(shí)也遮蔽著一個(gè)不可見(jiàn)的世界, 它可以是畫(huà)框外的世界, 可以是畫(huà)面掩蓋的世界, 也可以是畫(huà)面在觀者意識(shí)中激活的一個(gè)含有各種可能性的世界, 而那正是作品的世界所回歸之處, 海德格爾稱(chēng)之為“ 大地”。
這意味著繪畫(huà)并非像萊辛所說(shuō)的那樣不能講故事。 萊辛給出的理由是, 繪畫(huà)的模仿是靜態(tài)的, 不是循序漸進(jìn)的, 也即, 繪畫(huà)是空間中的展示, 而不是時(shí)間中的敘事。但繪畫(huà)也同樣在講故事, 繪畫(huà)也是一種敘事。 萊辛用來(lái)開(kāi)啟此番討論的《 拉奧孔》 , 不也在講述拉奧孔和他的兩個(gè)兒子被波塞冬懲罰的故事嗎? 他不也引用了“ 希臘的伏爾太( 按: 伏爾泰) ” 的“ 畫(huà)是一種無(wú)聲的詩(shī), 而詩(shī)則是一種有聲的畫(huà)” 嗎? 盡管這話中所含的道理如此明顯, “ 以致容易使人忽視其中所含的不明確的和錯(cuò)誤的東西”⑥。而這不明確或錯(cuò)誤的東西就是: “ 畫(huà)和詩(shī)無(wú)論從模仿的對(duì)象來(lái)看, 還是從模仿的方式來(lái)看, 卻都有區(qū)別。”⑦
然而, 對(duì)象也好, 方式也好, 無(wú)論區(qū)別有多大, 它們都不涉及本質(zhì)的相似性。 蘇東坡提出“ 詩(shī)中有畫(huà), 畫(huà)中有詩(shī)”。 詩(shī)畫(huà)同質(zhì), 所同之“ 質(zhì)” 就在于二者賴(lài)以構(gòu)成的形象性。 萊辛把同質(zhì)的藝術(shù)分成專(zhuān)注于行動(dòng)進(jìn)程的“ 時(shí)間藝術(shù)” 和只呈現(xiàn)瞬間凝滯畫(huà)面的“ 空間藝術(shù)”。 前者是詩(shī), 即使拉奧孔因哀號(hào)而變形的臉被描寫(xiě)得丑陋可憎, 慘不忍睹, 卻仍由于不那么直觀和明顯而讓人能夠接受; 后者是畫(huà)或雕塑, 其直觀性會(huì)使人對(duì)丑陋產(chǎn)生反感, 因此就只能把拉奧孔的“ 放聲號(hào)叫” 刻畫(huà)成“ 輕微的嘆息”, 這樣才不至于破壞“ 希臘藝術(shù)所特有的恬靜和肅穆”⑧。 在萊辛看來(lái), 這完全是古代藝術(shù)模仿美和描畫(huà)美的要求使然: 藝術(shù)是用來(lái)表現(xiàn)美的, 即使在表現(xiàn)極度扭曲的痛苦時(shí)也必須避免丑⑨。 而在翁貝托·艾柯看來(lái), 萊辛的意義恰恰就在于他以此開(kāi)啟了“ 丑的現(xiàn)象學(xué)”, 發(fā)動(dòng)了浪漫主義對(duì)丑的拯救⑩。
雖然萊辛堅(jiān)持認(rèn)為, 在引起快感方面, 詩(shī)和畫(huà)對(duì)丑的處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但他承認(rèn)“ 無(wú)害的丑在繪畫(huà)里也可以變成可笑的……有害的丑在繪畫(huà)里和在自然里一樣會(huì)引起恐怖”?, 因?yàn)槌笸瑯涌梢杂|及靈魂。 這意味著, 丑與美一樣, 也可以實(shí)現(xiàn)藝術(shù)的崇高, 也可以使靈魂升華, 也即, 丑可以通過(guò)視覺(jué)認(rèn)知中的形象轉(zhuǎn)化來(lái)實(shí)現(xiàn)美的“ 崇高” 目標(biāo)。 實(shí)際上, 在萊辛生活的18世紀(jì), “ 崇高” 已經(jīng)成為思想家和藝術(shù)家們經(jīng)常討論的話題, 并由此而改變了人們對(duì)丑陋和恐怖事物的看法, 也就是說(shuō), 在美的問(wèn)題上, 重點(diǎn)討論的已經(jīng)不再是美的規(guī)則, 而是美( 丑) 對(duì)人的認(rèn)知作用。 埃德蒙·伯克提出, 我們?cè)谀慷帽╋L(fēng)雨、 洶涌的海浪、 危險(xiǎn)的懸崖、 深淵絕谷、 陰森洞窟等恐怖事物時(shí), 只要它們不危及、 傷害我們, 我們就會(huì)產(chǎn)生快感。 康德把感官無(wú)法掌控、 想象卻可以擁抱的事物, 如星空和遠(yuǎn)山, 稱(chēng)作“ 數(shù)學(xué)式的崇高”, 把震撼我們靈魂、 使我們自感渺小并因此用道德的偉大來(lái)彌補(bǔ)的自然威力, 如暴風(fēng)雨和霹靂, 稱(chēng)作“ 力學(xué)式的崇高”。 席勒認(rèn)為崇高產(chǎn)生于我們對(duì)自身的局限之感。 黑格爾認(rèn)為我們?cè)诂F(xiàn)象界找不到足以表現(xiàn)無(wú)限之物, 所以才產(chǎn)生崇高之感。 丑進(jìn)入了審美的范疇, 進(jìn)入了基督教圣像學(xué), 正是從黑格爾發(fā)現(xiàn)美與丑的沖突開(kāi)始的?。 這一切都離不開(kāi)詩(shī)畫(huà)所共享的形象, 這形象就在語(yǔ)言和色彩之中, 我們既能再度尊崇形象表達(dá)的詞語(yǔ)的雄辯力, 同時(shí)也看到詞語(yǔ)中圖畫(huà)的再現(xiàn)力。 “ 想象力的救贖就在于接受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 即我們是在詞語(yǔ)與圖像再現(xiàn)之間的對(duì)話中創(chuàng)造了我們的世界。” (第54頁(yè))
二、形象的文本性
被萊辛稱(chēng)為“ 希臘的伏爾太” 的人, 是克奧斯的西蒙尼德斯。 他提出的“ 畫(huà)是一種無(wú)聲的詩(shī), 而詩(shī)則是一種有聲的畫(huà)”, 引起了西方古往今來(lái)關(guān)于詩(shī)畫(huà)的論爭(zhēng)。 然而,這場(chǎng)論爭(zhēng)“ 絕不僅僅是兩種符號(hào)之間的競(jìng)爭(zhēng), 而是身體與靈魂、 世界與精神、 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一場(chǎng)斗爭(zhēng)”, 用以標(biāo)志詩(shī)與畫(huà)之間差異的符號(hào)是“ 文本與形象, 符號(hào)與象征, 象征與語(yǔ)象, 換喻與隱喻, 能指與所指”, 它們之間并不構(gòu)成尖銳的二元對(duì)立, 而呈現(xiàn)為互補(bǔ)對(duì)仗的形式( 第58—59頁(yè)) 。 需要經(jīng)過(guò)復(fù)雜的推演, 才能從對(duì)仗中見(jiàn)出互補(bǔ)。 米歇爾的推演開(kāi)始于達(dá)·芬奇的《 繪畫(huà)論》 : “ 如果你, 詩(shī)人, 描寫(xiě)某些神的形體,那被寫(xiě)的神就不會(huì)與被畫(huà)的神受到相同的待遇, 因?yàn)楫?huà)上的神將繼續(xù)接受叩首和禱告。各地的人們將世世代代從四面八方或東海之濱蜂擁而至, 他們將求助于這幅畫(huà), 而不求助于書(shū)面的東西。” ( 第153頁(yè)) 出于對(duì)繪畫(huà)的偏愛(ài), 達(dá)·芬奇強(qiáng)調(diào)眼睛與其他任何感官相比都不易受到欺騙。 受到誰(shuí)的欺騙? 當(dāng)然是形象。 達(dá)·芬奇顯然觸及了一個(gè)不容否認(rèn)的事實(shí): 感官印象并不可靠, 其中摻雜著幻想的成分, 因而具有欺騙性。 無(wú)論是眼見(jiàn)還是耳聽(tīng), 其實(shí)都并非原初的“ 實(shí)”, 即使清晰準(zhǔn)確的理想的語(yǔ)言表達(dá), 也會(huì)受到相似性和形象的誘惑, 而不足以控制“ 幻想的畫(huà)面”。 米歇爾在此引用的是伯克的觀點(diǎn)。在伯克看來(lái), 崇高需要用詞語(yǔ)來(lái)表達(dá), 而美需要由繪畫(huà)來(lái)描畫(huà)。 詞語(yǔ)之所以是表達(dá)崇高的媒介, 恰恰因?yàn)樗鼈儾荒芴峁┣逦男蜗蟆?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 朦朧就是崇高, 愉悅就是痛苦消失后或遠(yuǎn)離痛苦之時(shí)的感覺(jué), 而崇高與美在藝術(shù)上和身體上的區(qū)別就是詞語(yǔ)與形象、 痛感與快感、 模糊與清晰、 智力與判斷之間的對(duì)立。
如果我們?cè)俅斡貌说挠^點(diǎn)來(lái)對(duì)應(yīng)萊辛關(guān)于詩(shī)畫(huà)的區(qū)分, 就可以得出: 詩(shī)是用詞語(yǔ)表現(xiàn)崇高的時(shí)間藝術(shù), 畫(huà)是用描畫(huà)來(lái)表現(xiàn)美的空間藝術(shù)。 除了時(shí)間- 空間、 崇高- 美的對(duì)應(yīng)之外, 萊辛還提出了另一組對(duì)應(yīng): 身體( 物體) - 行動(dòng)( 情節(jié)) , 并指出物體(身體) 是繪畫(huà)所特有的題材( 對(duì)象) ; 行動(dòng)( 情節(jié)) 是詩(shī)所特有的題材( 對(duì)象)?。 一方面, “ 一切物體不僅在空間中存在, 而且也在時(shí)間中存在”, “ 因此, 繪畫(huà)也能模仿動(dòng)作, 但是只能通過(guò)物體, 用暗示的方式去模仿動(dòng)作”; 另一方面, 動(dòng)作也“ 并非獨(dú)立地存在”, 須依存于作為物體的人或物, “ 所以詩(shī)也能描繪物體, 但是只能通過(guò)動(dòng)作,用暗示的方式去描繪物體”。 如此, 詩(shī)與畫(huà)就都采用暗示或隱喻的方式模仿, 其唯一的區(qū)別在于, 前者通過(guò)動(dòng)作來(lái)模仿, 后者通過(guò)物體來(lái)描畫(huà)。 這是因?yàn)槲矬w美源自雜多部分的和諧效果, 畫(huà)家可以同時(shí)將其并列于畫(huà)面之上, 而用詞語(yǔ)進(jìn)行描寫(xiě)的詩(shī)人則不然,他只能按次序一個(gè)一個(gè)地歷數(shù), 以獲得整體和諧的形象, 最終“ 達(dá)到對(duì)整體的理解,這一切需要花費(fèi)多少精力呀”?! 至此, 關(guān)于時(shí)間藝術(shù)與空間藝術(shù)的問(wèn)題被歸結(jié)為“ 符號(hào)經(jīng)濟(jì)” 的問(wèn)題, 即創(chuàng)造過(guò)程中要付出多大努力來(lái)捋順這些用以標(biāo)識(shí)時(shí)空關(guān)系的符號(hào)。實(shí)際上, “ 藝術(shù)品, 與人類(lèi)經(jīng)驗(yàn)中所有其他物體一樣, 都是時(shí)空結(jié)構(gòu), 而有趣的問(wèn)題就是理解特殊的時(shí)空構(gòu)造, 而不是給它貼上時(shí)間或空間的標(biāo)簽” (第129頁(yè))。
標(biāo)簽還是要貼的, 關(guān)鍵看貼得是否妥當(dāng)。 柏拉圖的《 克拉底魯篇》 主要討論的就是如何正確標(biāo)識(shí)或命名的問(wèn)題, 其結(jié)論是“ 詞自然相似于它們所再現(xiàn)的對(duì)象” ( 第94頁(yè))。 這個(gè)結(jié)論的前提是蘇格拉底提出來(lái)的: “ 由相似性所再現(xiàn)的被再現(xiàn)的物絕對(duì)完全地優(yōu)越于偶然符號(hào)的再現(xiàn)。” ( 第95頁(yè))?“ 由相似性所再現(xiàn)的被再現(xiàn)的物” 顯然可以指基于形象的畫(huà), 而與之相對(duì)的“ 偶然符號(hào)” 則是由習(xí)俗所決定的語(yǔ)言符號(hào)。 達(dá)·芬奇依據(jù)“ 自然相似性” 之理說(shuō)“ 畫(huà)高于詩(shī)”, 因?yàn)楫?huà)模仿自然; 雪萊則斷言“ 詩(shī)高于其他藝術(shù)”, 因?yàn)樵?shī)的媒介是語(yǔ)言, 而“ 語(yǔ)言是由想象力任意生產(chǎn)的, 只與思想相關(guān)” ( 第96頁(yè)) 。 經(jīng)過(guò)懷疑、 辯解、 論證, 貢布里希終于從忽左忽右的兩難狀態(tài)中走出來(lái), 認(rèn)識(shí)到詞語(yǔ)、 圖畫(huà)、 視覺(jué)形象不管包含什么, 都是自然符號(hào)。 畫(huà)與詩(shī)之間的區(qū)別顯然是形象與語(yǔ)言、 自然符號(hào)與習(xí)俗符號(hào)之間的區(qū)別, 但這個(gè)區(qū)別是不真實(shí)的, 因?yàn)樽匀环?hào)只在起點(diǎn)上才是自然的, 如果沒(méi)有這個(gè)起點(diǎn), 我們就永遠(yuǎn)不能獲得使用詞語(yǔ)或形象的技能。 究其實(shí), 貢布里希的形象論所說(shuō)的“ 自然” 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構(gòu)成, 一種特殊的意識(shí)形態(tài), 也是西方文化中特有的物戀或偶像崇拜。 它告訴我們一個(gè)幾乎所有論者都否認(rèn)或忽視的事實(shí), 即無(wú)論是詞語(yǔ)還是形象、 詩(shī)還是畫(huà), 它們只是與所再現(xiàn)或命名的物在起點(diǎn)上有一種自然的相似關(guān)系, 起點(diǎn)之后便都是通過(guò)習(xí)俗和約定運(yùn)作的, 因此都是不完善的、 有偏差的, 不能完整準(zhǔn)確地反映或再現(xiàn)事物的真實(shí)(第115頁(yè))。
這就是說(shuō), 詩(shī)與畫(huà)都依賴(lài)相似性再現(xiàn)其客體, 而相似性是無(wú)所不包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根據(jù)相似性來(lái)描述, 因此它不是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必要和充足條件。 詩(shī)或畫(huà),文本或圖畫(huà), 語(yǔ)言的圖像理論或圖畫(huà)的圖像理論, 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dú)說(shuō)明藝術(shù)或世界的“ 差異語(yǔ)法”, 無(wú)法證明“ 世界存在的方式”, 這是尼爾森·古德曼的結(jié)論: “ 對(duì)語(yǔ)言的圖像理論的破壞性攻擊是, 一種描寫(xiě)不能再現(xiàn)或反映真實(shí)的世界。 但是我們已經(jīng)看到, 一幅畫(huà)也做不到這一點(diǎn)。 我開(kāi)始時(shí)就丟掉了語(yǔ)言的圖像理論, 結(jié)論時(shí)采用了圖畫(huà)的圖像理論。 我拒絕用語(yǔ)言的圖像理論, 理由是一幅畫(huà)的結(jié)構(gòu)與世界的結(jié)構(gòu)并不一致。 然后我得出結(jié)論, 使某物與之相一致或不一致的世界結(jié)構(gòu)這種東西并不存在。 你可以說(shuō)語(yǔ)言的圖像理論與圖畫(huà)的圖像理論一樣虛假或真實(shí); 或, 另言之, 虛假的不是語(yǔ)言的圖像理論, 而是關(guān)于圖畫(huà)和語(yǔ)言的某種絕對(duì)觀念。” ( 第76—77頁(yè)) 米歇爾指出, 古德曼似乎對(duì)絕對(duì)論者“ 犯下了每一種可能的罪過(guò)”: 他否定了用以檢驗(yàn)語(yǔ)言和圖畫(huà)再現(xiàn)的一個(gè)世界的存在, 顛覆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再現(xiàn)的地位, 把幾乎所有的象征形式和認(rèn)知行為“ 都簡(jiǎn)化為建構(gòu)或闡釋”, 而地圖與畫(huà)、 形象與文本之間的嚴(yán)格區(qū)分并不是由共享的自然所決定, 而是由“ 共享的慣習(xí)” 所決定的(第78—79頁(yè))。
這決定了古德曼獨(dú)樹(shù)一幟的“ 密度” 論, 即用有刻度的和無(wú)刻度的溫度計(jì)來(lái)區(qū)分近乎確定的閱讀和不確定的閱讀。 刻度等于密度, 在有刻度的溫度計(jì)上, 水銀抵達(dá)之點(diǎn)都是確定的或近似于確定的, 因此是確定的閱讀; 在無(wú)刻度的溫度計(jì)上, 水銀抵達(dá)之點(diǎn)都是相關(guān)的和近似的, 是一個(gè)無(wú)限數(shù)或系統(tǒng)內(nèi)的一個(gè)記號(hào)。 一幅畫(huà)就好比一個(gè)沒(méi)有刻度的溫度計(jì), 線條、 質(zhì)地、 色彩的每一次變化都具有潛在的意義, 其象征性是超密度的、 飽滿(mǎn)的, 具有無(wú)限的可能性; 而在區(qū)分的符號(hào)系統(tǒng)( 有刻度的溫度計(jì)) 里,一個(gè)標(biāo)記的意義取決于它與所有其他標(biāo)記的關(guān)系( 如字母表中的任一字母) , 它是經(jīng)過(guò)區(qū)分的, 因此是沒(méi)有密度的、 斷裂的和中斷的。 “ 圖畫(huà)在句法上和語(yǔ)義上是‘ 連續(xù)的’, 而文本則采用一組‘ 不連貫的’、 由沒(méi)有意義的空隙構(gòu)成的符號(hào)。” ( 第82頁(yè)) 重要的是, 這兩種溫度計(jì)并不是截然區(qū)別開(kāi)來(lái)的。 也就是說(shuō), 密度的有無(wú)取決于閱讀的方式: 一幅畫(huà)可以被讀作一種描寫(xiě), 放在字母表里按次序來(lái)讀; 而一段話( 文本) 也可以讀作城市景觀(圖畫(huà)) , 作為有密度的系統(tǒng)被建構(gòu)或?yàn)g覽, 其閱讀的方式是由起作用的符號(hào)系統(tǒng)來(lái)決定的, “ 而這通常是習(xí)慣、 習(xí)俗和作者約定俗成的問(wèn)題——因此也是選擇、 需要和興趣的問(wèn)題” (第86頁(yè))。
最終, 米歇爾把上述討論的文本- 形象問(wèn)題歸結(jié)于這樣一個(gè)話題: “ 形象是某種或可獲得或可利用的特殊權(quán)力的場(chǎng)所; 簡(jiǎn)言之, 形象是偶像或物戀。” ( 第192頁(yè)) “ 偶像” 和“ 物戀” 這兩個(gè)概念顯然相關(guān)于位于圖像學(xué)核心的偶像崇拜與偶像破壞, 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意識(shí)形態(tài), 也必然與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píng)密切相關(guān)。 馬克思認(rèn)為, 任何“ 精神事實(shí)” 和“ 概念總體” 都是“ 知覺(jué)和形象同化和轉(zhuǎn)化為概念的結(jié)果”, 他同時(shí)規(guī)定了分析概念的步驟: “ 第一個(gè)步驟就是把有意義的形象簡(jiǎn)化為抽象的定義, 第二個(gè)則通過(guò)推理而從抽象定義到具體環(huán)境的再造。” ( 第201—202頁(yè)) 從形象到抽象, 再?gòu)某橄蟮骄唧w, 這是一個(gè)再生產(chǎn)的過(guò)程。 米歇爾認(rèn)為馬克思是通過(guò)“ 制造隱喻” 來(lái)使概念具體化的, 比如用暗箱中投射的非實(shí)質(zhì)性幻影喻指精神活動(dòng), 而作為精神活動(dòng)的意識(shí)形態(tài)又將自身投射和銘刻到商品的物質(zhì)世界上來(lái)。
三、形象的意識(shí)形態(tài)性
“ 暗箱” 指的是銀版照相法的發(fā)明, 也標(biāo)志著一種新的形象產(chǎn)業(yè)的出現(xiàn)。 有閑階級(jí)可以用這種相機(jī)生產(chǎn)新的收藏品, 又可以將其用作人類(lèi)理解的新模式, 也就是馬克思所說(shuō)的一種虛假理解的模式, 因?yàn)榘迪淅锍尸F(xiàn)的影像是倒置的, 恰如這個(gè)生活世界。倒置的出現(xiàn), 是因?yàn)槟切┪ㄐ闹髁x者是“ 從人們所說(shuō)的、 所設(shè)想的、 所想象的東西出發(fā)”, “ 從口頭說(shuō)的、 思考出來(lái)的、 設(shè)想出來(lái)的、 想象出來(lái)的人出發(fā), 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 我們的出發(fā)點(diǎn)是從事實(shí)際活動(dòng)的人, 而且從他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過(guò)程中我們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guò)程在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fā)展。 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guò)經(jīng)驗(yàn)來(lái)確認(rèn)的、 與物質(zhì)前提相聯(lián)系的物質(zhì)生活過(guò)程的必然升華物”?。簡(jiǎn)言之, 唯心主義者的出發(fā)點(diǎn)是人的意識(shí), 正如蘇聯(lián)時(shí)期的標(biāo)準(zhǔn)手冊(cè)《 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基礎(chǔ)》 中所說(shuō), “ 存在于人的意識(shí)之中的不是物本身或它們的屬性或關(guān)系, 而是精神影像或這些影像的反映” ( 第220頁(yè)) 。 也就是說(shuō), 唯物主義者的出發(fā)點(diǎn)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從事實(shí)際生活活動(dòng)的人, 他們的意識(shí)甚至頭腦中模糊的東西都來(lái)自物質(zhì)生活及其經(jīng)驗(yàn)。 因此, 矯正被唯心主義者所倒置的形象的唯一辦法, 就是將其置于時(shí)間之中,置于歷史生活的進(jìn)程之中。 任何一位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家都必須自覺(jué)依照歷史規(guī)律,從全人類(lèi)的普遍利益出發(fā), 去批判虛假的意識(shí)形態(tài), 而對(duì)于馬克思而言, 全人類(lèi)的利益就是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利益, 其最終目標(biāo)是無(wú)產(chǎn)階級(jí)斗爭(zhēng)和實(shí)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
倒置不僅是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影像之間的形象倒錯(cuò), 它“ 也是意識(shí)形態(tài)自身的一個(gè)特征, 把價(jià)值、 先后順序和真實(shí)關(guān)系倒置起來(lái)” ( 第227頁(yè)) 。 米歇爾認(rèn)為, 相機(jī)的倒置機(jī)制恰恰是浪漫主義文學(xué)中的一個(gè)藝術(shù)手段, 也是視覺(jué)藝術(shù)中至關(guān)重要的一種技術(shù)。作為隱喻, 它不但揭示出意識(shí)形態(tài)的幻覺(jué), 而且成為視覺(jué)藝術(shù)領(lǐng)域中“ 倫勃朗式” 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媒介。 本雅明認(rèn)為, 相機(jī)是“ 在革命世紀(jì)的門(mén)口揮舞的一種兩用引擎”, 攝影是“ 第一個(gè)真正的革命的生產(chǎn)手段”, 是“‘ 與社會(huì)主義的興起同時(shí)’ 發(fā)明的”, “ 能夠使藝術(shù)的全部功能以及人的感覺(jué)發(fā)生一場(chǎng)革命”, 是“ 終結(jié)意識(shí)形態(tài)的‘ 歷史生活過(guò)程’ 的象征”。 相機(jī)的倒置機(jī)制導(dǎo)致了作為藝術(shù)的攝影的問(wèn)世。 然而, 米歇爾指出, 對(duì)本雅明來(lái)說(shuō), “ 攝影既不是藝術(shù), 也不是非藝術(shù)( 純技術(shù)) : 它是改造藝術(shù)整個(gè)性質(zhì)的一種新的生產(chǎn)方式”。 這種生產(chǎn)方式既給第一批攝影師以及后來(lái)作為藝術(shù)家的攝影師帶來(lái)了光暈, 同時(shí)也驅(qū)散了傳統(tǒng)藝術(shù)中縈繞在物周?chē)墓鈺灒?把物從光暈中解放了出來(lái)(第231—233頁(yè))。
對(duì)本雅明贊揚(yáng)的攝影這一革命性媒介, 馬克思始終保持沉默, 這也許是由于他當(dāng)時(shí)對(duì)人類(lèi)學(xué)以及原始宗教發(fā)生了強(qiáng)烈的興趣, 因此無(wú)暇顧及攝影( 也恰恰是這無(wú)暇顧及使他開(kāi)始了更加宏大的《 資本論》 的研究) 。 他從對(duì)人類(lèi)學(xué)和原始宗教研究的閱讀中抽象出“ 商品拜物教” 的概念, 與“ 意識(shí)形態(tài)” 概念構(gòu)成了互補(bǔ): 前者是物質(zhì)的, 是對(duì)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控制, 后者是精神的, 是對(duì)上層建筑的控制, 這兩個(gè)概念都是進(jìn)行偶像破壞的武器, 都是理解藝術(shù)的理想手段。 這并不是說(shuō)藝術(shù)就是商品, 或通過(guò)商品來(lái)研究藝術(shù)(盡管這二者在今天都已成為事實(shí)) , 而是說(shuō)商品與藝術(shù)一樣, 作為透明的存在而被賦予了神秘的屬性, 其意義和歷史屬性也是需要破譯的。 馬克思甚至用浪漫主義美學(xué)和詮釋學(xué)的詞匯來(lái)形容商品, 認(rèn)為“ 商品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 充滿(mǎn)形而上學(xué)的微妙和神學(xué)的怪誕”?。 其神秘性“ 不是來(lái)源于商品的使用價(jià)值, 也不是來(lái)源于決定價(jià)值的性質(zhì)”, 而是源自下列三種形式: “ 人類(lèi)勞動(dòng)的等同性, 取得了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等同的價(jià)值對(duì)象性這種物的形式; 用勞動(dòng)的持續(xù)時(shí)間來(lái)計(jì)量的人類(lèi)勞動(dòng)力的耗費(fèi), 取得了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價(jià)值量的形式; 最后, 生產(chǎn)者的勞動(dòng)的那些社會(huì)規(guī)定借以實(shí)現(xiàn)的生產(chǎn)者關(guān)系,取得了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形式。”?商品的雙重面紗在于它一方面在人們面前呈現(xiàn)為物與物的關(guān)系的虛幻形式, 另一方面, 它又表現(xiàn)為價(jià)值形式和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價(jià)值關(guān)系。馬克思認(rèn)為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一個(gè)適當(dāng)?shù)谋扔鳌?“ 在那里, 人腦的產(chǎn)物表現(xiàn)為賦有生命的、 彼此發(fā)生關(guān)系并同人發(fā)生關(guān)系的獨(dú)立存在的東西。 在商品世界里, 人手的產(chǎn)物也是這樣。 我把這叫作拜物教。 勞動(dòng)產(chǎn)品一旦作為商品來(lái)生產(chǎn), 就帶上拜物教性質(zhì), 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chǎn)分不開(kāi)的。”?可見(jiàn), 作為“ 虛幻形式” 的商品與意識(shí)形態(tài)中的“ 虛幻” 的觀念一樣, 是光在視覺(jué)神經(jīng)中留下的印象, 所不同的是,商品的虛幻性具有客觀屬性, 光投在勞動(dòng)產(chǎn)品上; 而意識(shí)形態(tài)的虛幻性則是主觀投射的, 如同原始宗教中的物質(zhì)偶像也是一種主觀投射。 于是, “ 意識(shí)形態(tài)和商品, 暗箱的‘ 幻想形式’ 和拜物教的‘ 客觀屬性’ 并不是可分離的抽象形象, 而是同一個(gè)辯證過(guò)程中相互維護(hù)的兩個(gè)方面” (第243頁(yè))。
在米歇爾看來(lái), 由于拜物教或物戀具有濃重的偶像崇拜性質(zhì), 不僅把物質(zhì)生產(chǎn)轉(zhuǎn)換成人的幻覺(jué), 而且把活的意識(shí)變成死的、 把無(wú)生命的物質(zhì)變成有生命的崇拜物, 在人們之間生產(chǎn)一種物質(zhì)關(guān)系, 在物之間生產(chǎn)一種社會(huì)關(guān)系, 因此是一種邪惡的交換(第244頁(yè)) 。 這最典型地體現(xiàn)在貨幣這個(gè)價(jià)值符號(hào)上。 馬克思正確地看到, 貨幣并不是交換價(jià)值的想象符號(hào), 而是商品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的價(jià)值, “ 因此, 雖然貨幣運(yùn)動(dòng)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現(xiàn), 但看起來(lái)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貨幣運(yùn)動(dòng)的結(jié)果”?。 隨著貨幣在商品交換的領(lǐng)域里無(wú)休止地流通, 它已經(jīng)取代了它自身作為價(jià)值符號(hào)的一些功能, 成為物戀, 成為物自身。 貨幣由符號(hào)變成了物。 它具有超自然的魔幻力量, 以平凡的社會(huì)生活、 自明的交換形式和純粹的量化關(guān)系遮蔽了自身最深的魔力( 乃至罪惡) , 使商品以及貨幣自身成為了一個(gè)永恒的語(yǔ)碼。 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里, 貨幣和金錢(qián)具有為自身增加價(jià)值的屬性, 無(wú)休止地、 貪婪地生產(chǎn)“ 金蛋”, 令貨幣繁殖貨幣, 甚至連資本家自己也成為“ 人格化了的資本”, 成為剩余價(jià)值的意識(shí)表征( 第250頁(yè)) , 就好像當(dāng)下一些人按“ 身價(jià)”來(lái)論社會(huì)地位的高低, 用“ 量” 來(lái)衡量學(xué)問(wèn)的大小, 或用頭銜的多寡來(lái)判斷人的才能一樣。
馬克思在討論商品拜物教時(shí)提到了象形文字和語(yǔ)言, 并將其置于宗教的偶像崇拜和偶像破壞的語(yǔ)境之中。 在米歇爾看來(lái), 這種討論或許意在說(shuō)明, 商品拜物教也是進(jìn)行偶像破壞的一種偶像崇拜, 其悖論在于, 不同的偶像崇拜中存在著一種相似性, 不同的偶像破壞之間也存在著一種相似性。 偶像崇拜者總是幼稚的、 受騙的、 可憐的,因?yàn)樗偸翘摷僮诮痰臓奚罚?偶像破壞者總是進(jìn)步的、 發(fā)達(dá)的、 建構(gòu)的, 總是與偶像崇拜保持著歷史的距離。 然而荒謬之處在于, 偶像破壞者在打破了舊的偶像的同時(shí)也確立了新的偶像, 因此與偶像崇拜者一樣犯了道德錯(cuò)誤: 他們忘記或拋棄了人性,把人性投射到新的偶像上去了, 如新教與羅馬天主教的分裂, 或費(fèi)爾巴哈所說(shuō)的希伯來(lái)人從對(duì)偶像的崇拜到對(duì)上帝的崇拜, 或拜金主義對(duì)任何宗教信仰的取代。 頗為有趣的是, 米歇爾認(rèn)為馬克思為這種“ 偶像破壞的偶像崇拜” 找到了“ 一個(gè)合適的象征”,即拉奧孔( 第257頁(yè))?。 馬克思( 抑或米歇爾) 把拉奧孔比作新教徒, 把蛇比作財(cái)神或商品, 拉奧孔實(shí)際上并未努力抗?fàn)幰詳[脫正在使他窒息的蛇, 這是因?yàn)樗绨萆撸直簧邠肀В?因而將其當(dāng)作偶像來(lái)崇拜, 結(jié)果拉奧孔成了一個(gè)偶像崇拜者, 而他自己也將( 在萊辛的幫助下) 成為一個(gè)偶像, 因此也最終必然經(jīng)由偶像破壞而被新的偶像所取代。 由是觀之, 現(xiàn)代政治經(jīng)濟(jì)中的全部交流工具和視覺(jué)藝術(shù)中的“ 形象制造”, 包括電視、 電影、 廣告中的名人崇拜、 媒體崇拜或符號(hào)拜物教, 也把“ 藝術(shù)” 變成了資本主義美學(xué)的物戀, 使其具有了散發(fā)著濃濁銅臭味的“ 光暈”, 誠(chéng)如波德里亞所說(shuō), 甚至博物館也成了銀行, 媒體也成了非交流的建構(gòu)者( 第262頁(yè)) 。 這意味著, 非但物沒(méi)有被從光暈中解放出來(lái), 就連精神也仍然被物質(zhì)的光暈所籠罩著。
結(jié) 語(yǔ)
潘諾夫斯基認(rèn)為, 被當(dāng)作從屬性或約定俗成的含義之載體的母題也是形象, 把這種不同的母題綜合起來(lái)就是作品, 就是創(chuàng)作, “ 我們習(xí)慣上把它們稱(chēng)作故事和寓言”?。什么是母題? “ 由被當(dāng)作基本或自然含義的載體的純形式構(gòu)成的世界”?就是母題, 母題即由形象、 故事和寓言顯示出的主題或由概念構(gòu)成的世界, 它們具有基本的自然的含義, 但卻不是基本的自然的題材。 比如, 看到一群人按一定方式排列、 以一定姿勢(shì)坐在餐桌前, 這就是再現(xiàn)《 最后的晚餐》 的母題。 《 圣經(jīng)》 中耶穌與十二門(mén)徒的最后一次晚餐是題材, 達(dá)·芬奇《 最后的晚餐》 則是對(duì)這個(gè)題材、 故事、 母題的再現(xiàn), 它前無(wú)古人的創(chuàng)造性就體現(xiàn)在把圣經(jīng)故事中的“ 圣餐設(shè)立” 和“ 宣告背叛” ( 概念) 結(jié)合起來(lái), 體現(xiàn)了門(mén)徒們“ 無(wú)聲的喧嘩” 與耶穌“ 最強(qiáng)的和聲” 之間的鮮明對(duì)比, 歌德稱(chēng)之為“ 精神的有機(jī)體”, 貢布里希稱(chēng)之為“ 啞劇”, 沃爾夫林盛贊其形式與內(nèi)容的有機(jī)統(tǒng)一。 然而, 對(duì)其歷史性含義卻要基于基督教的基本態(tài)度或原則來(lái)理解。 當(dāng)我們把這幅畫(huà)看作被再現(xiàn)的“ 最后的晚餐” 時(shí), 就仍然在與故事本身打交道, 從而將其構(gòu)圖和肖像畫(huà)特點(diǎn)當(dāng)作作品本身的特點(diǎn); 而當(dāng)我們把這幅畫(huà)看作達(dá)·芬奇畫(huà)風(fēng)轉(zhuǎn)變的表現(xiàn)或意大利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文明或宗教態(tài)度的文獻(xiàn)時(shí), 它就具有了符號(hào)價(jià)值, 所表現(xiàn)的就是“ 某種別的東西”?。 對(duì)同一幅畫(huà)的兩個(gè)不同層面的解釋?zhuān)?構(gòu)成了肖像學(xué)(iconography)與圣像學(xué)(iconology) 之間的區(qū)別: 前者指畫(huà)法、 寫(xiě)法以及描述性的內(nèi)涵; 后者指思想、 理念以及解釋性的內(nèi)涵。 “ 圣像學(xué)就是一種帶有解釋性質(zhì)的肖像學(xué)”, 而“ 對(duì)形象、 故事和寓言的正確分析也是對(duì)它進(jìn)行正確的圣像學(xué)解釋的前提”?。 當(dāng)圣像的從屬性題材全部消失, 內(nèi)容直接過(guò)渡到風(fēng)景、 靜物或風(fēng)俗時(shí), 或當(dāng)1200年左右“ 維羅尼卡面紗” 也即耶穌的“ 真實(shí)圖像” 被發(fā)現(xiàn), 之后據(jù)說(shuō)是根據(jù)真實(shí)的、 以生活為原型的耶穌的正面圖像不斷被復(fù)制時(shí), 圣像便進(jìn)入了肖像畫(huà)時(shí)代。 此后至今, 我們所面對(duì)的就只有作為圖像的形象, 或作為形象的圖像了。 于是, “ 圣像學(xué)” 也就變成了包含“ 肖像學(xué)” 在內(nèi)的“ 圖像學(xué)”, 這一“ 轉(zhuǎn)向” 的意義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時(shí)代都更加重大。
①②③④ W. J. T. 米歇爾: 《 圖像何求? 形象的生命與愛(ài)》 , 陳永國(guó)、 高焓譯,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第xii頁(yè), 第xii頁(yè), 第xii—xiii頁(yè), 第xi頁(yè)。
⑤ 雅克·朗西埃: 《 沉默的言語(yǔ): 論文學(xué)的矛盾》 , 臧小佳譯, 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 第7頁(yè)。
⑥⑦⑨?? 萊辛: 《 拉奧孔》 , 朱光潛譯, 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3年版, 第2頁(yè), 第3頁(yè), 第17頁(yè), 第150頁(yè), 第100頁(yè)。
⑧ 朱光潛: 《 詩(shī)論》 , 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2年版, 第181頁(yè)。
⑩? 翁貝托·艾柯: 《 丑的歷史》 , 彭淮棟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 第271頁(yè), 第276—279頁(yè)。
? 萊辛: 《 拉奧孔》 , 第90頁(yè)。 參見(jiàn)W. J. T. 米歇爾: 《 圖像學(xué): 形象, 文本, 意識(shí)形態(tài)》 , 陳永國(guó)譯,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 第126頁(yè)。
? 此處為了論述的方便, 依米歇爾提供的英譯文譯出。 可參考王曉朝的譯文: “ 用與事物相似的東西來(lái)表現(xiàn)事物比隨意的指稱(chēng)要強(qiáng)得多。” ( 柏拉圖: 《 克拉底魯篇》 , 《 柏拉圖全集》 第2卷, 王曉朝譯,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125頁(yè))
? 馬克思: 《 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 ,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25頁(yè)。
???? 馬克思: 《 資本論》 ,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88頁(yè), 第89頁(yè), 第90頁(yè), 第138頁(yè)。
? 實(shí)際上, 馬克思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只有一次提到《 拉奧孔》 , 即1837年11月10—11日給父親亨利希·馬克思的信中: “ 這時(shí)我養(yǎng)成了對(duì)我讀過(guò)的一切書(shū)作摘錄的習(xí)慣, 例如, 摘錄萊辛的《 拉奧孔》 、 佐爾格的《 埃爾溫》 、 溫克爾曼的《 藝術(shù)史》 、 盧登的《 德國(guó)史》 , 并順便記下自己的感想。”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 人們出版社2004年版, 第11頁(yè)) 。
???? E. 潘諾夫斯基: 《 視覺(jué)藝術(shù)的含義》 , 傅志強(qiáng)譯, 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5頁(yè), 第34頁(yè), 第37頁(yè), 第39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