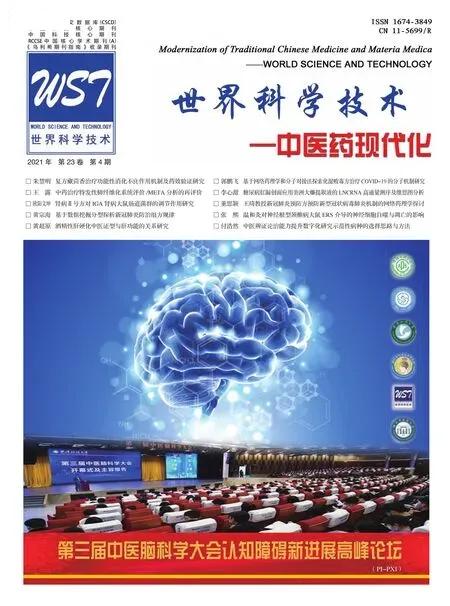基于文獻挖掘探討原發性肝癌用藥規律*
郭垠梅,吳泳蓉,張 振,鄺高艷,寧迪敏,田 莎,田雪飛**
(1.湖南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學院 長沙 410208;2.湖南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長沙 410006)
原發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以下簡稱肝癌)是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根據國家癌癥中心[1]2018年全球最新的癌癥報告,肝癌發病率在惡性腫瘤中占第6位,死亡率占第3位。目前西醫治療[2,3]肝癌主要有肝移植、肝切除術、放射治療、肝動脈化療栓塞、分子靶向、射頻及生物治療等,但西醫治療手段有一定局限性和毒副作用,影響患者的治療效果,患者生存預后較差,5年生存率低于5%[4]。肝癌[5]起病比較隱匿,病情進展迅猛,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如何利用中醫藥的優勢,提高肝癌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延長生命是目前肝癌治療領域的熱點與難點。大量的研究表明中醫藥在肝癌治療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它能夠抑制腫瘤進展,減輕手術并發癥,改善機體的免疫功能[6],進而改善患者的癥狀、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延長患者生存期[7-9]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更多的患者能夠長期與癌癥一起生存。中醫藥治療肝癌具有多途徑、多靶點等整體治療優勢,由于病因病機及臨床表現比較復雜,臨床組方遣藥時不能很好把握中藥間的配伍關系,故通過現代信息技術挖掘和分析中醫藥辨證治療肝癌有效方藥及用藥規律,可為臨床提供用藥配伍依據,具有重要意義。
中醫藥治療肝癌經驗是傳承中醫的重要載體,故本文基于數據挖掘和分析中醫藥治療肝癌經驗文獻,分析其用藥特點與組方配伍規律,探討中醫藥辨治肝癌的經驗,進一步反證肝癌的病因病機及理法治則,為中醫的傳承和臨床合理用藥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以“原發性肝癌”“肝癌”“中醫藥”為關鍵詞,檢索中國知網自建庫至2020年7月所收錄文獻,納入中醫藥治療肝癌經驗文獻,排除治療措施為中藥復方用于動物實驗、針灸或為針劑、丸散等非湯劑復方的文獻。搜集、整理其中的方劑。
1.2 數據篩選與整理
對上述納入文獻方劑進行篩選,若復方組成相同則只錄入1次。由2名研究人員核對篩選并進行審核,確保數據納入的準確性,若文獻納排存在爭議,由第3名研究人員進行篩選,閱讀并重新篩選可能符合納入標準的文獻,從而提高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此次篩選共納入明確治療肝癌復方113首。
1.3 數據處理與分析
將文獻檢索所得113個中藥復方錄入EXCEL2019,建立肝癌文獻數據庫,參照2015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0]規范統一中藥名稱,如“醋柴胡”規范為“柴胡”“炙甘草”規范為“甘草”,并對其進行性味歸經、分類等。統計各個中藥在性味歸經、分類的詞頻,并將詞頻從高到低進行排序。通過SPSSClementine 12.0.3軟件進行Apriori數據挖掘,觀察各中藥之間的配伍關系,設置支持度>20%、置信度>80%對中藥配伍進行二階、三階過濾分析,探索內在處方規律。
2 結果
2.1 藥物使用頻次分析
經過文獻檢索及篩選,最終納入文獻101篇,共篩選出113個中藥復方,涉及272味中藥,藥物總頻次2084次。使用頻次大于30次由多到少排列依次為白術、茯苓、柴胡、白花蛇舌草、黃芪、甘草、白芍、鱉甲、薏苡仁、雞內金、半枝蓮、莪術、八月札、黨參、麥芽、山楂、郁金、當歸(表1)。

表1 使用頻次≥30次藥物統計
2.2 藥物性味歸經頻次分析
將納入中藥四氣、五味、歸經數據進行頻次分析,使用藥物在四氣中所占比重由大到小依次為寒(880次)、溫(605次)、平(509次)、涼(66次)、熱(10次)(圖1)。使用藥物在五味中所占比重由大到小依次為甘(1104次)、苦(1008次)、辛(650次)、淡(211次)、酸(181次)、咸(176次)、澀(62次)(圖2)。藥物使用歸經頻次由多到少依次為脾(1093)>肝(1047次)>胃(828次)>肺(655次)>心(522次)>腎(472次)>膽(251次)>大腸(223次)>小腸(190次)>膀胱(152次)>三焦(29次)>心包(19次)(圖3)。

圖1 使用中藥在四氣中所占統計比

圖2 使用中藥在五味中所占統計比

圖3 使用中藥在歸經的分布
2.3 藥物功效分類頻次分析
將納入中藥按作用分類可分為18類,其中出現最多頻次為補虛藥,頻次為545次,占比27%,其次為清熱藥、活血化瘀藥、利水滲濕藥、消食藥、理氣藥等(表2)。

表2 使用藥物分類頻次統計
2.4 藥物關聯度分析
通過SPSSClementine 12.0.3軟件進行藥物關聯度分析,采用Apriori算法觀察各中藥間配伍關系,設置支持度>20%、置信度>80%、最大前項數為3對中藥配伍進行藥物關聯分析,共獲得29條中藥組合關聯規則,將所得結果按關聯規則進行排序,居前五(藥物不重復)依次為茯苓+黃芪+白術,茯苓+甘草+白術,茯苓+白花蛇舌草+白術,白術+柴胡+茯苓,白術+薏苡仁+茯苓(表3)。核心藥物網絡圖見圖4。

表3 使用藥物關聯規則分析結果

圖4 核心藥物網絡圖
3 討論
中醫并無“肝癌”病名,根據其病因和臨床癥狀,肝癌在中醫里面屬于“肝積”“癥瘕”“積聚”“脅痛”“黃疸”等范疇[11]。《靈樞·邪氣臟腑病形》有云:“肝脈微急為肥氣,在脅下,若覆杯”;《醫宗必讀·積聚》曾有記錄“積之成者,正氣不足,而后邪氣踞之”;《金匱要略》載有“黃家所得,從濕得之”。
3.1 肝癌的病機以脾虛為主,兼以濕、熱、痰、瘀
本研究結果提示,在藥物歸經使用中頻次最高的是脾經、肝經,由此可以看出名醫以肝脾辨證治療肝癌的規律。肝癌的外因為感受毒邪、肝氣郁滯、飲食所傷,內因為臟腑功能失調、正氣虧虛[12]。《醫學入門》中提出“五積六聚皆屬于脾”。肝癌[12]的本質為脾虛,水液停留、濕熱、瘀血為其標。脾虛生痰,痰濕內蘊,日久化熱,出現濕熱;同時,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氣為血之帥,脾虛則血行無力出現氣虛血瘀,故脾氣虧虛易生痰生濕生瘀生熱,濕、熱、痰、瘀互結日久,化為癌毒,結于脅下,蘊于肝臟發為肝癌。肝與脾同居于中焦,解剖位置決定了它們生理上關系密切,病理上相互影響。脾為中焦陰土,喜燥惡濕,主運化,主升清。肝屬剛臟,喜條達,惡抑郁,主疏泄,主藏血[13]。脾主運化水谷,為氣血生化之源,濡養全身臟腑,肝得脾之濡養才得以發揮肝主疏泄,脾得肝之疏泄才能正常運行[14-16]。肝癌患者往往肝氣郁結,久而克脾,脾失健運,肝失疏泄,肝木乘脾,橫犯脾胃,阻礙氣機,繼而出現噯氣痞悶、嘔逆納少、腹脹等癥狀。脾虛不能運化水濕,致水濕內停,郁而化熱,蘊蒸肝膽,以致膽汁外溢,形成黃疸,出現腹水。肝失疏泄,致膽汁分泌異常,繼而導致脾胃的消化吸收障礙,出現口干、口苦、脅痛、納食不化、黃疸、甚或惡病質等的癥狀[17]。所謂“養正積自除”,遵循“治肝先實脾,脾健肝自愈”的原則,《金匱要略》中指出“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中醫治療肝癌重視脾胃貫穿在整個治療過程中,針對不同時期的肝癌患者,早期以祛邪為主,兼顧正氣;中期患者攻補兼施;晚期患者以扶正為主,輔以祛邪[18]。?
3.2 肝癌治療以扶正健脾為主,兼以疏肝、清熱、化瘀軟堅散結
從藥物使用頻次來看健脾益氣類中藥白術、茯苓、黃芪、甘草、薏苡仁、雞內金、黨參、麥芽、山楂、神曲等藥物在臨床使用頻率比較高。按藥物功效分類,使用最多頻次為補虛藥。藥物關聯規則結果常以白術、茯苓、黃芪、薏苡仁、黨參等相配伍為核心。在藥物的五味方面以甘味為主,其次是苦、辛,甘能補、能和、緩解止痛,具有補益作用。《醫學心悟》中云“虛人患積者,必先補其虛,理其脾……然后用藥攻其積,斯為善治”。四君子湯[19]為傳統中醫健脾益氣的代表方,由人參、白術、茯苓、甘草組成,方中人參自清代以來多用黨參代替。薏苡仁、白術、茯苓、黃芪相配伍,為健脾化濕利水常用組合。雞內金、麥芽、山楂、神曲為健脾消食、行氣開胃常用配伍。可以看得出各醫家治療肝癌以“脾虛”為核心,以扶正健脾為治療本病的基礎,通過中藥歸經分析,肝癌治療與脾、肝二經關系密切,故臨床治療選取中藥多從脾、肝二經入手,從而達到健脾胃、滋肝陰作用。現代藥理學研究顯示,李明襄等[19]發現四君子湯中的黨參、茯苓、白術、甘草四味中藥的活性成分都有抗肝癌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調整肝癌細胞不同蛋白的表達活性、抑制肝癌細胞增殖、轉移、及誘導肝癌細胞凋亡。徐放等[20]提出黃芪中的提取物黃芪多糖能抑制SMMC-7721細胞侵襲和轉移,有良好的抗腫瘤活性。孫燕等[21]發現薏苡仁油在抑制腫瘤細胞增殖、遷移、腫瘤血管形成、誘導腫瘤細胞凋亡方面有良好的抗肝癌活性。孫思明等[22]發現山楂中酚類化合物可以通過抗氧活化酶活力和細胞凋亡蛋白來抑制SMMC-7721細胞增殖,促進細胞凋亡。這些基礎研究為從脾胃論治肝癌提供了依據。
在此基礎上,根據不同的臨床癥狀進行辨證治療。肝癌患者常常肝氣郁結,情緒易激易怒,根據藥物使用頻次,發現疏肝理氣類中藥使用比較多,柴胡、郁金、川楝子、青皮、陳皮配伍疏肝解郁行氣,肝氣條達,氣機升降正常,氣行則血行瘀化,與此同時應該重視對肝癌患者的心理疏導[23,24]。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張弛等[25]發現白芍、柴胡通過代謝通路、Ras信號通路、PI3K-Akt信號通路調控肝癌細胞過程及其代謝發揮抗腫瘤作用。黨寧等[26]發現郁金中的二萜類化合物C可通過上調Caspase-3和PARP的表達來誘導人肝癌HepG-2細胞發生凋亡而起到肝癌作用。
在藥物的四氣方面,肝癌所用的藥物以苦寒為主。按藥物功效分類,清熱藥物占比也比較大,比如白花蛇舌草、半枝蓮、半邊蓮、重樓、八月札、山慈菇等,肝癌中期患者多見化熱之象,寒能清熱涼血解毒。苦能燥濕泄熱,辛能行氣血。白花蛇舌草、半枝蓮、八月札是常用的清熱解毒抗癌殺毒藥對。同時發現在藥物使用頻次較高的中藥比如柴胡、八月札、鱉甲、土鱉、莪術、三棱等都屬于歸肝經的中藥,提示應該重視引經藥。肝癌晚期患者,氣血耗傷,肝腎陰虛,腎水不能滋肝木,肝陰虛進一步加重,患者常常出現脅肋部疼痛、腰膝酸軟、低熱、盜汗、失眠多夢等癥狀,多選用炙龜甲、炙鱉甲、女貞子、生地等藥物配伍清虛熱、滋陰潛陽,軟堅散結[27]。研究表明,白花蛇舌草[28,29]、半枝蓮[30,31]、八月札[32,33],這些植物抗癌中藥具有良好的抗腫瘤作用。孫陽等[34]發現鱉甲煎丸可能通過下調Bcl-2,上調Bax基因表達,并抑制IL-6/Stat信號通路,發揮其抗腫瘤作用。
肝癌患者臨床可見各種血瘀癥狀,比如腫塊、肌膚甲錯、瘀斑、面色黧黑、舌下脈絡曲張、舌質紫暗、脈結代等,需要辨證運用活血蟲類藥物和植物藥,一般早期臨床應用效果較好,晚期要慎用破血逐瘀之品。從藥物頻次統計可知,土鱉蟲、三棱、莪術、穿山甲、蟄蟲、延胡索、蜈蚣、干蟾皮等藥物使用頻次較高。毒蟲類藥物的應用不僅可以活血通絡,以毒攻毒,還可以引藥入肝經,直達病所,加強藥效。現代藥理研究證實土鱉蟲[35,36]、蜈蚣[37,38]、干蟾皮[39,40]在抑制肝癌細胞增殖及轉移、誘導肝癌細胞凋亡、抑制腫瘤新生血管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抗腫瘤作用。
綜上,原發性肝癌雖然證型復雜,兼癥雜多,但其臨床治療仍有規律可循,臨床辨證以脾虛為主,兼水液停留、濕熱、血瘀等癥狀。治法以扶正健脾為主,同時兼以疏肝、清熱、化瘀軟堅散結。本研究通過對運用中醫藥治療肝癌的病案進行數據挖掘,篩選113個中藥復方作為研究內容,在一定程度程度上可以反映各醫家治療肝癌的用藥規律,對中醫藥治療肝癌的用藥規律進行探究及分析,為臨床辨證治療肝癌有效方藥及用藥規律可提供用藥配伍依據,但由于本研究僅檢索中國知網自建庫至2020年7月所收錄文獻進行數據分析,得出的結果有局限性,故需以后納入更多診斷明確的醫案,以使結果對臨床的指導意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