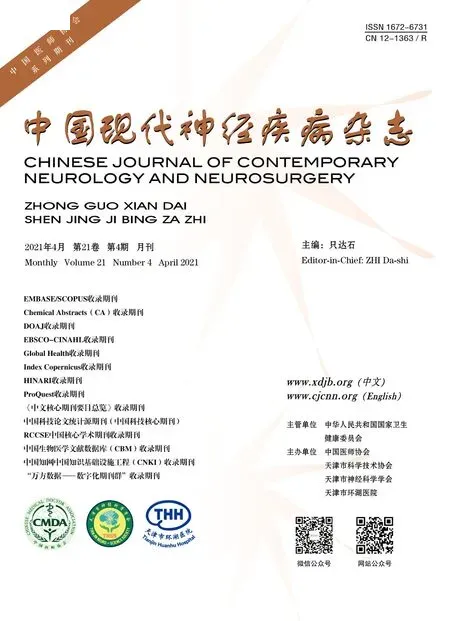人腦組織庫建設對阿爾茨海默病研究的意義
杜鵑 楊倩 米世雄 樊平 崔慧先 黃越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神經退行性病變越來越嚴重影響人類健康,給家庭和社會造成巨大精神和經濟負擔。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啟動“腦計劃”以揭示大腦奧秘。我國科學家經過多年醞釀,依據科技創新2030——“腦科學與類腦研究”提出研究方向,圍繞腦認知原理解析、認知功能障礙相關重大腦疾病發病機制與干預技術研究、類腦計算與腦機智能技術及應用、兒童青少年腦智發育研究、技術平臺建設共五方面部署。其中,針對阿爾茨海默病的研究,以人群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標志物異常表征、新型發病機制、危險因素綜合干預、認知功能訓練平臺、新型藥物等,從而揭示參與阿爾茨海默病發生與發展的新機制。然而,對人腦本質性的認識往往依賴以人腦組織為材料進行的直接研究,但受限于倫理學,研究者難以通過外科手術獲得正常腦組織樣本,更難以獲得完整腦組織。因此,建設人腦組織庫(以下簡稱腦庫),收集尸檢和活檢的人腦組織、采集捐獻者生前疾病信息,從而為科學工作搭建平臺,以直接研究疾病本體的模式揭示腦疾病的本質[1]。文獻綜述有助于揭示某一特定領域的研究發展歷史和未來研究之趨勢[2],本文重點回顧既往3年Cell、Nature和Science等國際頂級期刊發表的人腦組織與阿爾茨海默病及相關疾病研究成果(表1),旨在綜述人腦組織在阿爾茨海默病研究中的應用,以作為我國相關研究的借鑒。

表1 2018-2020年發表的人腦組織在阿爾茨海默病及相關疾病研究成果Table 1. Research on the use of human brain tissu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iseases published during 2018-2020
一、研究關注點
檢索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PubMed)2018-2020年文題和(或)摘要同時出現阿爾茨海默病及其他關鍵詞的文獻共48 305篇,發現β-淀粉樣蛋白(Aβ)、tau蛋白和病理仍為目前阿爾茨海默病研究的主題,分別為6955、5426和5006篇,各占文獻總量的14.40%、11.23%和10.36%(圖1)。

圖1 2018-2020年PubMed中阿爾茨海默病研究所出現的關鍵詞Figure 1 Keywords appeared in the research of Alzheimer's disease through searching PubMed limited from 2018 to 2020.
二、人腦組織研究取得的突破性進展
1.蛋白質分子生物學結構研究 202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梅奧診所(Mayo Clinic)聯合在Cell發表研究成果,研究者從來自梅奧診所腦庫的2例皮質基底節變性(CBD)和1例阿爾茨海默病的人腦組織中提取tau蛋白并行冷凍電子顯微鏡檢查,通過比較二者tau蛋白纖維結構和翻譯后修飾,發現tau蛋白泛素化可以修飾tau蛋白纖維之間的界面,進而提出基于結構的模型分析,建立多態tau蛋白纖維結構與神經退行性病變之間的框架[3]。同年,英國劍橋大學MRC分子生物實驗室對來自其腦庫的3例皮質基底節變性的人腦組織進行研究,發現其存在4R tau蛋白纖維結構[4];該實驗室還對來自劍橋大學腦庫的5例多系統萎縮(MSA)和3例路易體癡呆(DLB)的人腦組織提取共核蛋白并分析其結構,發現α-突觸核蛋白(α-Syn)包涵體由兩種類型纖維組成,每種纖維亦由兩種原纖維組成,即每種纖維中非蛋白分子均存在于兩種原纖維界面上,且多系統萎縮與路易體癡呆人腦組織α-Syn蛋白絲不同[5],這兩項研究成果均發表于Nature。可見蛋白質功能由其結構決定,因此,蛋白質分子生物學結構對藥物設計與研發以及疾病治療具有重要意義。
2.單細胞轉錄組學研究 美國Rush大學醫學中心Rush腦庫接受捐獻的標準是捐獻者須有生前標準化臨床隨訪資料,且這些臨床資料的采集是以臨床研究項目開展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腦與認知科學系基于信仰與Rush記憶和衰老研究(Religious Orders Study and Rush Memory and Aging Project)[6-7]對Rush腦庫的人腦組織進行阿爾茨海默病單細胞轉錄組學研究,取材24例阿爾茨海默病和24例正常對照人腦組織的前額葉皮質,分析6種神經細胞類型,即興奮性神經元、抑制性神經元、星形膠質細胞、少突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少突膠質前體細胞,共獲得80 660個單細胞轉錄組,包括與病理和特征有關的髓鞘形成、炎癥反應和神經元存活的調節因子,從而認為髓鞘形成參與阿爾茨海默病的發生[8]。
3.炎癥反應與tau蛋白病理發生機制研究 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蛋白3(NLRP3)炎性小體激活可導致tau蛋白病理改變[9]。德國Bonn大學醫院對來自Barcelona臨床醫院生物樣本庫的9例額顳葉癡呆(FTD)和8例正常對照的人腦組織進行驗證,結合轉基因動物模型發現,NLRP3炎性小體激活時聚集于小膠質細胞內,促使Caspase-1和下游白細胞介素-1β(IL-1β)釋放;通過調節tau蛋白激酶和磷酸酯酶以減少tau蛋白高度磷酸化和聚集,從而減弱NLRP3炎性小體功能;腦組織內注射Aβ可NLRP3依賴方式誘導病理性tau蛋白纖維形成[9]。
4.β-淀粉樣蛋白寡聚體通過血管周細胞收縮毛細血管研究 Aβ寡聚體可以通過血管周細胞收縮阿爾茨海默病人腦組織的毛細血管[10]。阿爾茨海默病早期腦血流量減少,因腦組織中的絕大多數血管阻力存在于毛細血管,表現為毛細血管壁可收縮周細胞功能障礙,因此有研究者驗證是否存在Aβ通過周細胞收縮毛細血管的現象。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和Queen Square國家神經內外科醫院對13例腫瘤手術切除的大腦皮質行免疫組化染色,結果顯示,6例無Aβ沉積,3例Aβ適度沉積,4例Aβ大量沉積,隨著Aβ沉積的加重,毛細血管管徑逐漸變小。腦組織毛細血管周細胞上的Aβ壓縮腦血管,這是由Aβ產生活性氧引起內皮素-1(ET-1)的釋放、激活周細胞ETA受體所致[10]。該研究結論在嚙齒動物模型中得到驗證,阿爾茨海默病小鼠模型腦組織中亦發生毛細血管收縮而非小動脈收縮[10]。因此,抑制Aβ引起的毛細血管收縮可能減少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能量缺乏、改善神經退行性變。
5.β-淀粉樣蛋白依賴性神經元高度激活的惡性循環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研究所用阿爾茨海默病人腦組織來自美國麻省總醫院麻省ADRC神經病理核心實驗室,取材1例67歲男性阿爾茨海默病患者(Braak分期Ⅵ期)腦組織用于制備水溶性提取物,取材1例69歲女性阿爾茨海默病患者(Braak分期Ⅴ期)的大腦皮質用于分離淀粉樣斑塊,結合Aβ沉積小鼠模型發現,神經元高活化是由于抑制谷氨酸再攝取引起的,Aβ介導的神經元激活具有明顯的神經元特異性;進一步對存在阿爾茨海默病病理改變的人腦組織進行Aβ二聚體提取和純化,同樣發現上述正反饋現象,并認為該現象是阿爾茨海默病神經炎性斑[NPs,亦稱老年斑(SPs)]形成的早期機制,表明阿爾茨海默病早期環路功能障礙系Aβ依賴性神經元高度激活所致[11]。
6.睡眠-覺醒周期對腦間質液tau蛋白的調節研究 睡眠-覺醒周期可以調節阿爾茨海默病人腦組織間質液和腦脊液中的累積Aβ水平[12],而慢性睡眠剝奪可促進Aβ斑塊形成,其中,tau蛋白的累積可以驅動阿爾茨海默病的神經退化。美國華盛頓大學納入8~16只小鼠(B6C3F1/J,P301S,B6C3-Tg,APP/PS-1)的腦組織以及6例認知功能正常者(30~60歲)的腦脊液,以探討睡眠-覺醒周期和睡眠剝奪是否影響腦間質液和腦脊液中tau蛋白表達、形成和擴散。結果顯示,小鼠腦間質液tau蛋白水平在正常覺醒期較睡眠期增加約90%、在睡眠剝奪期較睡眠期間增加100%,人腦脊液tau蛋白水平在睡眠剝奪期較睡眠期增加>50%;進一步觀察tau蛋白形成和擴散,發現慢性睡眠剝奪可促進小鼠腦間質液tau蛋白的病理性擴散,特別是小鼠的化學驅動覺醒可顯著升高腦間質液中Aβ和tau蛋白水平,表明睡眠-覺醒周期可以調節腦間質液tau蛋白的表達,睡眠剝奪可以增加腦間質液和腦脊液中tau蛋白的表達和病理性擴散[12]。
7.空間轉錄組和原位測序研究 比利時VIB腦疾病研究中心從荷蘭腦庫獲取3例阿爾茨海默病(平均年齡76歲)以及3例非癡呆對照(平均年齡為75歲)人腦組織額上回樣本,均為女性。他們在前期的動物實驗中采用空間轉錄組學觀察到,阿爾茨海默病小鼠模型Aβ斑塊周圍直徑100μm的結構域內發生轉錄變化,證實阿爾茨海默病早期改變與髓鞘和少突膠質細胞相關基因有關,而阿爾茨海默病后期改變則與補體系統、氧化應激、溶酶體和炎癥相關基因有關,并進一步采用原位測序方法在小鼠和人腦組織切片上得到確認[13]。由此可見,全基因組空間轉錄組學為闡明阿爾茨海默病及其他腦疾病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方法。
8.體細胞APP基因重組研究 人腦多樣性和復雜性被廣泛認為是編碼在1個恒定的基因組中,而體細胞基因重組通過改變種系DNA序列以增加分子多樣性,理論上可以改變這種編碼,但并未在人腦組織中證實。美國Sanford Burnham Prebys醫學研究所研究用新鮮人腦組織由美國圣地亞哥大學阿爾茨海默病研究中心、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神經損傷和障礙研究所和馬里蘭大學腦組織庫提供,包括7例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和7例正常對照人腦組織,該項研究發現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編碼β-淀粉樣前體蛋白(APP)的基因在神經元中以數千種變體“基因組c DNAs”的嵌合體形式存在[14]。DNA原位雜交鑒定出單個神經元中基因組cDNAs與野生型位點不同,而非神經元中不存在基因組cDNAs,神經元“反向插入”RNA產生基因組cDNAs,這一過程包括轉錄、DNA斷裂、逆轉錄酶活性和老化。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人腦組織神經元可見增加的基因組cDNAs多樣性,包括11種已知的與家族性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突變,而正常對照人腦組織神經元則不存在這些突變,表明神經元基因重組可能允許“記錄”神經活動,選擇性“回放”繞過剪接表達的首選基因變體,這對細胞多樣性、學習和記憶、可塑性以及腦疾病均有影響[14]。
9.大腦皮質環狀RNA表達圖譜顯示出臨床與病理的關聯性 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對來自其Knight阿爾茨海默病研究中心的83例阿爾茨海默病和13例正常對照人腦組織的頂葉皮質進行RNA測序,并參考西奈山腦庫(MSBB)中阿爾茨海默病RNA測序數據,定量測定阿爾茨海默病背景下頂葉皮質環狀RNA(circRNA)的表達變化,結果顯示,circRNA含量與阿爾茨海默病診斷、臨床癡呆嚴重程度和神經病理嚴重程度顯著相關,而大多數阿爾茨海默病相關circRNA與mRNA表達無關,亦與各類型神經細胞比例無關[15]。該項研究還觀察到,阿爾茨海默病相關circRNA與已知的阿爾茨海默病相關致病基因(APP、SNCA)共表達,并在阿爾茨海默病相關circRNA中識別出潛在的靶向致病微小RNA(mic RNA)結合位點。上述研究結果強調了分析非線性RNA的重要性,并可用于支持circRNA在阿爾茨海默病發病機制中潛在作用的研究[15]。
由此可見,通過總結2018-2020年阿爾茨海默病及相關疾病的重大研究成果,發現人腦組織在阿爾茨海默病及相關疾病的突破性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然人腦組織數量是腦庫建設的衡量指標之一,但并不完全取決于人腦組織的儲存數量,例如,Cell、Nature和Science等國際頂級期刊發表的相關研究中人腦組織數量均較少(表1),而是更主要取決于研究問題、研究技術和方法,以及各交叉學科技術的融合。
為適應神經科學和神經病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我國的腦庫逐步建立并完善。2017年,以基礎醫學院為核心,我國成立中國人腦組織庫協作聯盟,制訂《中國人腦組織庫標準化操作方案》[16-17];還成立中國解剖學會人腦庫研究分會。同年,國家科技部批準依托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和浙江大學醫學院成立國家發育和功能人腦組織資源庫、國家健康和疾病人腦組織資源庫。2018年,以臨床醫學院為核心,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籌建中心腦庫共同體[18]。河北醫科大學腦庫作為中國人腦組織庫協作聯盟單位和國家發育和功能人腦組織資源庫共建單位,積極參與并撰寫《人腦組織庫生物安全防護共識》(待發表)。通過各單位的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國科學家“無腦可用”的窘迫狀況[19]。基于這些樣本資源,國內研究者在中國人腦病理與生前認知功能相關性、衰老及阿爾茨海默病人腦組織Aβ斑塊蛋白質譜等方面開展相關研究[20]。同時,針對我國腦科學研究的逐步推進,腦庫作為其中的重要技術平臺,參與到阿爾茨海默病等認知功能障礙疾病的隊列研究中,共享樣本和數據,結合臨床診斷和尸檢病理,揭示阿爾茨海默病發生發展的新機制、篩查作用明確且可干預的危險因素、獲得早期精確診斷標志物和治療靶點,從而在神經系統疾病診斷、治療、預防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堅信我國腦庫的發展將更加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利益沖突 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