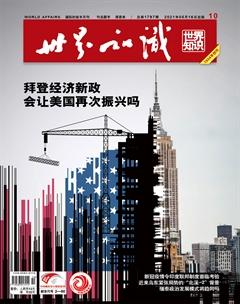中美在臺海空中博弈的是是非非
曹群
近年,美國大幅提升在中國沿海空域的軍機活動頻次和強度,在臺灣海峽亦多有消極動作,中方不得不做出回應。臺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美方罔顧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精神與民進黨當局勾連,不斷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破壞臺海和平穩定。在臺灣當局的有意引導和美西方一些智庫媒體的歪曲評析報道之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臺海及附近區域的正常空中演練被炒作為“軍事施壓”或“武力脅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的行動被解讀為“侵入臺灣防空識別區”,構成“引發臺海緊張”和“現狀改變”的“根本原因”。由于是非被嚴重混淆,我們有必要澄清謬誤、以正視聽。
所謂臺灣“防空識別區”
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臺海空域開展演訓活動天經地義。臺防務部門和島內綠媒利用普通民眾對相關專業領域缺乏了解,大肆炒作所謂解放軍軍機“侵入”臺灣“防空識別區”,企圖在島內營造“恐慌”氛圍以裹挾“民意”。
要看到,臺灣當局所劃“防識區”范圍從未得到各方承認,美日對其界線亦有異議。臺灣的“防識區”迄今仍維持其在1950年代的覆蓋范圍,為以下地理坐標點連線內的區域:北緯21度00分、東經117度30分,北緯21度00分、東經121度30分,北緯22度30分、東經123度00分,北緯29度00分、東經123度00分,北緯29度00分、東經117度30分,北緯21度00分、東經117度30分。
臺灣“防識區”不僅覆蓋中國臺灣省及其鄰近“國際空域”,還覆蓋中國浙江、江西、福建省的部分和廣東省的一小部分(比如南澎列島)空域,以及日本與那國島部分領空,但并未覆蓋中國釣魚島、東沙島及鄰近空域。按前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不同場合所述,臺灣“防識區”于1952年“公布”,1953年由臺當局與美國政府“共同協商制定”。之所以出現不同年份,若非口誤,可能是由于當時美臺之間關于臺灣“防識區”覆蓋范圍存在分歧,美國迄今仍僅承認“海峽中線以東范圍”。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防識區”不僅與中國東海防識區有所重疊,也與日本2010年擴展后的防識區范圍有小部分重疊。臺當局以事涉“主權及空域完整”為由表示“無法接受”日方“擴展界線”,迄今仍堅持美軍占領琉球期間所劃的縱貫與那國島上空的東經123度線為“臺日防識區分界”。
在國際慣例中,“防空識別程序”并不適用軍機,所謂“侵入”之說毫無法理依據。按臺當局相關“法規”,防識區“指經特別指定范圍之空域,于該空域內之航空器除應遵循飛航服務相關規定外,并應符合特殊識別及(或)報告程序”;“航空器進入或飛航于防空識別區時,應遵守防空識別規定”。具體的“臺灣防空識別程序”公布于“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指南”,主要包括如下“規定”:(1)“所有非作戰任務之航空器在公海上空飛航時,其高度不得低于4000呎并應沿規定之航路飛航,飛越各指定位置報告點時,應立即作位置報告,但經雷達引導者除外”;(2)“所有非作戰任務之航空器在進入臺北飛航情報區時,需與臺北區域管制中心或臺北通訊中心建立通訊”;(3)航空器不遵守防空識別程序或航管規則程序將被“攔截機攔截”,“被攔截之航空器如不服從攔截機所給之任何指示時,安全將無保障”,臺當局對“因不遵守航空識別程序或飛航管制規則程序而招致攔截機或其他武器之攻擊而受損傷”“不負任何責任”。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轟六”轟炸機。
可見,臺當局主張其“防空識別程序”的適用對象并不包括軍用航空器,各國軍機在臺灣防空識別區“國際空域”范圍皆享有“飛越自由”。俄羅斯、美國、日本等國軍機均曾在未事先通報的情況下進入臺灣“防識區”,臺當局不曾指責其違反“防空識別程序”,均較“冷靜”地按慣例進行查證識別或跟蹤伴飛,從未如針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一般進行大肆炒作和輿論渲染。
臺當局一向“崇美”,但并未像美國對待俄軍機進入美國防識區時那樣“冷靜”和“專業”。近十年來俄軍轟炸機多次飛入美國防識區演訓,甚至有意選在7月4日向實施“攔截”的美國戰機發出無線電“問候”:“我們在你們‘獨立日來這里向你們致意。”對此,北美防空司令部發言人表示,俄軍機完全有權在此活動,雙方相遇操作均很“專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相關演訓活動(包括“繞島巡航”)不僅進入所謂臺灣“防識區”,而且多在穿越臺灣“防識區”之后進入菲律賓防識區并靠近菲北部島礁空域,但菲方從未像臺當局那樣大驚小怪。
臺灣“防識區”與“臺北飛行情報區”(此處指的是國際民航組織認可的“臺北飛行情報區”范圍,而非臺當局單方面主張的“臺北飛航情報區”范圍)有較大面積重合,在“臺灣西南空域”也有不少民航航路經過,民航飛行接受相關空管單位“管制”自無問題,而且軍機一般會為“適當顧及”民航飛行安全盡量避免在民航航路附近活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相關演訓活動在飛行高度和范圍上充分顧及民航飛行安全,而美國軍機在本地區活動卻經常肆意妄行,甚至曾經多次冒用民航飛機電子代碼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臺獨”頑固分子一方面對于美國軍機擾亂有關空域航空秩序和安全的行為“視而不見”,一方面瘋狂炒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空中威脅”,借機為自己強化同外部勢力之間的勾連造勢,若一意孤行必將玩火自焚。
美方大搞“雙重標準”
隨著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美國頻打“臺灣牌”,妄圖借用臺灣這顆“棋子”遏制中國崛起,迫使中國在其他問題上妥協退讓。僅就近年來美有關臺海問題的政策轉變和在所謂臺灣“防識區”行動而言,其“雙重標準”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美方認為其有權在各種層面破壞兩岸關系現狀,為“臺獨”勢力撐腰打氣,但中國大陸不能“有所作為”。近年來,美國不斷提升美臺互動的官方層級,加大對臺軍售力度,通過多個涉臺法案,公然挑釁中國底線。中國外交部樂玉成副部長接受美聯社專訪時強調:“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和退讓的空間。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臺官方往來。美國不要打‘臺灣牌,這是一張危險的牌。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的紅線,我們絕不允許‘越線行為。”
第二,美方認為其軍用艦機在臺海活動系行使“航行和飛越自由”之權,而中國海空軍的“出海”行動屬“挑釁”“威脅”。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這條假想出來的“中線”很可能是緣于1950年代初美國為限制臺當局“反攻大陸”而劃設,當時中國海空軍實力較弱,而國民黨當局戰機多次在“海峽中線”以西大陸沿海地區執行偵察、空戰乃至轟炸任務。美國和臺當局似已忘記這段歷史,如今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在“海峽中線”以東空域演練視為“改變現狀”或“有害且無助區域穩定”之舉,與其歷史上的言行相對比是何等諷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臺灣西南空域”的演訓活動皆在“國際空域”進行,屬于美方主張軍機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享有的“國際合法用途”。美方似乎認為只有美國及其盟友艦機享有“航行和飛越自由”,可在鄰近中國領海、領空的“國際水、空域”進行抵近偵察等“和平的”軍事活動,而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美國至今尚未批準加入)締約國的中國,海空軍艦機一旦出海就構成“軍事威脅”,此種“雙重標準”立論是何等荒謬!

2020年12月31日, 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麥凱恩”號執行“印太巡航”任務并穿行臺灣海峽。
第三,美國對“臺灣防空識別程序”與其立場相異之處視而不見,僅挑戰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美方將中國劃設東海防識區指責為“過度海洋主張”,污蔑中國“違反國際規則”,并利用所謂“航行自由行動”(FONOP)持續“挑戰”東海防識區。在對“穿越”情況的適用問題上,臺灣“防識區”相關規則與東海防識區類似,但美國對此似乎毫不關注,也從未進行“挑戰”。美方似乎認為,其派遣軍機挑戰東海防識區屬于捍衛“國際規則”,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進入臺灣的“防識區”(當然也包括進入日本、韓國的防識區)就是“軍事威脅”,這同樣是“雙重標準”。
中美危機管控機制建設有待深化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近期答記者問指出,美國現政府就職以來,其軍艦在中國當面海域活動頻次比去年同期增加逾20%,偵察機活動頻次超40%,威脅地區和平穩定。為加強危機管控,降低由美方抵近偵察引發類似2001年“撞機事件”的風險,中美兩軍有必要進一步強化《中美關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附件三“空中相遇安全行為準則”中的共識,就雙方因國際法不同“解讀”所致不同立場的具體問題加強交流,積極推動探討便于實際操作、聚焦管控意外事件和避免摩擦的“細則”。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當中最核心的敏感問題。隨著中美兩國競爭的加劇和“臺獨”勢力危機感的提升,中美雙方在臺海空域的戰略博弈也會更趨激烈,緊張程度甚至會超過南海上空。鑒于臺海區域的高度敏感性和特殊性,中美有必要考慮設立較有針對性的“嚴格”規則,就雙方或多方軍機“對峙”情景下應如何避免摩擦之類的問題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