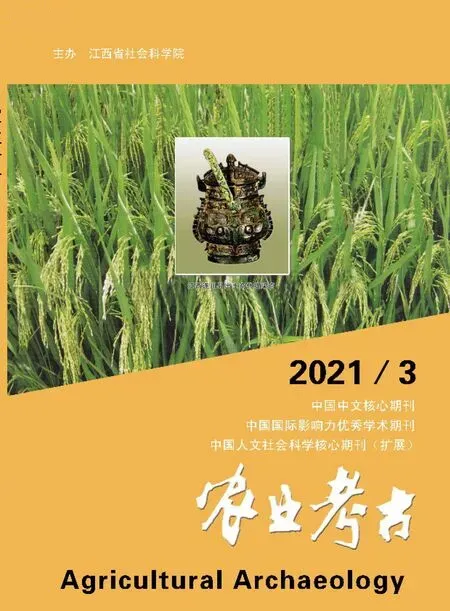清代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文化中心地角色的考察與剖析
——以獨流鎮(zhèn)、勝芳鎮(zhèn)和彭城鎮(zhèn)為中心
范貝貝
施堅雅在論述 “核心—邊緣”理論時提到:“在這一片土地上出現(xiàn)的新的中心地不僅是市鎮(zhèn),也就是說,不僅是經(jīng)濟中心地;別的種種“城市”職能,那些一度限于都邑的職能,也被移交給了他們。”[1](P26)這里所指的“城市”職能便是伴隨著市鎮(zhèn)工商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市鎮(zhèn)經(jīng)濟中心地功能輻射的不斷擴散而形成的,并以市鎮(zhèn)這一獨立的商業(yè)地理實體向廣大基層農(nóng)村開展的文化中心地角色與功能輻射。
有清一代,隨著海河干流及五大支流(大清河、子牙河、漳衛(wèi)南運河、北三河、永定河)構(gòu)建的水運網(wǎng)絡(luò)的形成和不斷完善,大量市鎮(zhèn)沿河流兩岸發(fā)育和聚集,成為華北地區(qū)市鎮(zhèn)發(fā)展的核心。獨流鎮(zhèn)居于大清河、南運河和子牙河三河交匯之地,為海河水系沿岸典型的交通樞紐型市鎮(zhèn)。勝芳鎮(zhèn)位于大清河北岸,在清初已經(jīng)是發(fā)展較為成熟的商品流通型市鎮(zhèn)。而彭城鎮(zhèn)則為海河水系沿岸較為典型的手工業(yè)專業(yè)市鎮(zhèn),鎮(zhèn)以制售磁器為業(yè)。三鎮(zhèn)雖同處于海河水系,但是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和市鎮(zhèn)經(jīng)濟發(fā)展方向與軌跡卻大相徑庭,是海河水系沿岸乃至華北地區(qū)不同經(jīng)濟類型市鎮(zhèn)發(fā)展的典型代表和縮影。通過對獨流、勝芳和彭城三鎮(zhèn)多元文化信仰空間的形成、廟會和花會的繁榮、文化教育機制、社會保障等多方面開展綜合分析和考察,可以清晰地把握海河水系沿岸不同類型市鎮(zhèn)文化中心地角色的建構(gòu)過程和輻射作用,提煉出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文化的普遍內(nèi)涵,有助于深入考察和理解清代華北地區(qū)市鎮(zhèn)文化與社會生活面貌。
一、多元文化信仰空間的形成
市鎮(zhèn)在其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帶動的人口的增加和聚集、短距離或長距離人口的流動,必然會帶動信仰、祭祀和崇拜的需求和遷移,這些多元的、流動的信仰和崇拜根植于市鎮(zhèn)的每個角落,凝聚在市鎮(zhèn)的街頭巷尾,構(gòu)成市鎮(zhèn)社會生活的重要篇章。
根據(jù)調(diào)查,清代獨流鎮(zhèn)的宗教信仰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以及民間宗教。佛教寺廟有文殊寺和大佛寺,祠廟、道教及民間信仰廟宇頗多。除了傳統(tǒng)的佛道寺廟和神廟,鎮(zhèn)內(nèi)的清真寺和李爺廟最具獨流特點。伊斯蘭教于嘉慶年間隨小批回族穆斯林移民傳入獨流鎮(zhèn),并在集聚區(qū)建立了清真寺。伊斯蘭教的廣泛傳播是清代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多元信仰融合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隨著海河水系構(gòu)建的水運網(wǎng)絡(luò)的盤活,大批回族穆斯林沿大運河或內(nèi)河經(jīng)商和遷徙,在河運交通發(fā)達、商業(yè)繁盛的城鎮(zhèn)定居,建造清真寺,圍寺而居,并且“以地域為中心,以伊斯蘭教、血緣、鄉(xiāng)誼為紐帶,以茶館、會館、公所、清真寺為其在異鄉(xiāng)的聯(lián)絡(luò)、計議之所,結(jié)成一種松散的、自發(fā)的商人群體”[2](P54)。
李爺廟建于光緒年間,由獨流鎮(zhèn)的富戶捐款修建,是獨流鎮(zhèn)唯一的地方神廟。廟內(nèi)僅供奉一位騎著白馬的陰陽臉少年塑像。據(jù)《獨流鎮(zhèn)志》記載:
“李爺”名為李正士,靜海縣西賈口村人,在其十三歲時騎一匹白馬赴獨流鎮(zhèn)上學(xué)的路上,被一只野兔驚了馬,從馬上墜亡,死于獨流鎮(zhèn)第三埠。李正士死后由于臉部血肉模糊,變成了一幅陰陽臉來到酆都城。閻王見他長相奇特,便封他為拘拿人家圣靈的“辦差官”。事有湊巧,在李正士死后的幾天內(nèi),獨流鎮(zhèn)的有四戶人家的公子都忽然得了重病,并在晚上都做了相同的夢:“如為李正士在第三埠修一座廟,病人即能痊愈”。后來這幾家富戶便捐錢建成了“李爺廟”,并且公子們的病就真的好了。[3](P433)
這種民間傳說多為以訛傳訛或者編造,但李爺廟在清末香火尤為旺盛卻是事實。由于其傳說的非常靈驗,津冀一帶的船戶都經(jīng)常到李爺廟燒香許愿,祈求船運平安。隨著李爺廟的聲名遠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李爺”信仰,在獨流鎮(zhèn)的許多村里都建起了“李爺廟”,以求庇佑船運平安。獨流鎮(zhèn)特有的李爺信仰是航運業(yè)發(fā)展過程中的產(chǎn)物,伴隨著河運的繁榮發(fā)展,李爺信仰成為船戶們的重要精神寄托,也是河運文化在民間信仰中的體現(xiàn)和深刻烙印。
清代彭城鎮(zhèn)分布的廟宇眾多,大大小小的寺廟四十余座,規(guī)模較大的玉皇廟(萬神殿)、龍王廟、大鐘寺和都土地廟合稱為清代彭城四大寺廟。除去常見的佛教和道教寺廟,還有缸神廟、火神廟、陶神廟、晉祠娘娘廟等多所與制瓷業(yè)相關(guān)的神廟,其行業(yè)神信仰尤為發(fā)達。行業(yè)神,又稱行業(yè)守護神、行業(yè)保護神,是從業(yè)者供奉的用來保佑自己和本行業(yè)利益,并與行業(yè)特征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的神靈[4](P5)。由于彭城鎮(zhèn)在清初已經(jīng)是成熟的陶瓷業(yè)專業(yè)市鎮(zhèn),其行業(yè)神信仰也隨著形成和發(fā)展,主要為陶神、缸神和火神。彭城鎮(zhèn)的陶神廟又稱為窯神廟,康熙三十四年(1695)《陶神廟戲樓碑記》載:“登其廟,殿宇巍峨,梁棟舞影,洋洋乎大觀也……募陶民約費白于金,而戲樓遂功成于乙亥(1695)之夏日。”從中可以看出,在康熙年間,陶神廟已經(jīng)是一座氣勢恢宏,初具規(guī)模的行業(yè)神廟,且在陶戶們心目中的地位神圣,在重修戲樓時,踴躍為戲樓捐資出力。除了供奉和祭祀陶神之外,陶神廟還是陶工們娛樂和交流的場所,“每年農(nóng)歷二月十五為陶工供奉祖師大會,提前請戲班在戲樓唱戲,一般為五天,由各窯場推舉總管負責(zé)籌資”[5](P11),這期間除了酬神演戲,娛樂消遣,陶戶們也在此相聚交流。
隨著彭城鎮(zhèn)制瓷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大批山西的工匠們來彭城鎮(zhèn)謀生。來自山西的工匠們主要從事缸窯燒制,這些缸匠們不僅在半壁街出資建造了缸神廟,還專門從山西請來了缸神爺供奉在廟內(nèi),所以缸神廟又被稱為“山西會館”。除了祭祀和供奉缸神,缸神廟還是山西缸匠們娛樂、接待和議事的場所,每年的九月初三為缸神爺生日,山西缸匠們便會籌資進行祭祀活動,包括唱戲、敬奉和還愿。火神不屬于行業(yè)神,但由于彭城鎮(zhèn)的陶瓷業(yè)對火尤為依賴,對陶瓷的制作,燒制過程尤為關(guān)鍵,因此大部分的窯工對火神尤為崇拜和景仰。道光年間的《重修火神廟序》載:“從來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然亦不過一鄉(xiāng)一邑已耳,而唯火德真君廟遍天下焉。況彭城缸碗兩行,莫不賴火以為陶冶。”[6](P1046)火神廟除去是窯戶和窯工的祭祀場所,還是燒工行會所在地。行會定期在火神廟舉行會議決定全鎮(zhèn)窯場各工種每燒一窯的價格,并處理和協(xié)調(diào)燒工之間的矛盾。彭城鎮(zhèn)的火神信仰區(qū)別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火神信仰,其反應(yīng)出的是制瓷業(yè)生產(chǎn)和發(fā)展過程中與民間信仰的互動與聯(lián)系,也是基層社會在生產(chǎn)和生活中對自然的敬畏與崇拜,進而轉(zhuǎn)化為更高層面的行業(yè)崇拜。
清代勝芳鎮(zhèn)也是寺廟紛繁,較為著名的有“三寺兩庵十八廟”。“三寺”是指東大寺、北大寺、石溝大寺;“兩庵”是如意庵、海月庵;“十八廟”是玉皇廟、老母廟、七神廟、關(guān)帝廟等,除去這些傳統(tǒng)的佛道寺廟及民間神廟,還有乾隆年間建立的清真寺和光緒末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在勝芳鎮(zhèn)復(fù)雜的信仰空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具有地方特色的火神和媽祖信仰。勝芳鎮(zhèn)的火神信仰源于該地葦編行業(yè)的興盛。在康熙末年中亭河開挖之前,勝芳淀水面寬廣,田地稀少,勝芳淀生長的大片蘆葦成為了當?shù)剞r(nóng)民重要的生活來源。“男打魚,女織席”的俗語是當時勝芳鎮(zhèn)農(nóng)民真實生產(chǎn)生活模式的描寫。葦行和席行是在此狀態(tài)下應(yīng)運而生的行業(yè),前者“專門經(jīng)營葦場,從事蘆葦收割、儲存、管理、買賣”,后者是指“收購葦行經(jīng)營者或百姓手中的蘆葦,并雇人編織成葦席或其他葦制產(chǎn)品,最終由其收購并賣給外地席鋪或其他客戶的買賣商”[7](P243)。由于葦行和席行的特殊行業(yè)性質(zhì),火災(zāi)便成為了最為需要防范的災(zāi)害,繼而便催生了勝芳鎮(zhèn)火神信仰的興盛,從事葦編行業(yè)的農(nóng)民籌資建起了火神廟。區(qū)別于彭城鎮(zhèn)“迎神”的祭祀活動,勝芳鎮(zhèn)是用“送神”的祭祀方式,在每年的農(nóng)歷四月初八和六月二十三開展持續(xù)四天的擺會,為火神爺送葬,祈求生產(chǎn)平安,后漸漸演變成為了著名的勝芳花會。媽祖信仰是典型的外來信仰,是明清內(nèi)河航運發(fā)展尤其是勝芳鎮(zhèn)航運業(yè)繁榮發(fā)展的產(chǎn)物。“漕糧運自東南沿海,海上形勢險惡難測。在這種形勢下,宋代在東南沿海地區(qū)產(chǎn)生并流行起的媽祖信仰自然會沿著海運路線向北遷移,這樣就形成了河北及京津地區(qū)媽祖信仰沿海河、北運河、通惠河至大都分布的格局。”[8](P137)清中期以后,勝芳鎮(zhèn)成為大清河上最要的商業(yè)碼頭,其航運業(yè)日益興盛,從事航運業(yè)的船戶、漁民和商人為祈求航程平安、貨物安全,開始信仰和祭祀媽祖,盛極一時。
在獨流鎮(zhèn)、彭城鎮(zhèn)和勝芳鎮(zhèn)的多元信仰文化空間的剖析中,可以發(fā)現(xiàn)工商業(yè)的繁榮與人口大量的集聚為市鎮(zhèn)多元信仰文化結(jié)構(gòu)的形成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肥沃的土壤,各種信仰文化遍布于市鎮(zhèn),本地與外來信仰文化在市鎮(zhèn)共生共存,形成了獨特的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信仰文化的特征,由于市鎮(zhèn)經(jīng)濟發(fā)展趨向不同,三鎮(zhèn)均形成了不同的“李爺”“陶神”“缸神”“火神”等行業(yè)神和地方神的崇拜,真實地反映出了海河水系沿岸區(qū)域經(jīng)濟生活狀態(tài),其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是區(qū)域基層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系統(tǒng)發(fā)展的文化性表達。
二、市鎮(zhèn)廟會文化的興盛
廟會是清代華北地區(qū)基層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體現(xiàn)在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構(gòu)建中,最直接反映的就是廟會文化隨著市鎮(zhèn)多元信仰文化的繁榮和商品貨幣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日益興盛,也是市鎮(zhèn)市場的一個重要補充。白洋淀沿岸的鄚州鎮(zhèn)有盛大的藥王廟廟會“諸會鱗集,祈福報賽者接踵摩肩”[9](卷二《建置·壇遺》),滹沱河沿岸的南孟鎮(zhèn)奶奶廟廟會,在清末“香煙甚盛,屆時婦女結(jié)隊胭脂成群,焚香祈禱者,絡(luò)繹不絕,繁華熱鬧,極一時之盛”[10](P104)。
獨流鎮(zhèn)、彭城鎮(zhèn)和勝芳鎮(zhèn)的廟會境況也是熱鬧非凡,獨具特色。獨流鎮(zhèn)的形成規(guī)模的廟會主要有藥王廟會、關(guān)帝廟廟會和李爺廟廟會。藥王廟廟會的會期是每年農(nóng)歷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是獨流及周邊地區(qū)最隆重的廟會;關(guān)帝廟廟會的會期為每年的農(nóng)歷九月九日;李爺廟廟會會期為每年的農(nóng)歷四月初六、九月初九、十二月初八日。彭城鎮(zhèn)的廟會有“八大”“九小”:土地廟廟會、萬神殿廟會、天齊廟廟會、缸神廟廟會、玉皇閣廟會等八處規(guī)模較大,會期一般持續(xù)二至三天;龍王廟廟會、火神廟廟會、奶奶廟廟會等九處是小廟會,會期只有一天。勝芳鎮(zhèn)的廟會較為隆重的有火神廟廟會、關(guān)帝廟廟會和娘娘廟廟會。
寺廟本是宗教信仰活動場所,所以廟會首先體現(xiàn)出濃厚的迷信崇拜色彩,來者首先是香客、祈禱者、信眾,后來許多寺廟所具有的文化娛樂與商業(yè)功能也都是由此而來的[11](P120)。獨流鎮(zhèn)、彭城鎮(zhèn)和勝芳鎮(zhèn)規(guī)模較大和較為隆重的廟會皆為鎮(zhèn)上最受崇拜和香火最為旺盛的寺廟,如獨流鎮(zhèn)的藥王廟、李爺廟,彭城鎮(zhèn)的陶神廟和勝芳鎮(zhèn)的火神廟等。民眾前來廟會的首要目的或是祈求神靈的庇佑、寄托情思,或是酬神還愿,以獨流鎮(zhèn)的李爺廟廟會為例,在廟會期間,獨流一帶乃至塘沽、漢沽等地區(qū)的漁民和船戶絡(luò)繹不絕前來燒香祭拜,以祈求航運平安,得到神靈庇護。在此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的基礎(chǔ)上,廟會才逐漸演變成為娛樂、聚會和商業(yè)交易的場所。廟會的娛樂活動最初是信眾自發(fā)的娛神、酬神和敬神的主要內(nèi)容和手段,雖逐漸演變成大眾娛樂,但其酬神祈靈的根源和目的始終存在。
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的廟會娛樂活動主要包括演戲和花會兩種形式。演戲是廟會娛樂活動中最普遍的的節(jié)目,在廟會興盛的廟宇中基本都建有戲樓,如彭城鎮(zhèn)的陶神廟、缸神廟、武圣廟和萬神殿均建有戲樓或者戲臺,除了固定的戲臺,每個廟會都會臨時搭建戲臺。花會是華北地區(qū)市鎮(zhèn)廟會獨具特色的娛樂文化,是一種獨特的廟會藝術(shù),和演戲酬神的性質(zhì)一樣,在廟會期間進行表演,以求神靈庇護、祈福還愿。《燕京歲時記》曰:“過會者,乃京師游手扮作開路、中幡、杠箱、五虎棍、跨鼓……耍獅子之類,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廟會,隨地演唱,觀者如堵。”[12](P63)獨流鎮(zhèn)有鑼鼓棒、龍燈、龍亭、鐘幡、法鼓、大高蹺、金錢蓮花落、少林會、桿會等幾十道花會。
而勝芳鎮(zhèn)的花會文化更為發(fā)達,在興盛時期可達到七十二道,比較著名的有勝芳南音樂會和跨鼓老會。每年的六月二十三日火神廟廟會期間,勝芳鎮(zhèn)所有的花會會社都要與火神爺游神儀式一起在全鎮(zhèn)進行巡游表演,持續(xù)四天時間,有迎神、敬神和送神的三個儀式。廟會的演戲和花會活動使得民眾在酬神祈靈的過程中進行放松和娛樂,給單調(diào)的生活增添樂趣,這對一年到頭忙于生計的鄉(xiāng)民極富有吸引力,“民俗終歲苦,間以廟會為樂,演戲召親”[13](卷五《禮儀志·風(fēng)俗》),使得廟會的性質(zhì)和功能都得到了延伸。
廟會在經(jīng)濟功能層面上可謂是市鎮(zhèn)商業(yè)市場的補充。廟會的宗教和娛樂功能集聚了大量的周邊人口,人口的聚集使得廟會具有較強的購買力,吸引市鎮(zhèn)以及周邊農(nóng)村地區(qū)的工商業(yè)從業(yè)者在廟會進行商業(yè)活動。根據(jù)表1(見次頁)統(tǒng)計,僅彭城鎮(zhèn)一處每年都會舉行十五次之多的廟會,超過一月一次的頻率。由于彭城鎮(zhèn)開設(shè)廟會的寺廟都集聚在鎮(zhèn)的前街、后街和南河溝三條大街,每場廟會時這三條大街都是攤鋪。每次廟會售賣的主要商品有所不同,視季節(jié)而定,有山貨、陶瓷、牲口、雜貨等,儼然和集市無甚區(qū)別。宣統(tǒng)元年(1909)《調(diào)查磁州集市廟會售賣物件冊》對磁州境內(nèi)的廟會售賣商品進行了統(tǒng)計,主要大宗商品有十四類,包括瓷器、礦產(chǎn)、米麥、牲畜、皮革、布匹、白酒等,除去本地的瓷器商和礦產(chǎn)商,牲畜商人多來自河南的林縣和涉縣,布匹商人多來自直隸曲周縣,白酒商人多來自山西襄垣和河南武安[14](P988-989),足可見彭城廟會市場的繁榮和商業(yè)吸引力。

表1 清代彭城鎮(zhèn)主要廟會情況匯總
三、基層文化教育的中心
“教育是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是文化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理解教育與文化的關(guān)系時,我們一般認為文化是本質(zhì)性的,教育是文化的形式,是一定人類文化的表現(xiàn)。”[15](P232)因此,在剖析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構(gòu)建過程中,市鎮(zhèn)教育是其重要的一項內(nèi)容,它不僅是市鎮(zhèn)文化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更是市鎮(zhèn)經(jīng)濟與社會在發(fā)展及近代化轉(zhuǎn)型過程中的重要一部分。在清末新政之前,“清朝地方教育體系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官辦的府、州、縣學(xué)及社學(xué)、義學(xué),二是獨立于官學(xué)系統(tǒng)之外的書院,三是里甲和私塾教育”[16](P122)。體現(xiàn)到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的文化教育中就是較為普遍的義學(xué)。
清代是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的義學(xué)建設(shè)的黃金時期。市鎮(zhèn)的義學(xué)教育屬于基礎(chǔ)性的普及教育,主要以官辦為主。官辦的“義學(xué)之設(shè),原以成就無力讀書士。……凡愿就學(xué)者,不論城鄉(xiāng),不拘長幼,俱令赴學(xué)肄業(yè)。其中有奮志讀書而貧乏無力者,該府尹酌給薪水以成就之。至建修房屋、師生膏火等費,應(yīng)于存公銀兩內(nèi)酌量奏請”[17]((嘉慶朝)卷三一七)。如彭城鎮(zhèn)義學(xué),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知州蔣擢設(shè)立,“捐備修補延師,以較童子而月試其文藝”[18],完全由官府負擔(dān)相應(yīng)支出。除去官辦,士紳出資捐立的義學(xué)也不在少數(shù)。“書院、義學(xué)所在有之,或先儒、明賢過化經(jīng)行之地。崇祀事以伸景仰,或窮鄉(xiāng)僻壤樂善好義之家,出錢谷以贍學(xué)徒,不必皆屬之官也”[19](P442),以獨流鎮(zhèn)為例,鎮(zhèn)內(nèi)共有義學(xué)四座,其中有兩座為靜海縣的士紳重修或捐建。也有官紳合辦的義學(xué),如勝芳鎮(zhèn)義學(xué),康熙年間由同知楊朝麟捐立,“延師由歲支公費”[20](卷二《學(xué)校·義學(xué)》)。無論是官辦還是士紳捐建,抑或是官紳合辦,市鎮(zhèn)義學(xué)的興辦吸引了鎮(zhèn)內(nèi)以及周邊農(nóng)村地區(qū)的士子們前來求學(xué),其建立形式的多樣化更是從側(cè)面反映出市鎮(zhèn)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文化教育之間的互動過程。
1901年,清廷開始實行“新政”,頒布了《興學(xué)詔書》,鼓勵各地興辦學(xué)堂。“除京師已設(shè)立大學(xué)堂應(yīng)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shè)大學(xué)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shè)中學(xué)堂,各州、縣均改設(shè)小學(xué)堂,并多設(shè)蒙養(yǎng)學(xué)堂”[21](P5-6)。市鎮(zhèn)的文化教育也進入了近代化改革階段,義學(xué)多改設(shè)為高等小學(xué)或蒙養(yǎng)學(xué)堂。“磁縣自前清末葉,庶政維新即開始舉辦新教育,當時邑人陳紹唐創(chuàng)設(shè)磁縣官立高等小學(xué)堂于城內(nèi),吳志仁開辦第二高等小學(xué)堂于彭城,凡學(xué)生書籍筆墨制服等概由學(xué)校供給,且每月予以津貼以資提倡”[22](P59)。“勝芳鎮(zhèn)高等小學(xué)系鎮(zhèn)款公立在河北大悲寺,清光緒三十二年成立。其建筑費二萬余吊由本鎮(zhèn)徐坤壽、彭王紳、祖經(jīng)勸募,立有碑記。”[23](P317)獨流鎮(zhèn)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獨流富戶趙向忠在元善義學(xué)的舊址上捐資建立了獨流蒙養(yǎng)學(xué)堂。三鎮(zhèn)的高等小學(xué)堂或蒙養(yǎng)學(xué)堂皆由當?shù)厣虘艟栀Y建立,且在其運行過程中也給予了大量的財力支持。以勝芳鎮(zhèn)為例,在勝芳高等小學(xué)堂建立之后,“勝芳鎮(zhèn)草捐全年洋八百元,由草商包辦。經(jīng)縣署規(guī)定年交洋八百元系最低數(shù),豐年再加,不許減”[23](P317)。另有油捐每年京錢四百吊、干鮮行津貼每年八十元、豬肉行津貼每年四十八元。
四、基層社會保障的中心
市鎮(zhèn)的基層社會保障中心是在其經(jīng)濟功能不斷輻射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逐漸形成的。清代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的普遍興起除了是周邊農(nóng)村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表現(xiàn),更是社會進入到封建社會末期出現(xiàn)的社會結(jié)構(gòu)變動的指征,最能體現(xiàn)這一特征的就是市鎮(zhèn)成了基層農(nóng)村地區(qū)的社會保障中心,主要包括社會救濟和社會服務(wù)兩個方面。
(一)社會救濟的中心地
市鎮(zhèn)作為基層農(nóng)村地區(qū)的救濟中心主要涵蓋救荒備荒、養(yǎng)濟孤貧、施棺助葬等活動,具體體現(xiàn)在社義倉、養(yǎng)濟院、棲流所、義冢等場所和組織在市鎮(zhèn)的設(shè)立。清王朝為了備荒、賑災(zāi)、調(diào)控糧食價格,從順治年間開始逐漸完善地方倉儲設(shè)置,至乾隆年間,基本形成了常平倉、義倉和社倉為主的地方倉儲格局,并諭令常平倉設(shè)于州縣治,義倉設(shè)于市鎮(zhèn),社倉設(shè)于鄉(xiāng)村。作為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的典型代表,獨流鎮(zhèn)、勝芳鎮(zhèn)和彭城鎮(zhèn)在清代設(shè)有義倉,且均設(shè)于乾隆年間。“靜邑舊有義倉九座,內(nèi)獨流一座”[24](P8),“文安義倉九處,一在勝芳鎮(zhèn)”[23](P165),“乾隆十八年,遵照通飭,勸諭鄉(xiāng)民在于州屬之……彭城……等九村鎮(zhèn)修建倉廒,勸捐義谷儲存,以備賑貸”[22](P13)。義倉從修建到管理和運行完全是按照“官倡民辦”的模式,以彭城鎮(zhèn)為例,修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的彭城鎮(zhèn)義倉,是遵照諭令,勸諭鄉(xiāng)民共同出資修建。義倉中所儲備的糧食皆來源于鄉(xiāng)民,“嘉慶十九年,奉文修整并令勸捐谷石,何州牧勸諭四鄉(xiāng)共捐谷五千余石儲存”[22](P13)。官府僅是倡導(dǎo)和勸諭,義倉的修建和儲谷都依靠鄉(xiāng)民,可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對于義倉在基層地區(qū)的賑濟范圍,康熙十九年(1680)曾諭令:“嗣后常平積谷留本州備賑,義倉、社倉積谷留本村鎮(zhèn)備賑,以免協(xié)濟外郡。”[25](卷十三《食貨十三·輕重上》)因此,市鎮(zhèn)的義倉的賑濟范圍僅限于本里社。根據(jù)地方志資料的統(tǒng)計,獨流鎮(zhèn)義倉賑濟輻射范圍內(nèi)的村鎮(zhèn)有8個,勝芳鎮(zhèn)義倉賑濟輻射范圍內(nèi)的村鎮(zhèn)有23個,彭城鎮(zhèn)義倉賑濟輻射范圍內(nèi)的村鎮(zhèn)有21個,具體見表2。

表2 三鎮(zhèn)義倉所輻射范圍的情況統(tǒng)計表
除了設(shè)立義倉以備荒和救荒,以官辦為主的留養(yǎng)局、棲流所、漏澤院等組織的設(shè)立以及清末逐漸出現(xiàn)的多元化民間慈善組織,共同構(gòu)筑了市鎮(zhèn)的救濟中心地的角色。留養(yǎng)局和棲流所由于社會救濟功能的一致性在多種史料中經(jīng)常被混用或統(tǒng)一歸為“留養(yǎng)局”,是在市鎮(zhèn)設(shè)立最多的救濟機構(gòu),乾隆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直隸總督方觀承率同官紳在直隸全省建設(shè)了留養(yǎng)局561所,均分布于“城市集鎮(zhèn)沖 途孔道”[26](P440),以“收 養(yǎng)道路貧病無依之人及本地孤貧之不在額者”[27](卷四《建置志·惠政》)。居于水陸交通要沖,輻射周邊農(nóng)村經(jīng)濟地區(qū)的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自然是設(shè)置留養(yǎng)局的首選之地,有的甚至規(guī)模和輻射作用超過縣治所內(nèi)設(shè)的留養(yǎng)局,如洺河沿岸的臨洺鎮(zhèn)留養(yǎng)局,有“局舍三十六間,知縣孔廣棣碑記所謂‘規(guī)制廣于城局’者也”[28](P28)。
作為工商業(yè)日趨繁盛的獨流、勝芳和彭城三鎮(zhèn),由于經(jīng)濟中心地功能輻射的不斷擴散,吸引了大量周邊失業(yè)的游民和流民到市鎮(zhèn)謀生,使得留養(yǎng)局或棲流所成為市鎮(zhèn)發(fā)展過程中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障,以保障市鎮(zhèn)的勞動力市場。以彭城鎮(zhèn)為例,在清初已經(jīng)是以制磁業(yè)繁盛著稱的彭城鎮(zhèn),由于窯場的增多和磁器運銷的擴張,吸引了大量周邊的流民來彭城鎮(zhèn)謀生,尤以山西一帶為多。為了救助隆冬時節(jié)來彭城鎮(zhèn)謀生且居無定所的山西游民,知州蔣擢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立了棲流所:“知州蔣擢因彭城地方有山西一帶流民到境,時值隆冬,往往棲宿窯內(nèi)廟中,多致斃,鄉(xiāng)地紛紛呈報。乃捐俸設(shè)立空局三間,凡真正流丐來到者,鄉(xiāng)保地方一面即時安插,一面查明姓名、籍貫、年歲、來歷、到境日月,報官存案,每人每日官給錢三十文,一月一發(fā)。保地領(lǐng)錢,按名給散,仍取領(lǐng)狀附卷以防詐冒。自十月起至二月終止。外又查照人數(shù)量給草束,以便臥宿,并查單衣無棉者給棉衣一件。自是外來流丐有所棲止。”[18](卷五)
進入清末之后,隨著市鎮(zhèn)經(jīng)濟的近代化發(fā)展,市鎮(zhèn)的社會救濟組織也趨于多元化,除了官辦的棲流所或留養(yǎng)局,出現(xiàn)了諸多民辦或商辦的慈善組織。以獨流鎮(zhèn)為例,在清末由鎮(zhèn)內(nèi)富戶出資建立了救恤會和掩骨會。救恤會是清末獨流鎮(zhèn)最大的慈善救濟組織,“設(shè)立在獨流鎮(zhèn)玄帝廟內(nèi),經(jīng)費由董事捐納,或施藥品或施棺木,又分設(shè)貧民學(xué)校恤嫠會,臨時兵災(zāi)救濟會等”[19](P443)。掩骨會是一種類似于漏澤院或義冢的民間助葬機構(gòu),清末獨流鎮(zhèn)的掩骨會在每年的清明節(jié)、七月十五“鬼節(jié)”、十月初一“寒衣節(jié)”時,雇工將義地、亂葬崗中暴露在外的尸骨進行掩埋,除此之外,如有臨時在路邊凍死或餓死的路人,掩骨會也會雇人埋葬。
(二)社會服務(wù)的中心地
市鎮(zhèn)的社會服務(wù)功能是在工商業(yè)日益繁盛的基礎(chǔ)上逐漸產(chǎn)生的,作為社會保障中心地角色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服務(wù)主要通過市鎮(zhèn)的行會、商會以及水會等組織進行開展,涵蓋內(nèi)容多樣,包括對行業(yè)發(fā)展的維護和協(xié)調(diào)、工商業(yè)從業(yè)者利益的維護和糾紛的協(xié)調(diào)、工商業(yè)經(jīng)營環(huán)境的保護和調(diào)節(jié)以及對居民提供慈善救助服務(wù)等多方面。
隨著工商業(yè)從業(yè)者在市鎮(zhèn)的日益活躍,在清中前期,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中涌現(xiàn)出了大批的商人組織,他們或以行業(yè)為組織,或以地域為組織,被稱為“行會”或者“堂會”。行會涉及到市鎮(zhèn)商業(yè)和手工業(yè)各個領(lǐng)域,如較為普遍的牙行、腳行、水運行、騾馬行、糧油行等,也有具有市鎮(zhèn)自身特點的行會,如勝芳鎮(zhèn)的草行和彭城鎮(zhèn)的缸碗兩行。為了維護和管理草行,勝芳鎮(zhèn)專門成立了草商公會,叢中選取會長負責(zé)工會組織管理工作,公會組織中專門成立了護青隊伍。為了規(guī)范葦席行業(yè),草商公會還制定保護蘆葦生產(chǎn)的條規(guī)。清代彭城鎮(zhèn)的缸行為山西制缸匠人所壟斷,出資建設(shè)的缸神廟,并以此為行會會址,處理和協(xié)調(diào)匠人之間的內(nèi)部與外部關(guān)系,維護山西匠人的利益,又稱為“山西會館”。彭城的缸行制定了嚴格規(guī)定以維護山西匠人的捏缸技藝,如有私授技術(shù)者將被逐出彭城鎮(zhèn)。同時,如同鄉(xiāng)遇到困難,行會也會出資進行救助。

表3 光緒三十三年(1907)彭城鎮(zhèn)商務(wù)分會集議
進入清末之后,隨著市鎮(zhèn)工商業(yè)的近代化演變,商會開始出現(xiàn)在華北社會經(jīng)濟的歷史舞臺,以光緒二十九年(1903)天津商會總會商務(wù)設(shè)立為輻射中心,開始擴散至工商業(yè)比較發(fā)達的市鎮(zhèn),并在市鎮(zhèn)社會服務(wù)發(fā)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獨流、勝芳和彭城三鎮(zhèn)皆設(shè)有商務(wù)分會,彭城鎮(zhèn)商會分會設(shè)立最早,成立于光緒三十二年,入會商戶不僅限于瓷器業(yè),“外行各商情愿入會者尤復(fù)不少”[14](P197)。彭城商會分會在規(guī)范各行業(yè)市場、改良瓷器制作工藝、開辦學(xué)堂、穩(wěn)定貨幣流通和物價、街市管理等諸多方面發(fā)揮著尤為重要的社會服務(wù)功能,輻射市鎮(zhèn)各行業(yè)及人群。
除了行會和商會,以水會為代表的社會公益組織在市鎮(zhèn)社會服務(wù)中心角色的構(gòu)建和輻射過程中也占據(jù)有一席之地。水會又稱“水局”“救火會”,是典型的民間公益組織,最早出現(xiàn)于南宋。華北地區(qū)的水會,在清中期多設(shè)于州治或者縣治,直至清末才逐漸擴散到工商業(yè)發(fā)達、居民集聚的市鎮(zhèn)。獨流鎮(zhèn)水會組織最早建于咸豐年間,名為“保安水局”,后又于光緒年間建了“樂安水局”和“普安水局”。三處水局互為備用,一旦商戶及鄉(xiāng)民遇到火災(zāi),能夠及時撲滅救助。“謹案守望相助,鎮(zhèn)鄉(xiāng)皆同,況水火之警,其不披發(fā)纓冠者未之有也,惜其設(shè)備不完,時有束手之患。若下所載,皆有組合,有秩序,有器具,故有備無患”[19](P443)。清末文安縣境內(nèi)共有水會五處,僅勝芳鎮(zhèn)就占了四處,分別為:靜安、平安、勝安和鎮(zhèn)離,分設(shè)于鎮(zhèn)的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以求“消禍澹災(zāi),濟人之急”[23](P165)。作為民間慈善組織,市鎮(zhèn)的水會基本由個別大商戶捐資創(chuàng)辦,然后再由入會的商戶捐資購買滅火器材,例如獨流鎮(zhèn)的保安水局就由鎮(zhèn)上富商鄭氏創(chuàng)辦,共捐房五間。這些設(shè)置于市鎮(zhèn)各角落的水會,“遇有火警,鳴鑼伐鼓,奔走往撲,無遺力,無渙情,絕不令延及他方、成燎原莫救之勢。臨火者大可受其保護,無慮俱焚,地方公益,以此為最”[23](P165)。
五、結(jié)語
通過對比分析和考察,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以獨流鎮(zhèn)、勝芳鎮(zhèn)和彭城鎮(zhèn)為典型代表的海河水系沿岸市鎮(zhèn)已經(jīng)成為周邊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中心地。在市鎮(zhèn)文化中心地角色形成和擴散的過程中,市鎮(zhèn)工商業(yè)發(fā)展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市鎮(zhèn)中信仰文化空間、廟會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功能形成和擴展的主要驅(qū)動力,也正是由于市鎮(zhèn)工商業(yè)類型和自身發(fā)展狀況的差異,造就了單個市鎮(zhèn)文化空間的明顯差異,比如:地方神與行業(yè)神崇拜的差異化明顯,廟會活動體現(xiàn)形式及過程各有千秋、開展社會救助和服務(wù)的行會與商會組織也有較大差異,同時,也是海河水系沿岸不同經(jīng)濟類型、規(guī)模和等級市鎮(zhèn)在文化中心地功能構(gòu)建過程中的典型縮影。
在綜合視角之下,多元文化信仰的凝聚和融合、廟會文化日益興盛、義學(xué)的普遍建立以及社會救助和社會服務(wù)功能的不斷完善促使市鎮(zhèn)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構(gòu)建,促使市鎮(zhèn)社會形成了獨具海河水文化烙印的復(fù)合型市鎮(zhèn)文化特質(zhì)——水運文化、經(jīng)濟導(dǎo)向、多元功能,在區(qū)域經(jīng)濟社會中發(fā)揮著重要的文化中心地的作用。正是這種“和而不同”的發(fā)展趨向促使海河流域的市鎮(zhèn)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突破單一形象,更加復(fù)雜和多元。這些既有一致性又有獨特性的文化特質(zhì),承載著輻射范圍內(nèi)基層社會的物資和精神內(nèi)涵,依托海河水系構(gòu)筑的水運網(wǎng)絡(luò)帶動市鎮(zhèn)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構(gòu)建和功能的不斷向外圍延伸,成了清代華北地區(qū)基層社會文化中的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