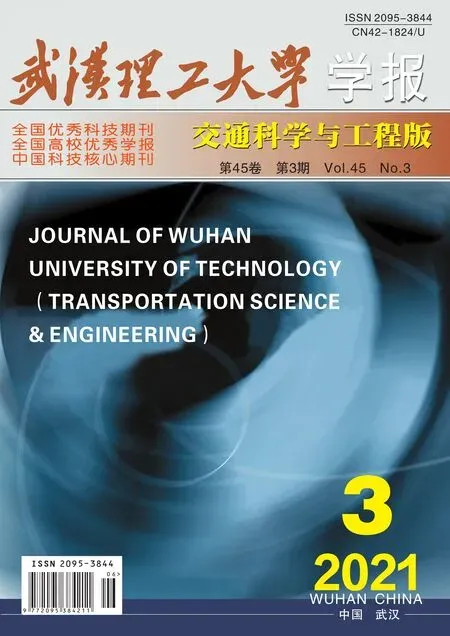多因素制約下的港區交通資源承載力研究
甘浪雄 龔楚鉅 張 羽 張 磊 束亞清 姜宇昂
(武漢理工大學航運學院1) 武漢 430063) (內河航運技術湖北省重點實驗室2) 武漢 430063)
0 引 言
隨著科技、貿易的快速發展,日益增大的船舶數量和水上運輸貨物量,導致了航道通過能力不足、錨地及泊位資源的短缺.由于受到港區岸線資源、可利用水域面積等因素的限制,港區交通資源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將達到承載極限,伴隨而來的是愈加復雜的交通態勢,將嚴重制約港口區域經濟的發展.因此,針對港區水上交通資源承載能力進行量化和分析,能夠有效評判港口交通資源的合理性,對未來合理的規劃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國內外關于港口交通資源承載力方面的研究多圍繞水土、景區及環境[1-4]等方面開展.于美娜等[5-6]對港區可持續發展性進行評價,分析影響港區環境承載力的主要因素.在港口資源承載力方面.桂勁松等[7]基于工程模糊集理論,結合港區能源消耗、環境污染所造成的代價以及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進行綜合評估,建立了基于港口貨物吞吐量的預測模型.陳楷根[8]定義了區域承載力的概念,認為承載力需要適度而非最大承載極限.韓鵬等[9]匯總了環境承載力的常見的評價方法,并根據實例探討了各個評價方法的優點和不足.
這些方法多為定性評價,缺乏以真實數據支撐的定量評價手段.文中構建航道、錨地及泊位的單因素量化模型,分析單因素之間的影響及制約關系,基于排隊理論構建港區交通資源承載力的計算模型來對港口整體的承載力量化計算,引入ALARP原則設定承載力分級標準,根據分級評價結果得知港區現階段交通資源承載能力,從而發現制約港口發展的因素,進而采取相應措施,更有效地服務于港口建設.
1 港區交通資源承載力建模
1.1 港區交通資源及其承載力的概念
港區交通資源指船舶運動所處的空間和條件,主要包括航道資源、錨地資源和碼頭泊位資源.承載力的實際含義就是反映出來某種物質的基礎與受體的耦合關系,表現在物質作為基礎條件能夠維持受載體的數量極限.港區交通資源承載力表示在一定范圍、時間和空間內,現階段港區的交通資源能夠支撐港口發展的經濟要求,同時又能維系系統安全、便捷、可持續發展的承受能力,其中包括航道的通過能力、錨地利用率以及泊位的服務效率.
1.2 ALARP分級標準
“最低合理可行”原則(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ALARP)[10],是當前國外風險可接受水平普遍采用的一種風險判斷原則.風險標準構成見圖1.

圖1 承載力分級圖
1.3 量化模型
1.3.1錨地承載力的量化
錨地利用率是指在不考慮船舶隨機到達規律特征的情況下,通過計算錨泊船占用水域面積的總值與錨地實際總面積的比值.單船錨泊面積計算根據拋錨系泊中單錨泊方式計算[11]:
S=πR2=π(ε+L+d)2
(1)
式中:S為船舶錨泊面積;R為錨泊船的安全半徑;ε為VTS定位產生的誤差;L為錨泊船舶的船長;d為錨泊船投放錨鏈的長度.
在計算出單個船舶錨泊所需的水域面積之后,通過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數據統計錨地內一段時間錨泊船舶數量及平均錨泊時間,最終求得該水域運輸船舶對錨地面積的需求.
錨地利用率的計算方式為
(2)
式中:Mi為錨地的利用率,即錨地的承載力指數;Ar為錨地的面積需求值;k為錨地有效利用系數;At為錨地的建設水域面積.
參照本領域內[12-14]的研究成果設定分級標準.表1~3分別為錨地、航道及泊位承載能力分級標準,表4為綜合多種因素后的綜合承載能力分級標準.

表1 錨地單因素承載能力分級標準

表2 航道單因素承載能力分級標準

表3 泊位單因素承載能力分級標準

表4 多因素制約的綜合承載能力分級標準
1.3.2航道承載力的量化
航道通過能力是指航道在一定時期內能夠通過的最大運輸量,其能力直接表現在港口的貨物吞吐量大小上.航道通航的飽和程度可以用來衡量航道的通航能力及服務能力,由實際的船舶流量與航道理論上的通航船舶容量比值表示,計算的結果可以用來反映航道某一時間段或區域段的擁擠程度.
為方便計算需進行交通流量的換算,根據不同船長的船舶在某區域交通流量中的占比,以該區域航行的占比最大的船舶類型作為標準船型,設定其換算系數為1,其它噸位的船舶參照中國船舶換算系數換算,得到最終的交通流.
航道年貨物承載能力為
Tf=Cad×DWT
(3)
式中:Cad為航道的年基本交通容量;DWT為船舶平均載重.
航道的飽和度研究可以體現出港口中航道現階段使用情況,具體可以表示為航道實際貨物吞吐量與理論貨物承載量的比值.航道的實際交通流量需要考慮生產生活中的影響因素,如航道環境、交通態勢等[15].
航道飽和度為
Hi=Tr/Tf
(4)
式中:Hi為航道飽和度;Tr為貨物吞吐量,億t;Tf為貨物承載能力,億t.
1.3.3泊位承載力的量化
當系統中有k艘船舶時,系統的狀態為k,此時的概率為Pk,k隨著船舶到達和離開港口而不斷發生變化,Pk隨著時間t而發生變化.當k從狀態1轉移到0說明系統中有一艘船舶并且船舶被服務完畢離開港口的轉移率為μP1;從狀態2到狀態1時,那么說明2個泊位上被服務的船舶中有一艘船舶服務完畢離開港口,轉移概率為2μP2;同樣的道理,從狀態C轉移到c-1時,如果k 狀態轉移的過程中,系統處于穩態或平衡狀態的充要條件是 ρ=λ/Cμ (5) 式中:ρ為排隊系統服務強度,反映泊位的利用率;λ為每天到港船舶的平均數量;C為泊位數;μ為每天服務完畢的船舶數量. 排隊系統中船舶平均在港時間以及船舶平均等待時間可以反映出港區交通資源錨地的承載水平,等待時間及等待的船舶數量能夠反映出錨地的承載能力. 碼頭泊位全部空閑事件發生的概率 (6) 在港待泊的平均船舶數: (7) 船舶在港內的平均等待時間td為 td=Lq/λ (8) 將航道飽和程度與泊位的利用率進行比較,貨物吞吐量越大則泊位越繁忙也就意味著泊位利用效率越高,航道也就越擁擠.假定港口貨物吞吐量為某一定值的情況下,如果碼頭泊位利用率達到高載或高負荷狀態,相對于航道交通資源來說,泊位資源就是承載力的“短板”;如果航道的通過能力不足或者嚴重擁擠,導致船舶靠離泊作業以及駛離港口的效率過低,那么航道資源就是承載力的“短板”.將錨地利用率與碼頭泊位的利用率作比較,貨物吞吐量越大也就說明泊位利用率越高,而在錨地資源上可以從錨地船舶數量以及錨地船舶平均等待時間等指標上體現.當貨物吞吐量一定時,如果錨地利用沒有達到高載或超載狀態,還可以容納船舶到達排隊,而泊位的利用率已經超負荷,導致錨地船舶等待時間較長,則泊位是瓶頸因素;如果泊位的利用率尚處于正常且健康的運作狀態,而錨地卻已經達到高載或滿載狀態,導致港口整體的服務水平較低,可認為錨地資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因素. 排隊服務強度反映碼頭泊位的繁忙程度,服務強度大于1會造成船舶無限排隊,當服務強度小于1時說明港口服務強度滿足要求,航道承載力可參照航道承載力預警指標. 排隊等待船舶的錨地需求面積為 Ay=Lq·Td·S (9) 錨地排隊等待船舶的承載力指數為 Mj=Ay/Af (10) 港區綜合承載力 M=min(Mi,Mj) (11) 選取深圳西部港區水域范圍并獲取2018年全年AIS數據進行實例計算.西部港內共建泊位107個,深水泊位25個;共有90個生產性泊位,集裝箱泊位28個,危險品泊位6個,雜散貨泊位24個,客運泊位20個及其他功能泊位;錨地7處,錨地總面積約30.45 km2,主要通航航道5條,貨物吞吐量為2.51億t.通過船舶AIS數據得知,2018年進出港船舶總數量約為37.43萬艘·次,其中集裝箱船進出港數量為12.81萬艘·次,約占總體數量的34.2%. 1) 錨地相關參數 根據篩選的結果計算出錨地的平均錨泊船數、錨泊船的平均船長,以及平均錨泊時間等相關系數,見表5. 表5 錨地AIS信息篩選統計結果 2) 航道相關參數 根據2018年深圳西部港區的航道參數,將航道劃定為多邊形的水域范圍,并找到每個節點的坐標,導入MATLAB中進行船位點的船舶AIS信息篩選,依照篩選導出的結果計算航道的通航船舶數量、平均航行時間等參數,見表6. 表6 航道AIS信息篩選統計結果 3) 運輸船舶在港數據 本文通過對深圳西港2018年掛靠港61 366艘·次船舶數據,利用MATLAB對船舶類型、平均船長、船寬、平均在港時間,以及平均作業時間進行統計,統計結果見表7. 表7 船舶在港數據 將各類參數代入承載力計算模型后,依據ALARP原則對其進行分級顯示.以集裝箱船為例,每天到港船舶的平均數λ為57艘;泊位數C為28,平均服務船舶數μ為2.65艘/d,利用式(5)計算得到服務強度ρ為0.769 3,利用式(7)計算得到平均排隊船舶數為0.806 8艘,利用式(8)得到平均排隊時間為0.089 5 d.再依次得到雜、散貨類,油、危險品船及綜合計算結果,見表8. 其中,錨地、航道及泊位三個影響港區交通資源承載力的單因素計算結果見表9. 表8 港區交通資源承載力計算結果 表9 影響港區承載力單因素計算結果 根據計算結果可知,目前整體來看,深圳西部港區承載力為0.826 7,雖然仍然處在可接受范圍也就是“ALARP”區域中,但數值已經十分接近“不可接受區域”.另外通過對不同類型進行分類計算可以發現,集裝箱類泊位服務能力仍未飽和,還有較為可觀的承載空間,而雜散貨類型卻已經處于“不可接受”區域,承載能力較弱,泊位高度繁忙,到港船舶需要排隊時間接近7.98 h,這也與船舶AIS信息中統計的平均等待時間較為接近.分析承載力的單因素指標可以發現,貨船錨地、液貨船錨地以及黃田3號錨地已經處于超載的“不可接受區域”,銅鼓航道、媽灣航道也十分繁忙和擁擠,這些交通資源的承載力低下無法滿足當前港口運輸船舶的需求,需要及時采取措施. 根據計算結果,深圳西部港區的錨地資源已經呈現“高載”的態勢,建議深圳西部港區采取以下措施:①擴建錨地,為錨泊船舶提供高質量服務;②優化錨地布局,部分錨地的利用率并不高.航道資源中,銅鼓航道及媽灣航道的飽和度指標分別為0.913和0.862,已經在“不可接受”的風險范圍內,可以通過擴建現有航道、設置船舶定線制等來提升航道通航能力.泊位資源中,僅有雜散貨類的泊位處于“不可接受”風險區域,貨船錨地、液貨船錨地已經處于嚴重超載的狀態,可通過增設泊位,合理分配資源,增加散貨船泊位以滿足此類船舶的運輸裝卸需求;同時可以優化產業結構,合理規劃其港區分布,增設錨地,避免集中在某一空間導致嚴重超載的情況發生. 本文從錨地、航道和泊位三個單因素出發,分別構建了量化模型,并進一步構建了多因素影響下的綜合量化模型,對承載力進行等級界定.最后以真實港區數據進行實例研究,通過對得到的結果進行分析,提出了有針對性的交通資源優化建議.本文研究內容有助于提高海事局對于轄區內交通環境狀況的認知和把控,并且提供量化指標供港口管理者做出科學決策.1.4 綜合承載力計算
2 計算結果分析
2.1 數據來源
2.2 計算結果





2.3 優化建議
3 結 束 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