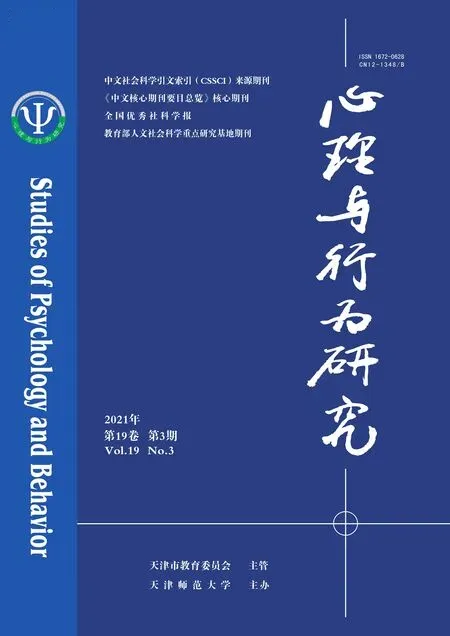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關系:心理韌性與同伴影響抵抗的鏈式中介作用*
張珊珊 鞠 睿 李亞林 王曉莊
(1 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職業教育學院,天津 300222) (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387) (3 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天津 300387) (4 學生心理發展與學習天津市高校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87)
1 問題提出
問題行為(problem behaviors)通常分為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兩類。內化問題是指個體經歷的一些負性情緒情感,包括焦慮抑郁、退縮、身體主訴等;外化問題是指個體違反社會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的行為,包括違紀、攻擊等(Achenbach &Rescorla, 2001)。在青少年階段,內外化問題普遍存在,會對青少年社會適應和身心健康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張野, 韓雪, 張珊珊, 王凱, 2020)。生態系統理論指出,家庭作為個體成長中最直接的微觀環境,是影響青少年情緒與行為發展的第一環境系統(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其中,親子依戀(parent-child attachment)作為家庭養育環境的核心變量,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Brumariu & Kerns, 2010)。親子依戀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間建立的持久且強烈的情感支持與聯結(Groh, Fearon, van IJzendoorn, Bakermans-Kranenburg, & Roisman, 2017)。與不安全親子依戀相比,同父母建立安全依戀模式的青少年焦慮、抑郁和退縮水平更低(Kerns & Brumariu, 2014),敵意和攻擊性行為更少(聞明晶, 滕樹元, 馮曉杭,田金來, 張向葵, 2020)。可見,安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密切相關,是其內外化問題的關鍵保護因子。那么,親子依戀如何影響青少年內外化問題?基于資源保存模型(Hobfoll, 2011),親子依戀作為影響青少年問題行為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性資源,需要個體特質資源(如心理韌性、同伴影響抵抗)的傳遞作用。然而,目前還缺乏相關研究的深入分析。因此,本研究探討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影響中的作用機制。
1.1 心理韌性的中介作用
青少年心理發展受外部環境和內在特質因素的共同影響(Magnusson & Stattin, 1998)。因此,親子依戀對青少年行為發展的保護作用需要個體內在品質的助益,適應逆境的能力是減少問題行為的關鍵因素之一(Calkins, Blandon, Williford, &Keane, 2007)。心理韌性(resilience)是指個體面對生活逆境、創傷或壓力等情境下的應對能力(Connor & Davidson, 2003)。社會建構模型認為,如果兒童早期初步形成了與重要他人的安全依戀關系,發展了被接納和自主的需要,就會形成韌性的自我建構,發展出抵御環境危機,運用內在保護力量的積極社會適應能力,并作用于個體與環境的互動(Ungar, 2001)。可見,親子依戀對個體心理韌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正如研究發現,高質量親子依戀的個體擁有較高的心理韌性水平(王中會, 藺秀云, 2018; Yule, 2011),而青少年心理韌性的提升可有效減少內外化問題(陳燕, 2019; 萬鵬宇, 林忠永, 馮志遠, 陳露露, 楊新國,2017; Huang, Chen, Greene, Cheung, & Wei, 2019)。因此,研究假設心理韌性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之間起中介作用。
1.2 同伴影響抵抗的中介作用
青少年的校園生活多于家庭生活,在強烈的群體歸屬需求下,為了不脫離同伴規范或同伴群體角色的社會情境,青少年可能在不良同伴壓力中服從同伴的興趣、愛好和行為(Steinberg &Monahan, 2007)。因此,青少年對同伴壓力的敏感性的個體差異,即拒絕服從同伴壓力的同伴影響抵抗(resistance to peer influence)能力將成為制約青少年問題行為的重要因素(Pfeifer et al., 2011)。
研究顯示較低的同伴影響抵抗能力將增加青少年認同不良同伴行為的可能性,提高外化問題行為發生的風險(安靜, 2014; Mercken, Steglich,Sinclair, Holliday, & Moore, 2012)。而父母的愛護會促使青少年形成較好的抵抗同伴壓力影響的能力,進而減少其物質濫用、情緒障礙等問題行為發生的風險(劉玲玲, 田錄梅, 郭俊杰, 2019; Smorti,Guarnieri, & Ingoglia, 2014)。可見,同伴影響抵抗可增加親子依戀對內外化問題的助益。因此,研究假設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之間起中介作用。
1.3 心理韌性與同伴影響抵抗的鏈式中介作用
文獻回顧顯示,目前缺乏直接證據說明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問題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基于資源保存理論(Hobfoll,2011),良好的親子依戀關系是外部的家庭環境資源,將促進個體內部積極心理資源的建構和維持,并通過增益螺旋效應增強心理資源積累,減少內外化問題。也就是說,一開始擁有較多心理資源的個體具有更多機會,進而更有能力獲得新的資源,資源的增益表現為螺旋式上升(Hobfoll,Halbesleben, Neveu, & Westman, 2018)。而心理韌性屬于抵御危險情境的應對能力,擁有這一積極心理資源的個體不但有能力獲得其他積極資源,且所獲得的積極資源會有更大的增益效果。高心理韌性的個體由于擁有充足的社會適應能力(如抵抗不良誘因、抗挫折),對不良同伴行為的抵御能力更強,問題行為更少。因此,有利的家庭環境資源促進了青少年心理韌性資源的發展,從而提高了其自律和社會適應等心理能力(Johnson,2012)。而自律的增強有助于抵抗不良同伴影響(Marsden, 2017),進而減少青少年內外化問題。因此,研究假設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行為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另外,有研究表明同一心理變量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影響強度不同(彭源, 朱蕾, 王振宏,2018; Martínez-Ferrer & Stattin, 2017)。因此,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影響是否有差異,以及心理韌性與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和青少年內外化問題之間可能的中介作用路徑是否相同,也需要探討。綜上,本研究在生態系統理論和資源保存理論的框架下,探討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影響機制及其差異。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取整群抽樣法選取吉林省某中學的學生施測。發放問卷1093份,回收1029份,有效回收率為94.14%。其中男生536人,女生493人;獨生子女604人,非獨生子女425人;初一558人,初二245人,初三226人;來自城市的學生753人,農村的學生276人;父親學歷為小學及以下190人,初中549人,高中/中專211人,大專及以上79人;母親學歷為小學及以下200人,初中539人,高中/中專205人,大專及以上85人;平均年齡為13.05±1.49歲。所有被試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2.2 測量工具
2.2.1 親子依戀問卷
采用簡版父母與同伴依戀問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中父子與母子依戀分問卷(Raja, McGee, & Stanton, 1992)評價初中生和父母的親子依戀。每個分問卷有10個項目,以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計分,含信任、溝通和疏離3個維度。由于中學生報告的父子依戀與母子依戀之間具有高相關,參照王樹青、張光珍和陳會昌(2014)的方式將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的數據合并作為親子依戀得分。分數越高代表親子依戀的安全性越好。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聚合成親子依戀高階因子模型的擬合指數良好,χ2/df=4.93,RMSEA=0.07,CFI=0.93,TLI=0.92,SRMR=0.04。
2.2.2 心理韌性量表
采用簡版心理韌性量表(Short Form of the Resilience Scale, SFRS)評價初中生的心理韌性能力水平(Wang, Shi, Zhang, & Zhang, 2010)。共10個項目,以1(代表“從不”)~5(代表“總是”)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心理韌性水平越高。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一因子模型擬合指數良好,χ2/df=4.05,RMSEA=0.07,CFI=0.96,TLI=0.95,SRMR=0.03。
2.2.3 同伴影響抵抗量表
采用同伴影響抵抗量表(Resistance to Peer Influence Scale, RPIS)評價初中生獨立與同伴交往的程度(孫瑩等, 2014; Steinberg & Monahan,2007)。量表含10種不同的同伴交往情境,每種情境分為“順從同伴的影響”和“拒絕同伴的影響”兩種相反的交往模式,被試選擇其中一種,并以1(代表“完全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對同伴不良影響的抵抗能力越強。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刪除2題后的一因子模型擬合指數良好,χ2/df=2.47,RMSEA=0.08,CFI=0.94,TLI=0.90,SRMR=0.04。
2.2.4 青少年自評量表
采用Achenbach青少年自評量表(Youth Self-Report, YSR)2001年中文修訂版評定初中生的內外化問題(王潤程等, 2013)。內化問題維度含焦慮/抑郁、退縮和軀體不適因子,共31題;外化問題維度含攻擊行為和違紀行為因子,共32題。量表適用于11~18歲,以0(代表“無”)~2(代表“明顯或經常”)計分。得分越高代表個體具有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可能性越高。
2.3 數據搜集
以班級為單位施測。培訓過的主試采用標準化指導語布置任務后發放知情同意書和問卷。被試完成填答后當場提交。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Harman單因素法結果表明共有22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個因子解釋了22.13%的變異,小于40 %的臨界值標準。同時,單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項擬合指數為:χ2/df=5.72,RMSEA=0.07,CFI=0.45,TLI=0.44,SRMR=0.09,模型擬合不理想。另外,以單一共同方法因子控制法分析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無法擬合。綜上,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值與潛變量相關估計
首先,對各研究變量對應題目的原始分進行平均數和標準差的描述統計。然后,為了更好地控制測量誤差,以潛變量相關分析估計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問題行為的樣本數據呈正偏態分布,故采用穩健極大似然估計的參數估計方法進行模型擬合。使用潛變量共5個:親子依戀、心理韌性、同伴影響抵抗、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結果顯示模型擬合指數良好,χ2/df=3.85,RMSEA=0.05,CFI=0.93,TLI=0.92,SRMR=0.04。親子依戀、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之間均存在兩兩正相關,而它們與內外化問題均存在負相關;內化與外化問題之間存在正相關。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觀測值描述統計與潛變量相關估計值
3.3 親子依戀對內、外化問題的直接預測效應檢驗
控制性別(男=0,女=1)和年級后,以內外化問題為因變量,親子依戀為自變量建構結構方程模型。模型擬合指數良好,χ2/df=3.26,RMSEA=0.04,CFI=0.98,TLI=0.98,SRMR=0.04。親子依戀對內化問題(β=?0.55)和外化問題(β=?0.52)均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p<0.001)。但是,限定親子依戀影響內外化問題行為的路徑系數相等后,Wald檢驗結果顯示,Δχ2=102.08,Δdf=1,p<0.001,說明親子依戀對內化問題的影響大于對外化問題的影響。
3.4 心理韌性與同伴影響抵抗的鏈式中介作用
控制性別和年級后,考察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內外化問題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顯示模型擬合指數良好,χ2/df=3.72,RMSEA=0.05,CFI=0.92,TLI=0.91,SRMR=0.05。如圖1所示,加入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兩個中介變量后,親子依戀對內化問題(β=?0.26)和外化問題(β=?0.18)仍具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p<0.01),表明親子依戀對內外化問題的預測作用部分以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為中介。

圖1 鏈式中介作用模型圖
采用重復抽取1000次的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對全模型中介效應的顯著性進行檢驗。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內化問題之間的標準化總間接效應值為?0.25,95%置信區間為[?0.34, ?0.18],三個中介效應路徑均成立。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內化問題之間的總間接效應值為?0.31,95%置信區間為[?0.40, ?0.21],三個中介效應路徑均成立。具體效應構成見表2。

表2 中介效應Bootstrap檢驗的效應值和置信區間
另外,當限定模型中心理韌性影響內、外化問題的路徑系數相等時,Wald檢驗結果顯示,Δχ2=2.30,Δdf=1,p>0.05,說明心理韌性在親子依戀影響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中的中介作用無差異。但限定模型中同伴影響抵抗影響內、外化問題的路徑系數相等時,Wald檢驗結果顯示,Δχ2=11.74,Δdf=1,p<0.001,說明相對于內化問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對外化問題的影響中具有更大的中介作用。
4 討論
4.1 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直接效應
研究探討了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關系及內部作用機制。潛變量相關分析顯示,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均存在顯著負相關。同時結構方程模型表明,控制性別和年級后,親子依戀能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內外化問題,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彭源等, 2018; ?tefan & Avram,2017)。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兩個中介變量后,親子依戀對內、外化問題的直接預測作用仍顯著。表明親子關系作為遠端的微觀環境變量,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影響雖然可以部分通過個體特質變量起到“橋梁”作用,但直接影響仍不能忽視,說明早期家庭養育環境對個體發展意義深遠,支持了生態系統理論。
同時,研究發現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即親子依戀與內化問題的關系更強。前人指出,個體的外化問題以指向外部的不良行為表達內在痛苦、憤怒與敵意等不良情緒,而內化問題直接指向個體內部,并通過焦慮、抑郁等情緒癥狀表達內心痛苦(Martínez-Ferrer & Stattin, 2017)。可見,內外化問題均是內部心理癥狀的表達。研究顯示,青少年內化問題可能以外化問題的形式表現(侯金芹, 郭菲, 陳祉妍, 2013),且內化問題會隨時間推移加重外化問題(韓紅, 程南華, 2020)。因此,內化問題的形成與存在是青少年有各種不良行為的關鍵。在良好的親子依戀中,父母的支持和良好的情感互動能夠帶來安全感,促使青少年更加積極地面對問題,減弱了生活壓力事件的內部破壞作用。這也從某種角度解釋了相對于外化問題,親子依戀與內化問題關系更強。因此,親子依戀對內外化問題的不同作用強度表明,個體早期與父母發展的安全性親子依戀雖然有助于減少指向外部的敵意,但對內在情緒問題影響更深遠。
4.2 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的中介作用
研究發現心理韌性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之間具有中介作用,與以往研究一致(陳燕, 2019)。盡管壓力事件、創傷性損失等不良外部環境將增加青少年罹患焦慮、抑郁的風險(Kerns &Brumariu, 2014),但有研究發現受害本身并不一定引發心理問題,心理功能受損才是根源(Calkins et al., 2007)。因此,不良親子關系對內外化問題的直接影響有限,而對不良環境的心理抗壓能力更重要。社會–心理–生物整合模型(Adler & Stewart,2010)強調社會環境會影響個體心理特征與行為,消極的家庭環境與有限的支持資源(不安全親子依戀)通過不足的心理資源(低心理韌性)影響認知功能和自我控制能力,增加了個體風險行為和情緒問題。這說明親子依戀構建的高功能家庭環境提供的保護有助于青少年合理應對負性生活事件,提高對壓力環境的適應能力,從而提升了心理韌性(王中會, 藺秀云, 2018),減少了焦慮、抑郁、攻擊和違紀等問題行為(萬鵬宇等, 2017)。
另外,研究表明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之間具有中介作用,特別是對外化問題的影響更大。青少年的逆反心理使其與父母的距離變遠,與同伴更親密,面臨親子關系主導到同伴關系為主的依戀結構轉變。兒童早期與父母關系的內部工作模型表征是個體后期其他依戀關系發展的原型(Suess, Grossmann, & Sroufe,1992)。青少年時期,親子依戀不再占據主導地位,但良好的親子關系仍能為青少年提供支持環境,減輕不良同伴行為的負面影響。以往研究表明,青少年對不良同伴行為的觀察學習極大增加了吸煙、飲酒等外化問題(安靜, 2014)。因此,培養青少年抵御不良同伴影響的能力對預防外化問題至關重要。
此外,研究發現心理韌性和同伴影響抵抗在親子依戀與青少年內、外化問題之間均具有鏈式中介作用。良好的親子依戀關系作為積極家庭環境資源,可以提升心理韌性,豐富的積極心理資源又增益了青少年抵抗不良同伴影響的能力,緩解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并降低了違紀、攻擊等風險行為發生的概率。相反,不良親子依戀直接影響人格特質資源的建構,個體將無法應對外部壓力,缺乏有效資源,難以抵抗不良同伴的影響,最終產生內外化問題(Smorti et al., 2014)。該結果支持了資源保存模型,說明青少年個體的積極心理資源的螺旋增益效應可以增強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抑制作用。
5 結論
(1)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具有直接影響,能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內外化問題。(2)親子依戀通過間接路徑影響青少年內外化問題,個體的家庭養育環境資源促進內部積極心理韌性資源的發展,并增益對不良同伴環境的抵抗能力,減少內外化問題。(3)親子依戀對青少年早期內外化問題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具有差異。相對于外化問題,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內化問題的影響作用更強;相對于內化問題,安全親子依戀對青少年外化問題的保護作用可通過個體的同伴影響抵抗能力得到更大的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