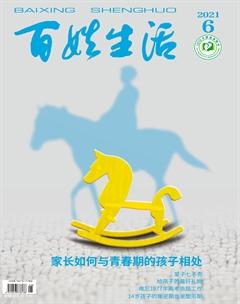他用相機記錄“世界工廠”背后的英雄
鄧瑞璇

二十年前一開始學習攝影,占有兵就將鏡頭對準了和自己一樣的打工群體。從農民工轉型成為專職攝影師,他的視角始終不曾改變。
100多萬張照片,占有兵的鏡頭記錄下二十年來廣東東莞這個“世界工廠”打工者的境況之變,也記錄了以東莞為代表的中國制造業的躍進。
將相機對準他熟悉的兄弟姐妹群體
別的可以不拿,但必須背上自己掉了漆的相機,這是占有兵出門前的“標配”。
走在東莞市長安鎮的街上,今年47歲的占有兵腳步匆匆,卻依然透過鏡頭對這個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好奇地觀察著。
“老鄉,怎么不打燒餅了?”占有兵一邊打著招呼,一邊對著路邊正在休息的燒餅攤攤主“咔咔”拍上兩張;一對情侶騎著電動車駛過,他連忙“咔咔”兩張;一個媽媽推著嬰兒車走過,他“咔咔”又是兩張。他甚至不用看取景框,托在手上,拍照速度和他的健步如飛一樣讓人目不暇接。
二十年里,占有兵拍下了100多萬張照片。他的鏡頭里,除了街頭的普通人,記錄最多的,是東莞這個“世界工廠”里無數的打工者。
1995年,退伍的占有兵從湖北老家來到廣東打工。和大量流向珠三角的農民工一樣,他渴望著“闖世界賺大錢”。
但是,很快占有兵發現,在這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地方,盡管電線桿上、招工欄里貼滿了招工廣告,但“新手”想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招的都是各式各樣的熟手,極少招普通工人。
占有兵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靠體力從千軍萬馬中“殺”出重圍得到的。
“深圳一家酒店招5個保安,來了快100號人,把停車場都站滿了。”占有兵記得,當時面試考的第一個項目是做俯臥撐,保安隊長數到“30”的時候,場上剩下的不到20個人,數到“50”時只有9個人了。
剛退伍的占有兵一口氣做了102個俯臥撐,堅持到了最后,成功被錄取。幾個月后,他跳槽去了另一家酒店,工資翻了將近一番。
隨后幾年間,占有兵又多次跳槽,干過保安,做過人事,工作不斷變動。“感覺自己完全就是隨波逐流的浮萍,失業、找工作、保飯碗,腦子里全都是為生存而戰。”占有兵說。
2000年,占有兵跳槽到了東莞長安鎮的一家電子廠,成為一名保安主管。也是在這里,他接觸了攝影。他買了一臺二手相機,自學攝影技巧。
一開始,占有兵拍照片是為了帶給老家的家人,讓他們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樣。慢慢地,他開始發現,這記錄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自然而然地,他把相機對準了自己身邊最熟悉的打工群體。
“世界工廠”和流水線上的青春
流水線上的女工、集體食堂堆放的碗筷、亮起燈的宿舍、路邊談戀愛的年輕人、廢棄的工廠大門……二十年來,一代又一代打工群體和他們的生活,都被占有兵的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
中國制造聞名全球。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東莞靠“三來一補”起家,加工制造業得到快速發展。幾十年間,林立的廠房代替了稻田和香蕉林,無數產品從這里流向世界各地。人們曾用“東莞塞車,世界缺貨”來描述其“世界工廠”的重要地位。
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遷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這背后,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務工者日復一日地打拼。他們是支撐中國制造的重要力量,但也是最默默無聞的“平凡英雄”。
“以前大家關注到打工者,往往是因為一些報道有特點的個體事件,但是很少關注他們的普通生活。我要記錄他們的真實生活給大家看,修正大家對打工者的偏見。”占有兵說,自己也是打工群體中的一員。他從觀察者的角度觀察的,也是自己的生活。
占有兵鏡頭下的打工生活,是密集的。給員工存放私人物品的柜子、集體食堂的飯碗柜、一排一排的宿舍樓、樓里的水表、整整齊齊地掛在墻上的鑰匙、陽臺上晾得密密麻麻的衣服、工作前集中在空地做早操的員工、吃飯時涌入集體食堂的人們,都是密集的。生產線上產品的工序被細分,每個員工只需要做其中一道,這樣效率最高、價值最大。“一個人可能在鞋廠里干了一輩子,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一雙完整的鞋。”占有兵說。
占有兵鏡頭下,工作之外的打工者是鮮活的。他們不是流水線上的機器,也有著豐富的生活與情感。
工業區里有很多培訓機構,給工作之外想要充實自己的人幫助。英語、會計、平面設計、計算機……“工作之外的時間還是自己的,只要你有想法,機會總是很多。”占有兵說。
如今在東莞一家科技公司做消防安全管理的吳先訓,曾和占有兵在一個工業區,他的宿舍生活也曾被占有兵收進相機中。1998年從家鄉湖南來到東莞打工,他在這里生活了22年。“來到東莞的人,很多都會改變。”吳先訓頗為感嘆,他身邊有不少初中學歷卻努力考上大專的人,為了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努力。占有兵也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后來,工業區里不少人也開始學攝影。我們都說,一個占有兵走出去了,更多的占有兵站起來。”
在這片劇烈變化著的土地上,永遠不缺少抓住機會不斷蛻變的追夢者。有的人從打工者變成了職業歌手,有的人在流水線上堅持寫作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有的人創業成功開啟人生新篇章——在東莞,這些故事隨時都在發生。
相機不離身的這些年里,占有兵目睹著東莞的巨大變化。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逐步被自動化的生產線取代,高新技術企業越來越多,流水線坐著一排排工人的情景很難再現。
珠三角之外,打工群體有了更多的選擇。他們涌向不同的地方,或者留在家里做起了電商、快遞等新興工作。工業區的招工也出現了變化,企業使出渾身解數,提高工資、安排夫妻房、宿舍裝空調、組織文化娛樂活動等,希望能留住員工。
如今,新一代的年輕人依然源源不斷來到東莞,他們開啟的是新的故事。
“照片走得比我更遠”
“如果不是拍照,現在我可能就是被工廠淘汰的農民工,回湖北鄉下種地了。”對于占有兵來說,攝影把他帶向了不曾想象過的遠方。
占有兵的作品在北京、上海、廣州、平遙、大理等國內多個城市展出。2012年,他的個展《新工人》參加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獲得新聞報道類優秀攝影師獎;2016年,他的個展《中國制造》應邀赴紐約展出。
從在博客分享被關注,到在多家媒體發表攝影作品;從作品在國內各大攝影節(展)頻頻露臉、攬下無數攝影獎項,再到赴海外舉辦個展,占有兵也創造了自己從打工者到攝影師的人生逆襲。如今的占有兵,已經是一名專職攝影師,也是長安鎮融媒體中心一名記者。
攝影對于占有兵來說,已經不只是愛好,更成為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我希望自己的照片,能系統、全面地呈現制造業打工者的常態生活,所以關注照片的歷史價值、檔案價值、時間價值、記錄的深度和連貫性。”占有兵說,他想通過自己社會紀實的專題攝影,系統地關注東莞制造業,關注打工者、工廠和工業區的生命周期變化。
“尤其是飛速發展的今天,只要有一瞬間沒有被記錄下來,很可能就會永遠留下遺憾。”占有兵愈發有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2020年疫情期間,他也沒有停下在工廠街頭拍攝的腳步。“如果我沒拍,那么疫情里人們的生活和之前相比有什么變化,就沒有記錄下來,就是不完整的。”
在拍攝的間隙,占有兵也在通過各種渠道,收集打工者曾經在工業區生存的物證、痕跡。有工廠搬遷、關閉,他聽說了,就會過去找找工廠和工人們留下的照片、書籍、員工卡、文件甚至是生產資料等物料。他還經常轉一轉二手書市場,收集一些打工者的書信和照片。
自己家盛不下了,占有兵專門租了一個小房間用以儲存。這些東西加起來有幾千斤,占有兵正在慢慢對它們進行分類整理,希望最終呈現出來一個綜合性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