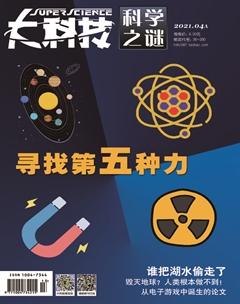動植物的抗病神技
蘇一橫

疾病是人類健康的大敵,病原體一直隱藏在四面八方,悄悄地試圖入侵人體。導致了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就提醒人類——病原體的威脅時刻存在,而且不斷地變化,人類稍有疏忽,就會經受一場浩劫。
不過,病原體本質上也是生物,它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生存和茁壯成長。所以,受疾病威脅的生物可以根據病原體的喜好來制定防御策略。如今,隨著人類開始將目光投向了疫苗、抗生素以外的下一代抗病技術,自然界很多生物的抗病妙招將會給我們帶來啟發。
蝙蝠的“免疫調控”
在古代,蝙蝠曾經很受寵愛,古埃及人就喜歡把蝙蝠吊在門口,他們似乎感覺到這種有翅膀的哺乳動物可以抵御疾病。在現代,蝙蝠卻越來越成為讓人們有些懼怕的小動物,因為人們身邊存在過的很多致命病毒——狂犬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以及新型冠狀病毒,全都曾出現在蝙蝠身上。
既然蝙蝠攜帶著那么多病毒,它們自身卻為何安然無恙呢?這就要歸功于蝙蝠獨特的“免疫調控”系統。
我們知道,免疫系統最主要的任務是檢測并對抗外來的病原體,但過激的免疫反應會造成炎癥。舉例來說,當大多數哺乳動物的細胞檢測到一種入侵病毒時,它們會釋放被稱為細胞因子的蛋白質,從而啟動一種抗病毒反應,試圖阻止病毒復制并傳播到其他細胞。這些試圖摧毀病毒的蛋白質就會引發炎癥反應,造成發燒等癥狀。有些非常厲害的病毒,比如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它們很擅長避開這種抗病毒反應,當人類感染它們之后,麻煩就來了——人體細胞將不停地釋放細胞因子,形成不可控的“細胞因子風暴”,進而產生劇烈的炎癥,損害器官,甚至導致死亡。

不過,科學家發現,蝙蝠細胞卻有著“雙重策略”,它們一方面產生強烈的抗病毒反應來進行防御,另一方面也能抑制炎癥。在免疫過程中,一種叫做干擾素的物質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它可以對病毒進行早期預警和直接攻擊,并長期保護蝙蝠體內活細胞。與人類細胞因子不同的是,干擾素對于蝙蝠和病毒雙方都相對“溫和”,既不會引發炎癥,又可以使病毒在可控、可進化的狀態下與蝙蝠細胞共存。這樣一來,蝙蝠可以持續感染非典病毒或者新冠病毒長達幾個月之久,維持自身免疫系統與病毒之間的動態平衡。
但是,科學家還發現,當病毒在蝙蝠體內的數量越積越多時,蝙蝠就越有可能將病毒排入周圍環境。因此,像砍伐森林、污染環境這樣的行為不僅會給蝙蝠帶來食物短缺等壓力,還會使病毒從蝙蝠傳給人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可見,盡管我們沒有蝙蝠那樣強大的免疫力,但通過對蝙蝠的研究,仍然有助于讓我們避免下一場潛在的大流性疾病。
蜻蜓的“納米殺菌”
不用高溫、不用消毒、不用噴藥,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就可以輕松殺滅細菌!自然界中真有這樣的殺菌高手,那就是飛來飛去、隨處可見的帶翅昆蟲,比如蜻蜓和蟬。
蜻蜓和蟬肯定不會像人類那樣使用香皂,那會對它們造成巨大的傷害,但它們纖薄的翅膀具有獨特的物理結構,可以使細菌一接觸就死亡。表面看上去,蜻蜓和蟬的翅膀平坦得像個飛機場,然而對于尺寸在微米量級的細菌來說,蜻蜓翅膀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利用電子顯微鏡,科學家發現,蜻蜓的翅膀上其實布滿了針刺狀的尖狀突起,一般有兩三百納米那么高,被稱為納米柱。當細菌停靠到蜻蜓翅膀表面時,它們實際上如同降落在了“狼牙棒”上面,細菌的細胞膜將會持續承受來自納米柱的巨大壓力,最終被拉伸或刺裂。

纖薄的翅膀具有獨特的物理結構,可以使細菌一接觸就死亡。
科學家已經通過電子斷層掃描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對納米柱殺菌過程進行模擬,發現它們特別適合殺滅一些危害人體的病菌,比如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在了解了納米柱殺滅細菌的機制后,科學家又有了下一步的任務,即,如何將模擬蜻蜓翅膀的納米柱用于設計和制造具備抗菌性能的餐飲或醫療用具。
桑葚的偽裝
植物需要保持呼吸通道的清潔和健康,就像動物一樣。植物通過葉子表面的氣孔來呼吸空氣,這些氣孔是植物維持生存所必需的器官,通常被葉面上突起的“山脊”包圍,但它們也是潛在的病原體的侵入點。
生長在南亞的喜馬拉雅桑葚常常患有白粉病(桑葉長白斑)和銹病(桑葉長銹斑),原因就在于白粉菌和銹菌很喜歡通過氣孔進入桑葉。當這兩種真菌落在葉子上后,真菌孢子發芽并放出細絲狀的管子,稱為菌絲。這些菌絲探索葉子的表面,尋找氣孔。當菌絲找到一個氣孔時,它們就進入并填充氣孔,從那里入侵到葉子的組織中,消耗營養物質。
真菌是如何發現這些氣孔的?科學研究表明,它們對葉子表面的紋理有特定的反應。銹菌能識別植物表面突出的“山脊”,并與之成直角生長,從而增加定位氣孔的機會,而白粉菌則能識別氣孔周圍特殊細胞的形狀,并以此為線索。生活在潮濕的氣候中,喜馬拉雅桑葚更容易被真菌感染。
然而,一些桑葚在它們的葉子上進化出了獨特的紋理。這些高低不平、毫無規律的崎嶇表面混淆了真菌菌絲,使其很難找到氣孔所在,而真菌菌絲不能直接穿透葉子的表面,它們必須通過氣孔進入。真菌一旦發芽出菌絲,就不能恢復孢子形態。通過掩護氣孔,桑葉會拖到真菌孢子,使其耗盡能量,在找到氣孔、進入葉子之前“餓死”。
螞蟻培養“抗生菌”
在自然界中,不同的物種之間常常相互合作,建立持久共生的關系——螞蟻、真菌、細菌之間的三角關系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早在6000萬年之前,一些螞蟻就已經開始了農業生產活動,遠遠早于人類。比如,亞馬孫叢林的切葉螞蟻懂得從植物上切下葉片,用于種植真菌。在切葉螞蟻的洞穴里,是一座真菌農場,也是自然界的一片樂土。螞蟻為真菌提供了食物和理想的生長棲息地,而真菌又是螞蟻的食物來源。
而這個和諧的局面想要持續下去,就離不開第三者——細菌的幫助。在漫長的歲月里,生命和環境一直在不斷地變化著,時常會有一些有害真菌(螞蟻無法食用)入侵或者衍生出來,這些不速之客將會破壞螞蟻辛苦種植的食物。此時,寄生在螞蟻身上的細菌就會站出來,制造各種抗生素,阻止不良真菌的生長。
科學家發現,螞蟻身上的抗生菌可以利用其DNA的不同片段來制造各種不同的抗生素。由于DNA可以提供指令,告訴細胞要制造什么樣的化合物,而抗生細菌經常使用“說明書”的不同部分,因此生產的抗生素總是不同的。其結果是,有害真菌始終無法快速形成防御系統,也就始終無法打開通往螞蟻真菌花園的“大門”。即使有害真菌偶然具備對某種抗生素的“抗藥性”,那么抗生細菌只需對DNA某些關鍵指令進行小改動,仍然可以阻止有害真菌打開“大門”。
人類很多疾病是由于感染致病細菌引起的,為了治療感染,醫生會使用一種抗生素來殺死病菌。隨著時間的推移,病菌可以學會保護自己,并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因此,人類可以學習螞蟻,也培養一些抗生菌,使病菌更難產生抗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