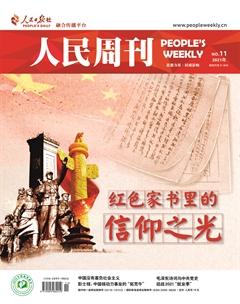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江竹筠與丈夫彭詠梧、兒子彭云合影。
【家書原文】
竹安弟:
友人告知你的近況,我感到非常難受。幺姐及兩個孩子給你的負擔的確是太重了,尤其是現在的物價情況下,以你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個甚么樣子。除了傷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決〔絕〕不會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難的日子快完了,除了這希望的日子快點到來而外,我甚么都不能兌現。安弟,的確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勝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獄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兩年坐牢的決心。現在時局變化的情況,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蔣王八的來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如〕何頑固,現在戰事已近川邊,這是事實,重慶再強也不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給它三四月的命運就會完蛋的。我們在牢里也不白坐,我們一直是不斷地在學習,希望我倆見面時你更有驚人的進步。這點我們當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話又得說回來,我們到底還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萬一他作破壞到底的孤注一擲,一個炸彈兩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這〈種〉可能我們估計的確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沒有。假若不幸的話,云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孩子們決〔絕〕不要嬌養,粗服淡飯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慶?若在,云兒可以不必送托兒所,可節省一筆費用,你以為如何?就這樣吧,愿我們早日見面。握別。愿你們都健康!
竹 姐
八月廿七日
來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談。
【時代背景】
江竹筠(1920—1949年),即江姐,曾用名江志煒、江雪琴,出生于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大山鋪鎮江家灣。1939年考入重慶中國公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系,翌年轉入農藝系。1945年與彭詠梧結婚,婚后負責中共重慶市委地下刊物《挺進報》的組織發行工作。
彭詠梧(1915—1948年),四川云陽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云陽縣委書記、重慶市委委員,負責組織宣傳工作,領導重慶學運和《挺進報》。1947年11月川東民主聯軍在云陽、巫溪發動起義,彭詠梧任聯軍縱隊政委。1948年1月16日在奉節鞍子山突圍時不幸犧牲。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萬縣被捕,被關押于重慶軍統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堅貞不屈。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北平宣告成立,11月14日,江竹筠英勇就義。13天后,重慶解放。江竹筠和戰友們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
【信仰之光】
這封信寫于1949年8月27日。當時獄中沒有筆、沒有墨,江竹筠用竹簽子蘸著棉花灰兌水調成的“墨汁”,將信寫在極薄的一張巴掌大的毛邊紙上,由同室難友曾紫霞出獄時帶出,交給了譚竹安。譚竹安,江竹筠的表弟,中共黨員,當時在重慶大公報社工作。
江竹筠在信中對革命即將取得勝利充滿了信心,甚至期待著能夠走出敵人的牢籠,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但同時也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因為窮兇極惡的敵人是什么都可能做出來的。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只有3歲的兒子,希望兒子能夠順利長大成人,繼承父母的遺志,為共產主義事業繼續奮斗。
20世紀60年代,長篇小說《紅巖》出版發行,電影《烈火中永生》上映,片中根據江竹筠的英雄事跡改編的江姐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她面對敵人的酷刑毫不畏懼,嚴守黨的秘密,對黨的信仰堅如磐石,感動了一代又一代人。
信中的云兒,指江竹筠和彭詠梧1946年所生的兒子彭云,當時在重慶上托兒所。1965年彭云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改革開放后公派留學美國,從事計算機研究。彭云的兒子彭壯壯,1974年生,在北京完成了大部分的小學和中學學業,高二時赴美讀書,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到中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