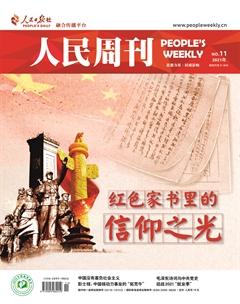界畫,于界線內超越限定
蘇丹
界畫是以建筑為主要描繪對象,以界尺為工具繪制的圖畫,在中國傳統畫史中又稱為“屋木”或“樓觀”,既是指一種繪畫的題材,同時也是指一種繪畫的技法。它最初運用于建筑圖稿,后經眾多畫家的藝術實踐,不斷豐富與完善其表現手法和繪畫技巧,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特殊的畫科。
由于時代背景、創作目的的不同和審美追求的差異,界畫在表現形式和繪畫風格上又顯現出各自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藝術風貌。
歷史上界畫的式微直至近乎失傳,與人們對它的歸類相關,也導致了界畫畫種的邊緣性。據說界畫的誕生可能出于建造目的,也就是說,界畫繪者的初心是精準,是一種工匠精神的表達和建造目的的表現。可以說,不具備匠心就不可能畫好界畫。
宋元時期的界畫曾經達到按比例放大即可指導施工的程度,具有現代工程制圖的現實效用。這一點在宋代漸興的文人畫美學的主流價值中,逐漸被排斥。此后的中國繪畫歷史中,依然偶爾有巨星闖入界畫這片逐漸被冷落的荒蕪之地,如宋代初期的郭忠恕,南宋的劉松年、李嵩,元代的王振鵬,清代的袁江、袁耀父子,現代的黃秋園,他們像流星劃過夜空,留下令人難忘的佳作,美輪美奐。
然而,界畫領域的冷僻倒是杜絕了“左顧右盼”的投機現象,敢于涉足于此的畫家必定是有備而來,雄心、知識、心性均不得缺席。一直以來界畫被歸于工藝美術的范疇,理由大概是和它的縝密工細有關。
事實也大致如此,界畫描摹建筑輪廓和造型常常使用界尺,而因界尺使用產生的直線就成為自古以來中國傳統繪畫中異質的元素。這些直線的邊緣性是個場域概念,也是個屬性概念。但匠心不等于匠氣,匠心是做事情的態度以及巧妙的心思,匠氣則是最終作品呈現出來的拘謹教條氣質。
界畫在紙面塑造的是人工環境和自然環境相交合的場域,沿用了山水畫的畫法和類似工程設計制圖的畫法,但其屬性并不是工程性的,它在自然的灑脫和人工的匠氣之間游走徘徊、權衡、控制,我以為這是界畫最迷人的地方。
在古代美術史學界,北宋郭忠恕的界畫被列為“神品”,蘇軾曾評價郭忠恕“尤善畫,妙于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其界畫作品《明皇避暑宮圖》工整細膩、筆法自然,墨色豐富,韻律感十足。文徵明亦曾不吝褒贊道:“千榱萬桷,曲折高下,纖悉不遺。而引筆大放,設色古雅,非忠恕不能也。”

《梁園飛雪圖》(袁江 繪,故宮博物院 藏)
此后,界畫在南宋亦流行一時,至元代時又卷土重來。郭忠恕的界畫對后世影響不可小覷,元代畫家王振鵬便深得其意,其作品《阿房宮圖》中對建筑的構圖處理十分巧妙,與郭忠恕的細節處理有異曲同工之妙。
清代畫家袁江、袁耀的界畫已經完全脫離了建筑設計圖的功能,作品中充溢著更多的個人情感,營造出一種可游、可觀、可居的意境。畫面使用了水墨加青綠的設色技法,清奇獨特。袁耀的《蓬萊仙境圖》中的亭臺樓閣體現出古代森嚴等級制度下的井然秩序,屋頂上的細節筆墨清晰,造型各異。對于蓬萊仙境的臆想,化為珠聯璧合的山石樹木與宮闕樓臺,畫面生成了多重有趣的空間層次。
時至當代,畫家張孝友的界畫成為中國書畫領域的一座奇峰,孤傲、獨特且難以效仿。其作品不僅將界畫的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更是開創了該畫種諸多新的觀念、境界和視覺趣味。
畫面里的宮闕樓臺還是那些飛檐微翹、氣魄雄渾的古建筑,但屋脊的鴟吻和檐下的斗拱卻精準應和了木構建筑的規制。廊腰縵回,檐牙高啄的建筑群只是形似,各抱地勢,鉤心斗角反映的是中國古代營造的環境觀和形態美學。
界畫作為一個古老的畫種,能否復興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它與當下的文化生態以及美學態度相關,應當具備一種新的姿態以體現它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