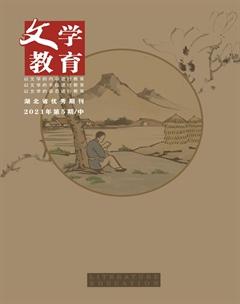高纓《達吉和她的父親》的民族意識
侯雅嵐
內容摘要:高纓的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講述了漢族生父任秉清和彝族養父馬赫爾哈對孩子達吉由相“爭”轉為相“讓”的故事,凸顯了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諧狀態。解放前,彝族奴隸主橫行霸道、冷血殘暴,他們強搶漢族父親的女兒,將她抓上涼山,又鞭打愛護養女的彝族父親;解放后,彝族父親與養女組建幸福家庭,漢族父親經歷千難萬險與女兒相認,但兩位父親因在女兒的歸屬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而產生矛盾沖突;經過眾人的調解,兩位父親最終相互理解并愿意女兒跟隨對方生活。小說通過敘述兩位父親矛盾沖突的化解過程,彰顯了漢彝兩族對共產黨的熱烈擁護與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充滿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同時,小說也是高纓的民族團結意識的顯現。
關鍵詞:高纓 《達吉和她的父親》 民族意識 民族團結
高纓在重慶文學季刊《紅巖》1958年3月號上發表了《達吉和她的父親》,并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討論。《達吉和她的父親》用日記體的形式以漢族干部李云的外來者視角,記錄了兩位父親因對孩子的愛而不愿與孩子分離,漢彝兩族父親在孩子的去留問題上產生分歧,但二人最終消除了民族隔閡與民族偏見,并愿意以犧牲個人的幸福為代價來成全對方的幸福這一事件,其中蘊含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本文試圖對《達吉和她的父親》中的民族意識做一些探討。
一.舊時代的漢彝關系
達吉被彝族奴隸主抓走淪為奴隸前叫妞妞。那天,任秉清到場上給妻子抓藥,五歲的妞妞獨自在地壩上玩耍。突然間,兩個騎馬的彝人沖下來將妞妞擄走,上了涼山。從此,任秉清失去了女兒,妞妞也成為了達吉,他們父女之間的悲劇分離由此拉開了序幕。
達吉受盡了奴隸主的虐待:她每天睜開眼睛看見的就是奴隸主兇狠殘暴的嘴臉,她推不動比她高的磨子,就被火塘里的火燒;在大雪天,她上山砍柴,砍得少了沒有飯吃,只能吃野菜喝雪水;因為羊被豹子吃了,她就被主子拴在林子里喂豹子。達吉手臂上全是奴隸主們留下的傷疤,“她心上的傷痕跟身上的傷疤一樣多呵!”[1]
馬赫爾哈和達吉一樣,也是“阿侯”[2]家的奴隸,他也遭到了舊社會的蹂躪,他本身就體現著奴隸制度的罪惡:“他凸出的前額上,刻著幾條深深的皺紋,好像是被鞭子抽打出來的;他的眼睛是細小的,微黃色的;他的背佝僂著,向火塘伸出枯枝似的手……”[3]。馬赫的外貌被苦難深深地摧殘了,昔日的痛苦在馬赫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作為奴隸,馬赫一生都沒有成家。
在封建制度的壓迫下,任秉清食不果腹,無力尋找女兒;妞妞被搶上梁山,遭遇飛來橫禍。在奴隸制度的迫害下,馬赫和達吉任打任罵、辛苦勞作,被拴鏈子,被抽鞭子,過著非人的生活。任秉清、達吉和馬赫爾哈都飽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苦難,他們都是舊社會的幸存者。作為階級兄弟,任秉清和馬赫本該惺惺相惜,但他們卻被事情的表象所欺騙而相互仇視:在任秉清眼中,達吉是被彝人搶走的,他要求達吉回到他的身邊;在馬赫眼中,達吉是自己的女兒,他不能與達吉分離。舊社會造就的痛苦留在了他們的心中,舊社會造成了骨肉分離、民族的隔閡和敵視,“……漢族與彝族自古便是兄弟,那時候不打架,不吵嘴,漢人給彝人五谷,彝人給漢人牛羊;后來漢人里出了漢官,彝人里出了奴隸主,他們就打起來了,誰都想把誰的骨頭打斷……漢官與奴隸主喝人的血,讓老百姓和‘娃子喝淚水……”[4]。漢彝本是一家,但因統治階級犯下的滔天罪行而生活于水深火熱中的勞苦百姓卻將各自的厄運歸咎于同胞。壓迫者造就的苦果讓被壓迫者吞食,民族隔閡和民族仇視由此生發。
二.矛盾沖突中的漢彝關系
《達吉和她的父親》不僅書寫了兩位父親之間為爭奪孩子而產生的矛盾沖突,還展現了擁有雙重身份的達吉的內心矛盾沖突。
任秉清是達吉的生父,他提出尋回女兒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在解放后,任秉清才擁有了尋找女兒的條件,他已經尋找了女兒一年多,走遍了涼山,也詢問了許多好心的彝胞。終于,任秉清在縣城遇到了長相酷似女兒妞妞的達吉,便“入魔”般地無憑無據地追問達吉,聲稱要找縣府幫忙尋回女兒。任秉清來到達吉所在的小村子,確認了達吉是他的女兒后,他便想將達吉帶回家。馬赫的阻攔激起了任秉清的暴怒,任秉清讓馬赫滾開,罵馬赫是蠻子,侮辱馬赫的人格。任秉清粗暴地傷害了民族兄弟的心。當達吉跟著馬赫離開后,任秉清要李云為他撐腰,并說一定要帶走女兒,不然就要到毛主席跟前去告狀。此時的任秉清被情感沖昏了頭腦,沒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任秉清沒有體貼將他的女兒撫養長大的馬赫的心情,內心被“個人主義”的思想所左右,一心想著與女兒團圓。此時,任秉清只能看到個人的痛苦與幸福,不明白中華民族是一個的道理。
馬赫爾哈是達吉的養父,他與達吉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視達吉為自己生存下去的慰藉與希望。馬赫因為達吉生父的問題“近來鬧情緒,工作勁頭不高”[5]。當被委派到村中了解農業社生產情況的共產黨員李云第一次拜訪馬赫時,馬赫對李云態度冷淡,不愿理睬。馬赫只是問李云現在漢人中還有沒有壞人,這些壞人還會不會再來欺辱彝人,搶彝人的人。李云第二次去見馬赫時,馬赫對李云比上次更甚,連狗都不為李云攆。直到馬赫明了李云不是來調查達吉的,馬赫才主動向李云打招呼,并請李云喝酒。但當任秉清突然出現,聲稱自己是達吉的父親,要把達吉帶走時,馬赫一時間無法接受這一現實。馬赫懷疑任秉清是漢人中的壞人,是來搶他們的人的,并認為李云欺騙了他。激憤的心情促使馬赫摸出匕首刺向任秉清。風波過后,李云找馬赫溝通,馬赫首先確認了李云是涼山自治州委派來的干部,不會偏袒漢人;其次說明達吉與任秉清沒有感情,達吉愿意留在自己身邊,任何人都不能強行拆散自己與達吉的家庭。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馬赫得知李云為達吉給任秉清寫信后,再次對李云毫不客氣。馬赫稱李云為“韓呷”[6],認為李云挑撥自己與達吉的關系,是從漢區來的、專為漢人辦事的漢官。馬赫威脅李云:若達吉被帶走,他也別想再在村子里展開工作了。深沉的父愛與狹隘的民族意識使得馬赫不尊重并反復無常地對待李云,進而對階級親人任秉清拔刀相向。
達吉自己在選擇跟隨哪位父親時,也是左右為難,難以取舍。達吉解答李云對于自己民族身份的疑惑時,肯定地說自己是漢人。達吉不愿意離開涼山與阿大馬赫爾哈,但她心中又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生身父親。當達吉與任秉清相認后,馬赫闖入讓達吉跟自己走。達吉對任秉清縱使百般不舍,但還是選擇與阿大馬赫回家。達吉離不開馬赫,她是在馬赫的保護下長大成人的。達吉也不愿意斬斷與任秉清的聯系,走之前對任秉清的回望包含了女兒的留戀與牽掛。三天后,達吉的情緒明顯好轉,眼神也明朗了,她堅定了要與馬赫永不分離的決心。感情的事總是反反復復,半點不由人。達吉找李云替自己給任秉清寫一封信,信中字字浸透愛意,句句寫滿思念,“你來的時候,要走大路,不要走山林里的小路,那里有豹子。你來的時候,要穿一雙好草鞋,免得石頭磨破腳;要穿一件披衫,免得雨水打濕身子。你渴了,不要喝冰冷的澗水,要到村子里要一碗熱水……”[7],表達了對父親的關懷。在之后召開的一次社務委員會中,達吉對自己的去留還是猶豫不決。馬赫體諒達吉與任秉清,他不愿他們為難,不想他們傷心。馬赫主動把達吉交給了任秉清。達吉含著眼淚,準備跟任秉清離開。豈料任秉清也與馬赫有著同樣的心境,任秉清也將達吉“讓”與馬赫。達吉這才表白心聲:她離不開涼山和彝胞們,愿意以后每年都回家看望任秉清。達吉在是跟隨生父任秉清還是養父馬赫一事上一直猶豫不決,內心也一直處于矛盾沖突中。達吉無法輕易舍棄任何一方,她心中蘊藏著民族的團結與友愛精神。
小說以飽含深情的筆調書寫了父女之情,破除了文學是政治的傳聲筒的模版。高纓以現實主義的筆法刻畫了精神創傷在心里仍舊留有陰影的人物形象,揭示了漢彝民族之間存在的民族偏見問題,正視社會改革中存在的困難,并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能性與方案。高纓對兩個家庭的書寫已經上升到了民族意識的高度。
三.新時代的漢彝關系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教育下,各族人民終將消除民族仇視,為迎接美好的未來攜手同行,為共同的社會主義事業奮斗。
李云的到來代表著黨中央對少數民族落后地區的關切、幫助與扶持。李云剛進村,了解到馬赫的情況,便急于解決馬赫的問題。李云并不只是通過口頭交流了解彝族地區的發展情況與勞動人民的生活情況,他更是身體力行地通過勞動融入到當地人民的生活中。李云三次主動登門拜訪馬赫,即使遭到冷遇,也絲毫沒有怒氣與怨言。李云聽說了達吉的悲慘遭遇后,想把達吉帶回漢族地區尋找親生父母,但他的理智壓倒了他狹隘的民族意識,他用“涼山人民翻身了,跟漢族人民同樣自由幸福”[8]的美好生活前景來安慰達吉。在面對達吉的問題時,李云充分尊重達吉的個人意愿,平等對待漢族的貧農任秉清和彝族的“鍋莊娃子”[9]馬赫爾哈,堅守“我是共產黨人,是中華各民族人民的兒子呵!”[10]的政治信仰,不偏不倚地維護并實踐著國家的民族團結政策。李云知道達吉問題的簡單性與復雜性,簡單在只要達吉與一位父親達成共識,并對另一位父親加以說服,問題即可解決;復雜在這一問題關系到兄弟民族的團結。任秉清沒能接走女兒后,揚言說李云也是漢人,要他為自己撐腰。李云當即制止了任秉清的胡言亂語。當馬赫對李云惡語相向,質疑李云違背了各民族的地位與權利平等的原則時,李云鎮定自若地表白“共產黨給我的心有多重,它便是多重!”[11]正是李云一貫的大公無私贏得了馬赫的尊重與信任。馬赫向李云敞開心扉:達吉已經兩天沒有吃過飯了,常常從夢中哭醒,口中呼喊著她的父親任秉清。馬赫懇請李云救救達吉,只要達吉能夠好起來,他愿意讓達吉走。馬赫堅硬的心軟下來,他希望李云找來任秉清,他愿意割愛讓達吉和任秉清一起生活。李云公正無私、不卑不亢的待人處事原則溫暖了馬赫,這為后來馬赫態度的徹底轉變奠定了感情基礎。李云并沒有過分意識形態化,他以一顆公正的心對待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作為一名支援民族地區發展的漢族干部,李云的一言一行都體現著黨的民族團結政策。
沙馬木呷是一名極具階級友愛與民族團結意識的農業合作社社長。沙馬對李云很是關心照顧。在達吉的問題上,沙馬一直對李云循循善誘。李云每次向沙馬發問時,沙馬都用彝族的諺語作答,沙馬讓李云自己深入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這為李云能夠融入彝胞的生活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當馬赫與任秉清第一次“短兵相接”時,沙馬社長采取強硬的態度壓制住了情緒過于激動的馬赫,他阻止馬赫對任秉清揮刀相向,并責備馬赫欺辱漢族同胞。沙馬沒有被任秉清具有侮辱性的話刺痛而怒發沖冠,反而對任秉清好言寬慰,他讓任秉清不要著急,并說一定會為他解決問題。在任秉清臨走前,沙馬大嫂還熱情款待任秉清。沙馬與李云相跟著送了任秉清二里路,一路上一直開導著任秉清。在十天后的社務委員會中,沙馬以一名具有高度黨性的會議主持人身份促進了達吉事件的圓滿解決。在會上,沙馬向在坐的各位解釋:現今的所有矛盾和困難都是舊社會造成的。馬赫和任秉清是受難者,是階級兄弟。只有毛主席才能驅散這些陰影,給予我們幸福和歡樂;只有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民族才能團結友愛。沙馬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演說感動了所有人,喚醒了他們心中的民族團結意識,他們放下顧慮,心貼著心坐在了一起。沙馬的鼓舞也使得馬赫將達吉讓與任秉清。更出乎意料的是,任秉清也愿意讓達吉留在涼山。兩位老人至此解開心結,相擁在一起。沙馬的演講“融化了橫亙在人們之間的民族隔閡和個人糾葛的冰霜”[12]。小說以沙馬社長呼喊大家坐在一起喝酒收尾,漢彝兩族人民結為了至親好友。
《達吉和她的父親》中不僅是領導人物具有高度思想覺悟,經過黨中央教育的普通群眾也不自覺地流露了民族團結意識。
達吉身為漢人,但在彝胞中長大,她兼有兩重身份,是連接兩個民族的橋梁。達吉第一次見到李云就問李云見過毛主席沒有,渴望了解漢區的建設情況,她對漢族人民的生活有著向往之情。達吉還為李云說話,幫助李云駁斥馬赫的漢人欺侮彝人的觀點,讓馬赫不要亂說話。達吉對李云有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她和李云合種包谷,還說“他們彝人太迷信”[13],承認自己的漢族身份。雖身為漢人,達吉還是一身彝族姑娘的裝扮,與彝族的兄弟姐妹相親相愛。達吉與任秉清相認后,達吉脫口而出稱呼任秉清為“阿大”[14],而不是“爸爸”,達吉對自己的彝族身份也是打心底里認同的。在馬赫與任秉清和解后,任秉清打開帶來的小包袱,讓達吉換上漢人的衣服,但馬赫希望達吉能夠穿著自己為她縫制的衣服離開,達吉自己也喜歡彝族的飾物,愛吃彝族的食物,愛唱彝族的歌。假如達吉身著彝服回到漢族地區,向漢族同胞宣揚彝族文化,這也不失為一種別樣的大團圓結局,這同樣也體現了民族的交融。最后,當達吉選擇留在涼山時,她說自己是“涼山人”[15],而沒有點名自己的民族身份,這表明達吉認同自己的雙重身份,她既是漢人的女兒又是彝人的女兒。達吉的存在說明了各民族都是相互依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馬赫在潛意識里是相信共產黨、熱愛共產黨、支持共產黨的,這也為馬赫與任秉清的和解提供了前提條件。馬赫非常崇敬毛主席。在初見李云時,馬赫本不愿搭理李云,但當他聽到李云說在夢里見過毛主席后,他也高興地附和李云,并說自己晚上做的十二個夢里都見到了毛主席。當馬赫明白是毛主席給中國帶來了光明時,他如夢初醒,“深沉的父愛和狹隘的民族意識紐結在一起,使矛盾的發展波瀾迭起,變幻莫測,扣人心弦。但是,黨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勞動人民的善良品德,終于使他們破除民族隔閡和偏見,由相爭而相讓,由拔刀相斗而緊緊擁抱了。這是勞動人民美好人性的閃光,這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勝利。”[16]
爾布等人的民族意識在小說中也有所突出。在開會時,爾布一人坐在任秉清身邊給任秉清當翻譯。另外的十幾人既不偏袒于自家人馬赫,也不敵視“搶人者”任秉清,他們相信的是社委會,是黨中央的干部。這些人擁護共產黨,贊美共產黨,堅決貫徹落實國家的民族團結政策,渴望民族團結的和諧社會環境,他們為促使兩位老父親化干戈為玉帛提供了堅強的群眾基礎。
“十七年”時期文學不乏宣揚民族團結意識的敘事作品,如瑪拉沁夫的《命名》《愛,在夏夜里燃燒》、徐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等。但《達吉和她的父親》與《命名》《愛,在夏夜里燃燒》《我們播種愛情》又有所不同。《達吉和她的父親》情節發展跌宕起伏,矛盾沖突激烈,以父女之情彰顯民族意識,以矛盾的化解宣揚民族團結意識。高纓在1960年將小說改編為電影劇本。電影削弱了小說二父爭女的矛盾沖突,轉為互為對方的幸福著想而甘愿犧牲自己的幸福,更加凸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總而言之,《達吉和她的父親》體現了高纓對新中國初期民族關系的思考,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注 釋
[1]高纓:《達吉和她的父親》,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23頁。
[2]同[1],第8頁。
[3]同[1],第5頁。
[4]同[1],第21頁。
[5]同[1],第3頁。
[6]同[1],第19頁。
[7]同[1],第19頁。
[8]同[1],第11頁。
[9]同[1],第8頁。
[10]同[1],第10頁。
[11]同[1],第20頁。
[12]馮牧:《<達吉和她的父親>——從小說到電影》,《文藝報》1961年第7期。
[13]同[1],第7頁。
[14]同[1],第15頁。
[15]同[1],第24頁。
[16]陳朝紅:《論高纓的創作》,《新文學論從》1981年第4期。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政策導向及其效應研究》(項目編號:18BZW181)和《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政策文獻的整理、研究與信息平臺建設》(項目編號:19ZDA28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