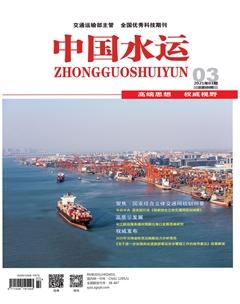防塵綠網及其環境效應研究
李鴻儒 李斗 孫衛星



摘 要:防塵綠網作為一種能有效控制散堆料場起塵與擴散的手段,近年來得以推廣,并得到關注。本文綜述了國內外防塵綠網的使用背景、應用現狀,從流行原因、技術不足等方面對防塵綠網進行了總結評述。同時著重介紹了防塵綠網老化后微塑料材料對海洋環境、土壤環境和對生物的影響,最后對防塵綠網目前存在的不足和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防塵綠網;微塑料;土壤污染
中圖分類號:X50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6—7973(2021)03-0129-04
1背景
隨著城市建設的深入,城市和道路中存在的建筑工地增長迅速,產生了粉塵問題。一方面,根據我國相關環保法規,對粉塵排放超標的工地將收取粉塵超標排污費。另一方面,堆場的粉塵污染將給周邊居民生活活動造成影響,工地揚塵污染已成為施工單位亟待解決的問題。
為了解決工地揚塵問題,考慮到成本因素,多數工地選擇使用防塵綠網。防塵綠網(見圖1)是一種治理露天堆料場揚塵污染治理的材料,廣泛運用于工程建設地短期堆場,棄土場等。
現有防塵綠網通常使用回收塑料生產,原料成分復雜,抗老化性能差,雖然其價格低廉,也有一定抑制揚塵的作用,但其老化后極易破碎,有時還需要在老化后的綠網上再多次鋪設。老化破碎后的防塵綠網回收困難,混合進入土體,進入了土壤的生態循環中。
2技術應用現狀
由于建筑工地和各類堆料場普遍存在揚塵污染,所以防塵綠網廣泛使用在口岸、儲煤場、露天料場、建筑工地(見圖2)。
3 技術缺陷
3.1 現有缺點
防塵綠網有如下缺點:
(1)防塵綠網針對揚塵有一定效果,但效果有限。
(2)防塵綠網耐用度低,在長時間暴曬及強風下容易破損,使地表的塵土重新裸露,造成揚塵污染。
(3)防塵綠網并不環保,處理防塵綠網方式多為掩埋,長時間內無法自然降解。
3.2 生態危害
防塵綠網的制作材料多是回收塑料,同時在原料中加入多種化學試劑,再經過特殊工藝制作而成。防塵綠網是土壤微塑料來源之一,在一定的條件下(如光照、溫度、輻射、氧化、機械設備磨損等)其成分會釋放到土壤中。如PBDES、用于著色的重金屬等[1-2]。此類微塑料中所含的有害物質在有機質、輻射、溫度等條件的影響下被釋放到自然界[3],通過淋溶作用進入土壤[1,4,5],對土壤生態系統構成不利影響,如塑料中所含有一些物質(如鄰苯二甲酸二酯)具有致癌、致突變及內分泌干擾等危害[6],在環境中會影響土壤微生物活性,同時可能通過植物吸收進入食物鏈對人類健康構成一定威脅[7]。
3.2.1 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2004年,微塑料的概念首次被發表于《科學》雜志關于海洋水體與沉積物中塑料碎片的論文提出。人類通過各種活動將微塑料排放到自然界,主要是生產尺寸在微米級的微塑料與大型塑料被各類物理化學作用分解而成的次生微塑料。目前,科學界對于微塑料的定義通常是指粒徑在5毫米以下的塑料顆粒,包括碎片、薄膜、纖維等。
微塑料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因尺寸小、數量多、不易降解等多種原因易被各類生物通過飲食攝取并積累在生物體內。科學家HU Riisg?rd研究了在多種貝類中2—10μm的微塑料攝取及滯留情況,研究發現,尺寸在4μm以上的微塑料完全地滯留在了生物體內,在4μm以下的微塑料也有35%—70%的保留效率[8]。
曾永平團隊[9]在前期實際測量數據的基礎上,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為主要預測因子建立了全球塑料河流入海通量模型,同時根據目前的實測數據對模型進行校準和驗證。模型估計,2018年全球主要河流的塑料年入海通量約為5~26萬噸之間。根據模型預測,全球塑料河流入海通量將在十年后達到頂點,微塑料對海洋生物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3.2.2 對土壤動物的影響
微塑料對土壤動物影響的研究時間較短,成果有限,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10],被用于研究過的有蚯蚓[10-14]、線蟲[15]及彈尾蟲[16]。在研究此類影響時,可借鑒微塑料對水域生態系統動物影響的相關研究。來源于水域生態系統的一些土壤動物,如軟體動物門、節肢動物門、線蟲、環節動物門等動物既存在于水生態系統(包括淡水與海洋)中,也在土壤生態系統中存在,由于土壤動物作為生態系統物質循環中的重要消費者,主要以植物為食,攝食習慣相似,攝入微塑料的方式也相似[17],因此,微塑料對水生態系統生物的影響,可部分適用于土壤生態系統的動物[18]在研究中可部分借鑒成果(見圖3)。
微塑料通過生物攝食等途徑進入生物體會對生物造成嚴重影響,包括生長、繁殖等等。它會導致生物體內部器官、組織物理撕裂,機體也會對入侵的異源物質產生炎癥響應,與此同時生物體還會被微塑料本身的毒性成分與吸附的帶毒物質影響。
3.2.3 對土壤微生物的影響
土壤動物表面的重金屬、污染物及病原菌會隨著土壤動物的生命活動進入土壤內部,這種轉移會造成土壤微生物區系、土壤理化性質等受到影響。目前土壤微塑料與微生物相關作用的研究方向還是空白,未見相關論文發布,只有少量的關于沿海沉積物、海洋微塑料與微生物相關作用的研究,亟需科研界對此展開研究。
3.2.4 對土壤物質循環的影響
微塑料對土壤物質循環的研究剛剛起步,研究成果有限,因此,微塑料對土壤物質循環起到何種作用與其作用機理等相關問題亟待解決。由于微塑料難于降解的特點,它可以長久留存于土壤中并開始積累,一旦土壤中存留的微塑料密度超過一定限度,對土壤乃至陸地生態系統功能及生物多樣性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
微塑料造成的土壤污染在我國尤其嚴重,1980年起,我國在一些農作物生產種植中開始使用地膜覆蓋技術,極大地增加了農業收入。由于塑料地膜應用的廣泛需求,與其清理困難、無法二次使用的特點,只能被丟棄在田間,從而造成塑料污染。污染源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大量耕作土壤均存在地膜殘留,特別是在西北部分地區農田土壤中的殘留地膜量達到了12-13公斤/畝,嚴重污染環境。
汪杰[19-20]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設計了兩種暴露模式,包括污染微塑料進入干凈土壤環境以及干凈微塑料進入污染土壤環境,研究這一過程中蚯蚓積累疏水性有機污染物的變化。同時考慮到微塑料在環境中會進一步破碎而形成更小顆粒的事實,課題組探討了微塑料顆粒大小是否對微塑料載體起到關鍵影響作用。研究表明,微塑料與污染物之間的平衡狀態是決定微塑料增加或減少污染物積累的關鍵,而微塑料對整個積累的貢獻則與微塑料顆粒大小相關。
微塑料對生物體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是微塑料本身在各種物理化學條件下產生的有毒物質,第二類是在自然界吸附的污染物,微塑料進入生物體內后,這兩類毒性物質會對生物體的生理、生化、生長、發育和繁殖產生一定影響,進而影響土壤物種的多樣性,從而影響植物的生長和繁殖、土壤物質循環。Ath-mann等 [21]研究表明,貘可以有效改善被各類植物根部所占據的地下土壤的孔隙,增加微生物的數量、密度、酶的活性、碳和養分的輸入,并為植物提供更多的營養物質(如磷),促進植物生長和土壤物質循環。 一旦像貘這樣的土壤動物因為土壤中的微塑料導致生長、發育與繁殖受到影響,土壤與地面植物之間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就會隨之受到波及,以至于整個生態系統都受到不利的影響。
4 結語
由于露天堆料場存在揚塵污染現象較為普遍,防塵綠網被廣泛應用。作為控制起塵和擴散有一定作用的工具,防塵綠網存在防塵效果一般、強度較小、有生態危害等缺點。
同時,由于防塵綠網的材料主要是聚丙烯和聚乙烯這類通過加聚反應而成的聚合物,進入陸生生態系統后,將對陸生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關于防塵綠色凈微塑料對土壤生態系統影響的研究很少。 微塑料種類繁多,其成分復雜,它們對土壤理化性質,土壤動物和土壤物質能量轉換的影響受許多環境因素的制約。 在以后的研究中,以下問題亟待解決:
(1)土壤微塑料的分離檢測。土壤結構成分復雜,土壤中的微塑料來源廣,部分大型塑料經過各種物理化學作用分解后與土壤難以分離,并對土壤生態系統構成嚴重威脅。
(2)不同粒徑微塑料顆粒的環境效應研究。需對不同粒徑微塑料顆粒對土壤生物體的毒性效應進行實驗,以確定土壤中不同粒徑微塑料的毒性機理。
(3)微塑料污染與土壤結構、成分,溫度、降雨、輻射等因素的關系。此類因素對微塑料表面性質的改變均有影響,從而導致同樣塑料在不同條件下造成的污染效應不同,因此,應在此方向上開展研究。
(4)微塑料對人體的毒性效應研究。目前此類研究成果少,且使用微塑料種類單一,因此,后續研究需進一步開展。
由現狀可知,防塵綠網技術仍有較多問題需要解決,同時由于目前防塵綠網的塑料結構對生態的影響不可預測,因此對防塵綠網的使用要十分謹慎。
綜合各種因素,建議選用天然植被措施防塵。
參考文獻:
[1] Teuten E L, Saquing J M, Knappe D R U, et al. Transport and release of chemicals from plastic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o wildlife[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2009, 364(1526):2027-2045.
[2] Rochman C M, Manzano C, Hentschel B T, et al. Polystyrene plastic:A source and sink for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47(24):13976-13984.
[3] Bising M, Amelung W. Plastics in soil:Analytical methods and possible source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612:422-435.
[4] Roy P K, Hakkarainen M, Varma I K, et al. Degradable polyethylene:Fantasy or realit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1,45(10):4217-4227.
[5] Xu S Y, Zhang H, He P J, et al. Leaching behaviour of bisphenol A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under landfill environment[J]. Environmen- tal Technology,2011,32(11):1269-1277.
[6] Erkekoglu P, Kocer-Gumusel B. Genotoxicity of phthalates[J]. Toxicology Mechanisms and Methods,2014,24(9):616-626.
[7] Sun J Q, Wu X Q, Gan J. Uptake and metabolism of phthalate esters by edible plant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5,49(14):8471-8478.
[8] HU Riisg?rd. Efficiency of particle retention and filtration rate in 6 species of Northeast American bivalves[J].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1988,45(3):217-223.
[9] Mai L ,Sun X , Xia L L , et al. Global Riverine Plastic Outflows[J]. Environmental 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XXXX(XXX).
[10] Horton A A,Walton A,Spurgeon D J,et al. Microplastics in freshwater and terrestrial environments:Evaluating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to identify the knowledge gaps and future research prioritie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7,586:127-141.
[11] Huerta Lwanga E, Gertsen H, Gooren H, et al. Incorporation of mi- croplastics from litter into burrows of Lumbricus terrestri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7,220:523-531.
[12] Huerta Lwanga E, Gertsen H, Gooren H, et al Microplastics in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Implications for Lumbricus terrestris(Oligochaeta,Lumbricida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6,50(5):2685-2691.
[13] Rodriguez-Seijo A, Loureno J, Rocha-Santos T A P, et al. Histopatho- logical and molecular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in Eisenia andrei Bouché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7,220495-503.
[14] Rillig M C, Ziersch L, Hempel S. Microplastic transport in soil by earthworms[J]. Scientific Reports,2017,7(1):1362-1368.
[15] Kiyama Y, Miyahara K, Ohshima Y. Active uptake of artificial parti - cles in the nematode Caenorhabditis elega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2012,215(7):1178-1183.
[16] Maa S, Daphi D, Lehmann A, et al. Transport of microplastics by two collembolan specie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7,22:456-459.
[17] Rillig M C. Microplastic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nd the soil[J]. Envi- 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2,46(12):6453-6454.
[18] Pao A, Duarte K, da Costa J P,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polyethylene microplastics by the marine fungus Zalerion maritimum[J].
[19]陳愛英.防風網的數值模擬[D].同濟大學,2007.
[20] Wang J , Coffin S , Schlenk D , et al. Accumulation of HOCs via Precontaminated Microplastics by Earthworm Eisenia fetida in Soil[J]. Environmental 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XXXX(XXX).
[21] Jie, Wang, Scott. Negligible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on animal fitness and HOC bioaccumulation in earthworm Eisenia fetida in soil.[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