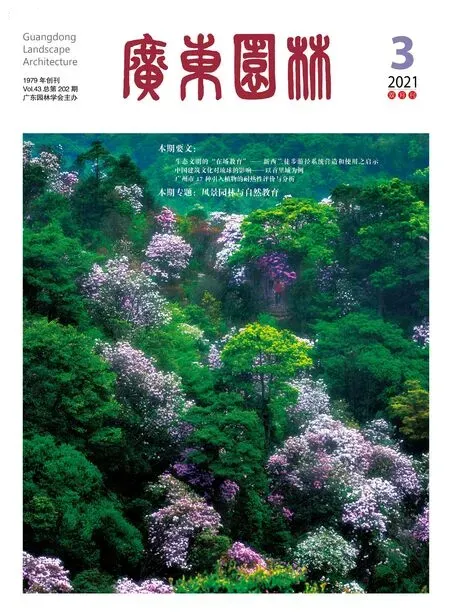廣州市17種引入植物的耐熱性評價與分析
黃嘉宇 黃頌誼 羅怡柳
HUANG Jia-yu,HUANG Song-yi*,LUO Yi-liu
植物的耐熱性是植物在高溫、高濕、干旱等多種因素影響下的一種復雜的綜合性狀。持續高溫會使植物活力降低、萎蔫或出現病蟲害,影響其正常的生長發育和新陳代謝,嚴重時會導致植物死亡。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耐熱性是植物(尤其是原產溫帶寒帶地區的引入植物)能否成功越夏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是熱帶、亞熱帶地區觀賞植物培育關注的主要性狀之一[1]。
生長環境的溫度超過植物體的耐受限度,會使植株的光合酶發生鈍化,甚至能破壞葉綠體結構[2]。這一系列反應在宏觀上表現為熱害征狀的出現[3],如葉片失水皺縮、葉色變淡、花色變淺、花量變少、植株生長緩慢等。因此植物熱害征狀出現的早晚和程度,可用于區分不同植物的耐熱性差異[4]。通過計算熱害指數能客觀地反映植株在高溫脅迫下的耐熱能力,熱害指數越高,植株耐熱性越差。
而葉面溫度和葉綠素相對含量則能從生理層面上反映植物在高溫環境下的變化。受蒸騰作用、環境濕度和葉片質地等多種因素影響,植物葉片表面溫度通常與環境溫度存在差距,其能更直接地表現出植物本身所承受的高溫,且葉片作為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對熱脅迫反應也較為敏感,容易在環境的影響下發生形態和結構上的變化[5~7]。耐熱性強的植物能在高溫環境下保持葉綠體的穩定性和完整性,保證植物體養分的正常供應;而耐熱性差的植物的葉綠體則容易在高溫條件下變形或破裂,導致植物體正常的營養供應鏈斷裂[4]。因此,葉綠素含量常被用作測定植物耐熱性的指標之一[8~9],在鐵線蓮Clematis florida[10]和蘇鐵Cycas revoluta[11]的研究中都發現其與耐熱性相關,耐熱性弱的種類葉綠素含量較低。
植物耐熱性分析除部分植物可采用單一指標(普適性較低)外[12],常采用多指標體系進行分析與評價[13~15]。 劉 易 超 等[16~18]在 對 菊 花Chrysanthemum morifolium和切花菊的研究中指出,應采用田間觀察與生理指標等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耐熱性綜合評價。許多觀賞植物包括鳶尾Iris tectorum[19]、仙客來Cyclamen persicum[5,20]、 百 合 Lilium spp.[21~22]、萬壽菊屬Tagetes植物[4]、杜鵑Rhododendron simsii[23~24]等也都有過耐熱性評價相關的實驗報道。
廣州市位于熱帶-亞熱帶過渡區,年均氣溫為20~22 ℃,高溫天氣持續時間長;最熱月7月平均溫度達28.7 ℃,最冷月為1月,平均溫度為9~16 ℃。廣州7—8月份日均最高氣溫達34℃,最低氣溫達27℃,引種植物能否成功越夏是育種工作者們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為增加廣州多年生花境植物種類多樣性,本實驗通過對17種(含種下分類單位)植物進行耐熱性分析與評價,期望篩選出適應廣州地區夏季高溫高濕環境的植物種類。
1 材料與方法
1.1 植物材料
17種引入植物分別為穗花牡荊Vitex agnus-castus、雄黃蘭(火星花)Crocosmia × crocosmiiflora、山桃草(千鳥花)Oenothera lindheimeri、紫嬌花Tulbaghia violacea、花葉紫嬌花Tulbaghiaspp.、百子蓮Agapanthus africanus、矮生百 子 蓮Agapanthus africanus‘Blue Ball’、萱草Hemerocallis fulva、柳枝稷Panicum virgatum、火焰狼尾草Pennisetum setaceum‘Fire Works’、 紅 巨 人 朱 蕉Cordyline fruticosa、彩葉朱蕉Cordyline fruticosa‘Amabilis’、 花 葉 熊 掌 木Fatshedera lizei‘Variegata’、 無 盡 夏 繡 球Hydrangea macrophylla‘Endless Summer’和麻蘭(新西蘭麻)Phormium tenax3個品種‘金邊’‘粉邊’‘青銅’。
植物材料引自昆明云上花境公司,原栽植地為云南昆明,引入后種植于廣州市陳田花園苗圃(133.29811°E,23.21470°N)。
1.2 實驗方法
于2019年7月1日—8月31日,對17種植物的田間生長狀態、葉綠素含量、葉面溫度和光照強度、環境溫濕度等指標進行觀測記錄,觀測頻率為7~10天/次,選擇晴天14:00—16:00進行觀測,采用熱害指數、葉面溫度、葉綠素含量對植物的耐熱性進行評價與分析。
1.2.1 熱害指數
現場觀測植株的熱害征狀,包括葉色、葉形、植株狀態、新芽狀況等,其分級體系參考田治國等[4]的進行調整(表1)。并根據熱害征狀計算熱害指數。

表1 熱害征狀分級表

1.2.2 生理及環境指標
葉綠素相對含量、葉面溫度采用葉綠素測定儀(TYS-B),于植株中部的葉片中段進行測定,重復3次取平均值。種植地的光照強度使用照度計(GM1020)測定,并測定環境溫度、濕度。
2 結果與分析
2.1 形態變化和熱害指數
觀測發現,大部分植物種類的葉色出現較為明顯的差異,隨著環境溫度的升高和時間的推移,花葉紫嬌花、麻蘭和紅巨人朱蕉等均出現葉色變化,葉片逐漸失綠變黃,且該征狀的出現時間和嚴重程度在不同種類之間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而葉形、新葉以及植株整體狀態3個觀測指標則相對穩定,僅個別種類出現較為嚴重的征狀,如矮生百子蓮出現明顯葉片卷曲和新葉皺縮,彩葉朱蕉出現死亡。因此,本文以葉色作為代表征狀,計算熱害指數。
根據不同時期植物的熱害指數和葉綠素含量,歸一化后采用歐氏距離進行k-均值和Ward最小方差聚類分析。根據k-均值劃分,將17種植物分為耐熱和不耐熱兩個類群(圖1)。其中,耐熱類群包括柳枝稷、萱草、雄黃蘭、穗花牡荊、山桃草5種植物,在高溫環境下性狀較為穩定,熱害征狀不明顯,熱害指數也相對較穩定,僅有小幅度波動或保持不變,大部分植物葉綠素相對含量在觀測末期出現小幅度增加,植株長勢稍差,但花期正常。其余12種植物屬于不耐熱類群,在高溫環境下熱害征狀逐漸加重,植株葉片萎蔫、黃化嚴重,出現大量枯黃和斑點,長勢極差,熱害指數持續上升,趨近于100。

圖1 Ward最小方差聚類分析與熱害指數
2.2 葉綠素相對含量變化
葉綠素是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色素,是反映植物光合作用強弱、植株健康狀態的主要指標之一[25]。試驗發現,絕大部分植物(76.5%)的葉綠素相對含量出現不同程度的降低,整體趨勢為先增后降(圖2)。不耐熱類群植物的葉綠素相對含量波動幅度較大,大部分植物的葉綠素相對含量在觀測期最后達到最低值,其中麻蘭‘金邊’、紅巨人朱蕉和彩葉朱蕉自進入7月后生長勢持續減弱,葉綠素相對含量大幅降低,麻蘭‘金邊’和彩葉朱蕉在觀測期間出現死亡,耐熱性極差。麻蘭的另外兩個品種‘青銅’和‘粉邊’在高溫環境下同樣長勢較差,葉綠素相對含量急劇降低。耐熱類群的5種植物葉綠素相對含量波動幅度較小,最大波動值小于13,整體變化趨勢接近穩定。

圖2 Ward最小方差聚類分析與葉綠素相對含量
2.3 葉面溫度與環境因子
觀測期間環境溫度與空氣濕度的變化趨勢幾乎相逆,溫度降低時濕度增加,形成“桑拿天”,導致體感溫度不變甚至上升。17種植物的葉面溫度除個別時段外均高于環境溫度(圖3),葉面溫度與環境溫度相關性極高(p<0.01),與植物種類相關性不大。在第32天即8月2日,因前幾日的暴雨,環境溫度較之前稍有下降,但空氣濕度大幅上升,植物處于“桑拿天”環境下,葉面溫度高于環境溫度,降幅較低,實際降溫效果略差于環境降溫。隨著觀測時間的推移,葉面溫度與環境溫度的差距逐漸拉大,植物體出現的熱害癥狀持續加重。

圖3 葉面溫度及環境溫度變化
觀測后期光照強度急劇增強(圖4),大大增加了植物度夏的環境壓力,對于長期暴露在高溫環境下植物的正常生長十分不利。麻蘭‘金邊’和彩葉朱蕉在此階段出現死亡。

圖4 濕度和光照強度變化
3 結論與討論
在本試驗中,17種引入植物經歷廣州最熱時期(7—8月)后,形態和生理對高溫的響應差異較明顯。根據耐熱性分析將17種植物分為耐熱類群和不耐熱類群,耐熱類群在高溫環境下性狀較為穩定,包括柳枝稷、萱草、雄黃蘭、穗花牡荊、山桃草5種植物,耐熱性良好,能在高溫高濕環境下露天生長,對廣州地區環境的適應性較強;不耐熱類群在高溫環境下容易出現葉片失綠變黃等征狀,包括紫嬌花、火焰狼尾草、百子蓮、無盡夏繡球、花葉熊掌木、矮生百子蓮、紅巨人朱蕉、彩葉朱蕉、花葉紫嬌花、麻蘭‘青銅’、麻蘭‘粉邊’及麻蘭‘金邊’12種,耐熱性一般,在高溫高濕環境下長勢較差,需要較好的養護管理條件。
受植物自身生長習性及形態影響,不同植物對同一生長環境的適應能力存在差異。為了應對高溫環境,部分植物進化出革質、蠟質、密生絨毛的葉片等性狀以更有效地反射陽光,降低自身溫度,提高耐熱性[26]。在報春花屬Primula植物中研究發現,比起耐熱性差的種類,耐熱性強的灰巖皺葉報春Primula forrestii的葉片厚度更大,葉肉細胞排列緊密,葉片表面著生大量的表皮毛和粉粒[27]。但在本研究中卻發現,不耐熱類群中的植物多為肉質葉和革質葉,這與以往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不符。進一步分析耐熱性極差的麻蘭、紅巨人朱蕉等植物,發現其原產地均為氣候較為冷涼的新西蘭及澳洲地區,與廣州高溫高濕的氣候條件相去甚遠,難以適應廣州7—8月份的高溫環境,熱害征狀均較為嚴重。而耐熱類群的植物原產地多為溫暖濕潤地區,與廣州氣候條件相對較為貼合,植物適應性較強。
綜上,廣州夏季高溫高濕且持續時間長,對植物耐熱性能力要求較高,在進行引種時應多選擇原產地氣候環境與廣州相似或耐熱性強的植物,否則即使植物能順利度夏,觀賞性狀也不明顯。不耐熱類群的植物多為原產溫帶的彩葉植物,正常狀態下觀賞性較高,在管養較為粗放的綠化帶或公園內較難存活,但在苗圃精細化管養下也可作為時令花卉來使用。
注:圖片均為作者自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