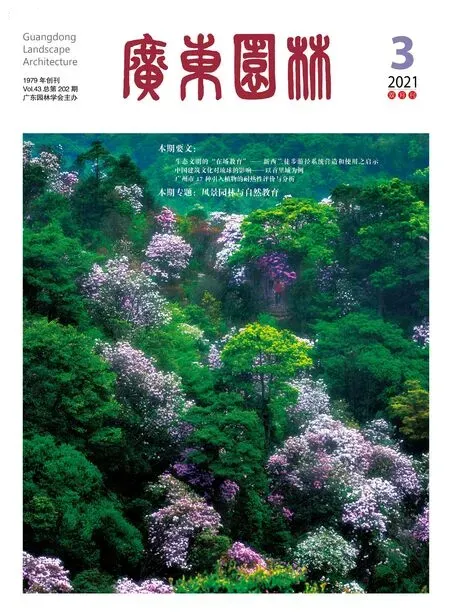消除中間尺度:對話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
采訪人/文稿翻譯:蔡淦東
文稿整理:蔡明潔
蔡淦東:最近出版的一期《新地理》雜志(2021年第11期)取名“地球之外”(Extraterrestrial),反映了設計學科的關注點延伸至外太空的最新學術思潮。伴隨著星球化研究的進行,一系列以星球為設計尺度的競賽也盛行起來,例如設計人類在火星上的棲居地。您如何看待星球議題對風景園林學科的影響?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星球是當下諸多議題的基礎語境,我對此很感興趣。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曾于三年前在哈佛設計學院進行名為“七個星球的故事”(The Tale of Seven Planets)的演講,討論了理解星球議題的難度,以及如何引導這類議題以應對氣候變化①布魯諾·拉圖爾,法國哲學家,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拉圖爾于2018年在哈佛設計學院進行關于星球化與氣候變化的演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UjXgbuBo_Q。建立在對全球化進程、氣候變化、國家意識,以及星球未來的理解上,他提出了七種思考地球的方式。我們如今更多面臨的并非地球外部而是內部的問題。我們該如何思考全球化及氣候變化,公共空間又該被如何理解?全球化一詞發明于西方世界18世紀啟蒙運動及其后的工業革命時期,是一個純粹的西方世界概念,僅代表了一個特定語境的社會現象。如今,全球化一詞的本意已不再符合當下任何一種語境,我們必須重新找到思考世界作為整體的方法,思考氣候變化,以及一切與全球化相關的后果。你提出的星球化概念在這樣的語境下尤為重要。我們需要在星球內思考和理解這樣的概念,而非宣稱人類已解決了一切問題并準備前往太空。我個人認為人類還無法適應太空環境,不應把注意力放在地球以外。關于地球以外的問題的有趣之處在于迫使我們思考人類與非人類生物均不存在的一種景觀。對我來說,這類討論更多是關于無生命景觀可能性的思考,是一種智力與美學上的練習。然而它們并沒有星球城市化理論重要,也與之關系不大。
蔡淦東:星球城市化也是發源自西方的概念。我們是否應該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西方世界之外,例如發展中國家和其他欠發達地區?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這是一個趨勢。在關于星球化議題的討論中,發展中國家與太平洋地區發生的政治沖突遠比地球以外的事物相關性強。星球化意味著對新概念的摸索以及對公共性的理解,它超越了西方思維,是一種全球尺度的理解。同時,它也意味著人類對氣候變化、政治經濟全球化以及一切相關問題的整體思考。
蔡淦東:我認為這里面有兩個趨勢,一個是全球尺度的整體性思考,另一個是深入本地進行在地性的思考。提到在地性,美國風景園林協會基金會(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2019—2020年度“研究與領導力獎”的6位獲得者在項目終期分享中,至少有三份獲獎提案都涉及到在地性的問題:深入地區與場地,與當地居民互動且傾聽其聲音,用設計的方法嘗試解決明確存在的本地問題。盡管設計地球乃至太空的熱情高漲,與之相對的對在地性議題的深入關注似乎也是當下的一大趨勢。您怎么看待這兩個看似背道而馳,但同時出現在我們專業討論熱潮當中的議題?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我同意兩個趨勢的說法,一個是探索全球化的軌跡,另一個是保持對本地特色的關注不丟失。我們在過去30到50年里看到越來越多的關于本地認同與社會公平的論調。這兩股力量正在形成互補,維持著兩者間的平衡。
蔡淦東:在學習過程中,我發現風景園林學科的尺度跨度很大。然而在最近幾年,當談論星球城市化以及本土問題時,這種尺度的跨度甚至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我認為風景園林可以擁有星球尺度的野心,但同時也需細致地觀察特定社群,建立人與其他物種以及環境之間的關系。同時從這兩個尺度入手的意圖是有益的。從這樣的立場出發,最極端的做法是舍棄中間尺度:不去關注國家、區域,和城市尺度。取而代之的,是關注最小尺度和能被控制、操作、享受以及體驗的瞬時事件。之后透過風景園林、氣候變化以及全球化的視角,把注意力轉向整體性的星球尺度及其政治經濟現象。這不一定是最有實操性的方式,也不是我所倡議的,但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話題之下的學科發展并采取相應行動,這是一個重要的嘗試。
例如,本學期風景園林設計課的主題是氣候變化與具體場地①指哈佛設計學院研究生項目2020年秋季景觀設計課(Core III)課程 From Off-Shoring to Near Shore: Littoral Landscapes at Work。。學生必須在地域尺度上思考,然后專注于傳統景觀尺度下非常具體的場地。介于兩種尺度之間,包括區域、國家以及城市的問題,均不在一開始的考慮范圍之內。我們在大尺度上理解產業更新,經濟與政策的關系,理解水文條件中的氣候變化趨勢。之后馬上轉移到小尺度問題上。所有中間尺度的事物都被放在次要的位置。這與過去20年間城市與區域規劃議題作為重點關注對象十分不同。當下面臨的情況指向一種新的空間理解模式:在最初介入時有意地忽略中間尺度而把關注度放在兩個極端尺度上。顯然這會帶來許多棘手的問題:不介入關乎國家與地區尺度會使許多人感到不適,然而我認為這是當下一種有價值且有必要的嘗試。設計從最初即可迅速地處理人類與其他生物的關系,對于本土社群或弱勢社群事關重要。同時,我們可以處理跨國界乃至星球尺度的核心大尺度問題。這是一種極具挑戰性的極端手法,我不認為人類世界是按這樣的方式構成的,因為更多的人慣性地首先關注中尺度問題。我完全同意你對兩種極端尺度的論述,這正是我們設計課目前在做的:在設計之初消除中間尺度。
蔡淦東:消除中間尺度!這是一個思考星球化與在地性的極有趣的方式。您富有煽動性的主張與我對您關于城市虛空的工作的理解相一致。在我看來,城市虛空是被主流語境與價值觀拋棄,但具有創造新型公共空間潛質的一種場所。基于全球化、資本流動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星球城市化是人類世界的一種宏觀敘事。把其投射于空間之中,可以理解為一切的公用空間都是相互連接的。這與您在《城市虛空匯編》(A Glossary of Urban Voids)②出版于2020年7月,其中文介紹文章由采訪人蔡淦東翻譯并刊登于《城市設計》期刊。一書中所認為的城市虛空是與資本積累和消費背道而馳的一種空間相悖。您是否主張城市虛空應扮演抵抗星球化并提供對公共空間替代性方案的角色?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你的理解是準確的。城市虛空是處于城市進程外部與邊緣的一類空間。我們該如何處理外部?這里面有兩個問題。首先,一部分城市虛空與社會及經濟不公平密切相關。城市虛空多產生于弱勢社區,因此針對它們的手段必須更具有實操性及符合常規,以適應資本積累的進程,從而成為有益于社區的財產。第二,更多的城市虛空與社會及經濟因素并沒有太大相關性。這種情況下,它們處于社會總體進程以外,允許著各種事件在其之中發生,這是星球化進程無法做到的,因此必須作為一種珍貴的空間類型受到保護。
城市虛空并非對星球化的抵抗,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而是對當下現實所做的空間上的隔斷,以形成一種替代式的現實。這為創造不一樣的中小尺度公共空間提供了新思路。我不認為城市虛空是為大尺度的討論而存在的;因此我們在討論星球問題時需要思考一種新的公共空間類型。我尚不清楚它是怎樣的一種空間,但它可以置于星球化進程以外。在你設置的星球化與在地性理論框架之后討論城市虛空十分有趣,因為它可被視為在地性一方的公共空間,盡管它仍然反映了大尺度的進程。在星球化一方,我們需要去尋找相應的公共空間類型,它將在氣候變化議題當中發揮著作用。
蔡淦東:最后兩個問題我希望談談疫情底下的公共空間。在一場弗蘭姆普頓(Kenneth Frampton)與北京城市建筑雙年展之間進行的訪談中①北京城市建筑雙年展聯合知識雷鋒,于2020年8月對弗蘭姆普頓進行了采訪。,他提到了視頻會議軟件Zoom作為新公共空間的可能性。他認為社會行為的自發性是公共空間的一項核心特性,而Zoom并沒有這樣的特性。同樣無法在Zoom里體現的還有人們的情緒。因此,弗蘭姆普頓的答案是否定的—視頻會議軟件不能被視作新的公共空間。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虛擬公共空間與Zoom一類的軟件或程序?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我認為媒介,尤其是移動技術在公共空間的定義上將會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Zoom作為一款有非常明確功能的具體軟件,只能被稱為交流工具,而不該被當做公共空間。公共空間作為聚集和體現社會文化公共精神的空間,其類別和特性應該十分明晰。Zoom只是為人們提供交流的平臺,和公共空間術語是完全不同的類別。
在視頻會議軟件之中,交流的是相互認識的人,或是因為某種原因必須認識的人。而在公共空間,更多的是陌生人。虛擬公共空間目前還不存在,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對于表達星球化的有趣問題。星球化需要的虛擬公共空間不再與物理場景綁定,而存在于網絡媒介之上。網絡,而并非任何一個特定的平臺,可被認為是一種公共空間。我一直思考移動技術和公共空間之間的關系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經驗:如何記錄和描述公共空間,如何進入或了解它們。透過公共空間的力量和影響,網絡世界與真實世界被連接著。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非常精確地區分虛擬公共空間與網絡社交媒介。例如,不存在“推特公共空間”,而只有虛擬的公共平臺。也許可以認為真實公共空間與網絡社交媒介是一種平衡。城市虛空可作為真實公共空間于在地性層面的一種替代性方案,至于星球化尺度,我們則需要尋找另一種建立在網絡社交媒介上的平臺。因此我們擁有了三組對應的術語:真實公共空間與網絡社交媒介,在地性與星球化,城市虛空與“未知”。
蔡淦東:我還想談談當下的公共空間。伴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和全球封鎖,人們必須逗留在家,公共空間變得多余并難以進入。一切關于公共空間的美好描述都顯得具有爭議,甚至連公用空間一詞本身也成為了危險的代名詞。盡管我們都認為疫情終將過去,但問題存在的時間比我們最初想象的要長得多,甚至將成為生活的一種新常態。您認為疫情改變了公共空間的定義嗎?新常態底下的公共空間會是怎樣的?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新語境下的公共空間正在朝個人體驗發展。公共性不再強調社區與集體,轉而成為了關于個體性的場所。然而我不認為公共空間因為疫情而經歷著極端的改變。無論是自然災害或是戰爭都有可能改變公共空間,例如使之成為臨時的避難場所。但這些是典型的臨時而非永久情況,公共空間的本質終會回歸。
蔡淦東:我最近開始關注公共空間中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不喜歡跟人過于接近,雖享受公共生活,但對于與陌生人閑聊感到不適。他們的感受在以往的公共空間設計中并沒有得到重視。然而經歷了疫情之后,個體性開始被重視,公共空間的設計應該更多地考慮到各種適用人群的需要。這是我關于后疫情時代公用空間的看法。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把公共空間用作讓人獨處的空間并非常見的做法,但絕對是公共空間應該具備的功能。允許孤獨與獨處行為的出現也是城市虛空作為公共空間的其中一種可能性。我認為豐富不同類型的體驗,包括享受獨處時光與保持自我,是對公用空間的一種富有意義的思考。
蔡淦東:感謝您接受這次的采訪并與我們分享了您的看法!
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