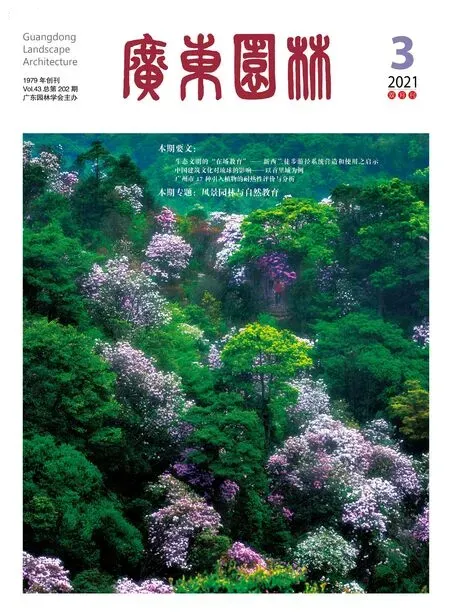基于星球化的學科思考:回顧風景園林思潮研究計劃(一)
蔡淦東
CAI Gan-dong
1 風景園林思潮研究計劃
風景園林學科在海外與國內的發展歷史和模式大不相同,近年來在海外院校中出現的新思潮一方面有跨尺度、跨學科的拓展趨勢,另一方面也有對學科歷史和設計文化的反思與探尋,均有被廣大的國內學者及從業者借鑒與討論的價值。風景園林思潮研究計劃開始于2020年8月,通過對海外風景園林學科針對尺度問題的多個前沿研究方向的分析,確定以星球化與在地性兩個極端尺度為切入點,展開系列研究,內容包括論文與訪談等。研究的重心首先放在了星球化議題的討論中心—哈佛大學設計學院。一方面,該校擁有星球城市化理論的重要研究學者布倫納(Neil Brenner)及其研究團隊城市理論研究室(Urban Theory Lab),是星球尺度議題研究與多項成果的重要基地①布倫納教授于2020年前往芝加哥大學任教,城市理論研究室也將開設在當地。但過去數年的研究仍應被認為是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重要工作成果,其影響力也留在了哈佛大學。。在研究計劃的第一篇文章《從星球化到在地性:基于克萊因四元群模型的風景園林思潮研究計劃》[1]中,筆者應用克萊因四元群模型,分析了當前海外風景園林理論思潮的兩大趨勢:一方面理論研究與實踐趨向星球化與在地性兩個極端尺度,體現在對全球宏大議題的興趣以及對本土社群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研究的手段在往外延(多學科搭接)與內拓(自身感知力探索)兩個方向發展,在強調學科協作的同時,亦從傳統與歷史中尋找自身學科文化。以克萊因四元群模型組建的矩陣產生出4個當下備受關注的風景園林思想議題,分別是星球城市化背景下的風景園林理論、新地理視角中的空間敘事、關注本土議題的風景園林研究,以及直覺導向的在地探索。
第二篇文章《星球城市化:風景園林的新理論基礎》[2]通過引入先鋒城市批判性理論星球城市化的基本觀點,提出其與風景園林學科的密切聯系,并介紹星球生態學、星球建筑學以及星球基礎設施等新概念,為風景園林學科提出新的思考角度與操作手法。在前兩篇理論建構與基本概念介紹的文章之后,研究計劃進而對四位海外風景園林學者進行了專訪,試圖從學科的不同細分領域深入探討星球化語境下西方風景園林教育中的理論發展趨勢。查爾斯·瓦爾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作為景觀都市主義理論(Landscape Urbanism)的提出者和倡導者,對學科歷史、設計文化、星球化背景下風景園林師扮演角色等問題最為關心。加雷斯·多爾蒂(Gareth Doherty)是《新地理》雜志的創辦人之一,對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理論發展沿革十分了解,并且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了星球尺度議題。耿百利(Bradley Cantrell)致力于本學科與環境科學專業的技術合作,認為技術進步與設計文化將共同指引風景園林在星球尺度下的實踐。塞爾吉奧·洛佩斯-皮內羅(Sergio Lopez-Pineiro)從更小尺度的城市虛空出發,提出星球化語境下消除中間尺度而往極大與極小尺度研究的可能性。
本文回顧四篇專題訪談的內容,整合提煉了四位學者關于星球城市化理論、地球以外探索、學科文化與本土文化、極端尺度的可能性等議題的觀點(圖1)。在此基礎上,筆者逐一對以上話題進行延展,并把其中的新思潮觀點放于四元群模型相應位置中,以檢驗理論框架的可行性,以及指導下一階段的研究與訪談方向。

圖1 四位學者基于星球化議題對風景園林學科的思考
2 “星球”理論的想象空間
星球城市化理論自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完全城市化思想(Complete Urbanization)得到啟迪,以新自由主義下的城市不均衡發展(Urban uneven development)為理論背景,經由布倫納及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等人發展成一套相對完整的城市批判理論體系。無論是中文譯名“星球城市化”,抑或其英文Planetary Urbanization,其中的“星球”一詞都使得城市研究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尺度。然而,使用“星球”二字容易讓人誤以為該理論的研究范圍在地球以外的宇宙世界,而忽略了其核心關注點仍然落在地球上的城市-鄉村地帶。從這個層面上考慮,其他的翻譯包括“全域城市化”“全球城市化”或更貼切,盡管二者均有其不適用之處[3]。但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星球”的多重含義給理論帶來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在理解星球城市化理論的時候,是否應限制于地球之內?地球以外的議題能否借由星球城市化理論探討?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是全球研究該理論最前沿的機構之一,其出版物《新地理》雜志反映了學院先鋒性設計思想方向,其主要編輯人員為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及導師。其中由布倫納帶領的城市理論研究室(Urban Theory Lab)的成員曾擔任雜志多期編輯工作。在最近數年里曾出現“后人類”(Posthuman)和“地球之外”(Extraterrestrial)的主題①“后人類”(Posthuman)出版于2018年,“地球之外”(Extraterrestrial)出版于2020年。,均指向了突破人類及地球邊界的研究,同時星球城市化理論依然是其重要的討論內容。因此,在“星球化與在地性”系列訪談中,如何理解“星球”在星球城市化理論中,以及在設計學科中的含義,成為了關鍵問題。
瓦爾德海姆認為全球意識與星球意識的覺醒來自20世紀60—70年代的太空探索運動,包括著名的 “地出(Earthrise)”照片②地出(Earthrise)照片由宇航員William Anders拍攝于1968年,被譽為最有影響力的環境類攝影作品。。如果說瓦爾德海姆認為對世界的認知能力取決于觀察方式的進步,耿百利在這個問題上則提供了更為詩意的思考。他認為人類對外太空的想象離不開一種鄉愁式的對地球的懷念,因此在眾多的科幻電影及文學作品中,均有人類帶著地球“家園”前往太空,并在地球的庇護下與外部惡劣環境抗爭的浪漫情節[4]。這涉及到地球大氣、土壤、能源等對人類的保護能力,而這與風景園林學科的工作息息相關。在《新地理》雜志的議題選擇和發展趨勢上,作為創刊人及前期主要負責人的多爾蒂認為,雜志向來以探索并突破設計學科尺度為主旨,發展立足全球的設計思想。從這一層面理解,星球城市化理論與地球之外議題似能達成一致:兩者均為跨越尺度邊界的探索,前者跨越城市區域與非城市區域,后者跨越大氣以內與大氣以外。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對探索太空的熱情持續高漲,關于移居火星等問題也從科幻虛構變成或可實現的計劃。一系列針對火星上的環境及城市建設競賽應運而生,吸引著設計師及學者的關注。然而,與探索太空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地球環境的一再惡劣,針對氣候問題的合作一再受阻。把精力投放于應對氣候危機,改善地球內部生存環境,抑或望向太空,尋求新的替代環境與庇護所,成為了全人類全學科共同的課題。以景觀人類學為研究方向的多爾蒂強調了探索太空運動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即人類唯有通過對未來的想象,才能擁有改變未來的力量。他創立的設計實驗室The Critical Landscapes Design Lab以“思考人與場所的關系”為主要研究方向,思考多尺度下的風景園林與氣候變化、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層面的關系[5]。在這個問題上,洛佩斯-皮內羅則提出了質疑,認為人類難以迅速適應外太空的生存環境,人類的注意力仍需放在地球上。在探索太空的意義問題上,他與耿百利的立場一致,均認為針對外太空環境及生物的思考既是一種美學與智力上的練習,從實際意義上也能推動人類思考地球上的問題。
主要由城市理論學家提出的星球城市化目前的關注重點并不在地球以外。但訪談中四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擴大了關于星球議題的新想象空間,體現了風景園林學科重視人類與環境關系,塑造人文精神,關注多生物環境,以及對美學的探尋等方面的思維廣度。筆者認為,風景園林的廣闊視角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星球尺度議題及人類與地球、地球以外環境的關系。
3 星球化背景下的學科協同發展
星球城市化理論由城市理論學家提出并發展,屬于批判性城市理論的范疇,無論中外,風景園林學科談論星球城市化的文章和著作仍十分匱乏。然而,該理論對非城市區域的關注,決定了其研究對象必然涉及到各類自然或人工景觀。例如,星球城市化研究學者,曾作為布倫納的博士生的Nikos Satsikis提出“全球腹地”(Hinterglobe)概念,并在與布倫納的合著的論文《操作性景觀》(Operational Landscapes)中提到了操作性景觀與全球腹地是具有農業生產、能源采挖以及運輸補給等功能的地表基礎設施,持續支撐著城市的運轉并逐漸與城市區域密不可分[6]。全球景觀已成為了前沿城市研究的對象,但由于缺乏風景園林學科的相關知識和經驗,目前已有的研究對景觀的理解不夠深入和全面,依然沿用了傳統城市視角,以人為主體看待多物種共存、多生態模式的全球景觀格局。筆者認為,風景園林學科應積極回應并參與到星球城市化的討論當中,發揮學科綜合性思考的優勢,為全球議題貢獻思想力量。關于學科如何參與到星球尺度的討論,瓦爾德海姆認為,傳統的風景園林實踐偏向于為特定場地輸出知識,在工作委任上往往處于規劃師與建筑師之后,但隨著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風景園林逐漸受到重視,風景園林師將有機會成為新時代的都市主義者,引領城市的新發展[7]。自21世紀之初倡議景觀都市主義以來,瓦爾德海姆便一直提倡景觀取代建筑作為城市發展計劃與整體框架的制定者等思想。景觀都市主義與星球城市化雖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論源起和主張,但都強調城市與景觀學科的綜合發展,消除二者間的專業邊界。兩套理論能否在星球尺度下共同發揮作用,以更好地針對全球景觀議題進行討論,是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學科研究方向。
多爾蒂以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風景園林學科的課程結構變化說明了學科在星球尺度尤其是其中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方面的探索。他提到開設于2020年秋季的理論課程Climate by Design以理解和認清風景園林學科在日益脆弱的星球中應扮演的角色為目標,并通過適應(adaptation)與緩解(mitigation)兩個側重點,分別討論氣候危機下社區的保護與復興,以及減碳策略在其中的作用①Climate by Design是哈佛大學設計學院2020年秋季學期的一門理論課程,由Jill Desimini, David Moreno Mateos, Martha Schwartz以及Emily Wsttstein指導。。該課程的主要帶課教授之一瑪莎·施瓦茨(Martha Schwartz)早于2017年便展開了關于全球氣候變化及應對的長期研究與教學,并通過與美國風景園林協會基金會(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的合作,呼吁對氣候問題的關注②瑪莎·施瓦茨于2017年始于哈佛大學開設氣候問題相關課程,并在其后的數年于美國景觀師協會(ASLA)年會中演講教學成果。。自2017年起持續兩年由施瓦茨開設的設計選修課Sequestropolis以城市為基本單元,討論如何憑借風景園林的綜合知識協調多學科共同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課程與哈佛森林研究所(Harvard Forest)合作,先在地域尺度設想了馬薩諸塞州在2060年的全域圖景,再于城市尺度以其中的大都市波士頓進行設計介入,探索多種固碳策略在城市設計層面的操作方法(圖2~3)。

圖2 波士頓紐伯里街未來固碳策略
耿百利也在訪談中介紹了他在弗吉尼亞大學開設的多學科合作實驗室Responsive Terrains CoLab,并介紹了風景園林與環境科學相關學科合作進行大尺度地域研究的可能。可以看出,借由多學科協作,以全球氣候變化與地域研究等議題為切入點,是風景園林進入并參與星球尺度討論的主要途徑。歐美各大院校均通過理論及設計課程的開設進行探索,并通過行業協會、出版物等方式發聲,加強學科在全球議題中的影響力,這一點值得國內學科借鑒與學習。
4 新時代下的學科精神與本土文化
以城市虛空為研究對象的洛佩斯-皮內羅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城市公共空間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關系。他在《城市虛空匯編》一文中指出,處于城市進程邊緣的城市虛空是被城市發展進程與時代淘汰而喪失了經濟價值、空間完整性等特質的一類空間,但也因此從資本文化的固有意識中得到解放,擁有被重新賦予力量的機會[8]。因此,被全球文化舍棄的虛空可以孕育出自發性的本土文化,而在空間實踐中對這種本土文化精神的保護和發揚正是風景園林學科在介入城市公共空間時的優勢所在。與洛佩斯-皮內羅探討的新型自發性形成的本土文化不同,更多的全球本土文化與生活習俗在全球化面前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在關于學科與本土文化的關系中,瓦爾德海姆對風景園林傳統上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性的見解,認為風景園林在歷史上更多的是為權力服務,而非創造人人皆可享受的公共資源,在對本土文化及土地的侵略問題上負有責任[9]。筆者與瓦爾德海姆進行的訪談進行于美國“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愈演愈烈之時③2020年8月,一場名為Dismantling Systemic Racism in Pedagogy and Practice的對話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進行,多個設計學科的實踐者和學者均針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發表看法。,其針對學科歷史的檢討和反思具有一定的時空局限性,但作為一次集體的反思,依然對學科的建設有積極意義。

圖3 波士頓紐伯里街未來固碳策略剖面圖
另外,瓦爾德海姆擔心,如果把風景園林的工作降低到純技術性的理解,則風景園林將在與環境科學、市政工程等其他領域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喪失了學科的核心精神:風景園林必須是一個關于文化、關于想象力,以及對新生活與工作概念思考的活動[9]。耿百利認同設計文化的重要性,同時提出對技術的新理解,即新技術的運動會形成新的設計文化與促進新的想象力,因此文化與技術二者應是相互相成的關系。在《響應式景觀》(Responsive Landscapes)一書中,他提到了運用響應式技術的實驗性項目可推動風景園林學科對不確定性與動態性研究方法的進步,而這對于風景園林作為一種與環境互動的媒介參與到地域尺度的討論中有關鍵意義[10]。耿百利在訪談中以弗吉尼亞風景園林系的教研特色為例,討論了利用數字與建模技術預測遠期趨勢,避免干擾環境及生態系統,發展自適應基礎設施等新的設計探索。
在星球化時代,承載生活記憶的本土文化在城市空間中會被重新重視,而數據采集與即時反饋等手段將會成為風景園林在全球尺度研究中的關鍵技術。瓦爾德海姆所認為的風景園林的學科精神—關于文化、想象力及生活的思考,也將在本土文化復興與新技術應用上進一步發展。
5 總結與展望:承接星球化議題的在地性探索
風景園林思潮研究計劃目前已有的兩篇文章與四篇訪談,主要圍繞星球化議題展開風景園林理論與實踐發展方向的探討。無論是就星球城市化理論所關注的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景觀二元消解議題的談論,抑或是暢想人類在地球以外建立新文明的機遇與挑戰,四位學者在跨尺度議題、都市主義、多學科協作方面均有獨到見解,為理論框架補充了重要的思想內容。更為關鍵的是,星球話題的討論在風景園林學科中并未興起,在國內相關話題的討論更為少見,這凸顯了研究計劃在豐富學科理論研究,為國內學科建設引入先鋒思想方面的意義。
第一階段的思潮研究計劃在星球化議題方面,重點放在理論與學科文化建設、地球以外的想象空間、地域尺度的多學科協作等,而在地性則討論了學科在本土問題上扮演角色、城市虛空的場所精神等議題。下一階段的工作將集中在新地理視角下空間敘事手法的變化,以及直覺導向的研究與實踐方法如何運用于在地性問題的探討。同時,研究計劃的訪談部分目前僅局限于北美東岸,尤其是在興起議題上有代表性的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新階段的研究側重點將與已完成的工作互補,共同豐富研究計劃的理論框架,搭建海外風景園林思潮與國內學科研究實踐交流的平臺。
注:圖2~3為作者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就讀期間,于Sequestropolis設計課程中的作品。指導老師:瑪莎·施瓦茨,Marcus Jat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