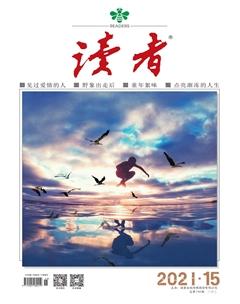我愿聽你說
劉娜
1
“離婚,離婚,我明天就和你爸離婚,這日子一天都過不下去了!”自我記事起,這種尖銳的控訴,在我們家就從未停止過。
憤怒的能量和驚恐的磁場(chǎng),從母親干瘦的身軀內(nèi),一點(diǎn)點(diǎn)往外蔓延,布滿家中每個(gè)角落,把躲在角落里的我和弟弟,一點(diǎn)點(diǎn)吞噬。
只有父親除外。他要么坐在客廳里,要么蹲在樓道里,要么在小書房里不慌不忙地畫著圖紙,沉默得像一個(gè)局外人。
對(duì)沉默不語(yǔ)的父親,我充滿了深深的同情,我甚至一次次在日記里寫道:“我爸太可憐了,他竟然從來不敢和我媽吵架。”
我12歲那年,當(dāng)母親又站在狹小的客廳里,用手拍著茶幾辱罵父親時(shí),我掙脫弟弟拽住我的手,說出那句憋了很久的話:“那你為什么不離婚呢?”
母親聽后,臉色大變。
隨即,她指著我破口大罵,說我是沒良心的東西,說我和父親是一伙兒的,說我在日記里譴責(zé)她的話,她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聽著母親翻來覆去地說著往事,第一次隱隱約約地揣測(cè):或許,母親從來沒有想過離婚。就像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jiǎn)畏矫姘l(fā)起的這一場(chǎng)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因?yàn)楦赣H從不應(yīng)戰(zhàn),所以她也從來不會(huì)贏一樣。
她的強(qiáng)勢(shì),她的指責(zé),她的控訴,她的不滿,更像是在通過喋喋不休,尋找某種平衡。這平衡是什么?年少的我不得而知。那時(shí),我只想帶著弟弟逃離這個(gè)家。
離開家最光明正大的道路,就是好好學(xué)習(xí),考上大學(xué)。
我從初一開始,就穩(wěn)居班級(jí)前5名。小我3歲的弟弟,在我的影響和教化下,也漸漸練成了“兩耳不聞家中事,一心只讀手邊書”的本領(lǐng)。
我們姐弟倆就這樣成了家屬院里“別人家的孩子”。
2
我如愿考上了離家1200公里的大學(xué)。3年后,弟弟考上了哈爾濱工業(yè)大學(xué)。我們都如愿離開了家。
我曾以為,遠(yuǎn)離母親,我就會(huì)像回歸山林的鳥兒一樣,身心自由,毫無牽掛。然而,事與愿違。
母親隔三岔五給我打電話,憤怒的語(yǔ)氣形成刺耳的聲波,在我的耳邊聒噪:“你爸天天加班,家中靜得掉根針都能聽見!”“我頭疼得要死,整夜整夜失眠,怕是活不了幾天了……”
我漸漸變得像父親一樣,無論她說什么,都不回應(yīng)。有時(shí),我強(qiáng)忍著憤怒,把電話放到床頭,任由她自說自話。
與此同時(shí),我的情感世界也如同沙漠地帶。
“你不配戀愛。”“你結(jié)婚也不會(huì)幸福的。”“你看看你爸媽多么不幸……”這些念頭就像植入我記憶的某種密碼,一次次向我叫囂。
我覺得自己要樂觀,要積極,要勇敢去愛,要做一個(gè)樂觀敞亮的人。但真實(shí)的我,總是陷入消極逃避的情緒中,不愿和任何人有親密聯(lián)系。
這種撕裂感,在我弟弟那兒有增無減——自成年起,他就宣布自己是不婚主義者。
我堅(jiān)定地支持他。
3
大學(xué)畢業(yè)后,我進(jìn)入國(guó)企上班。工作4年后,我買了房子。我忽然想有個(gè)自己的家,想過那種“有人為你立黃昏,有人問你粥可溫”的平凡生活。
一次偶然的機(jī)會(huì),我認(rèn)識(shí)了宋先生。他是技術(shù)男,在省研究所上班。他清瘦,寡言,嚴(yán)謹(jǐn),不茍言笑,做事認(rèn)真,踏實(shí)靠譜。
認(rèn)識(shí)9個(gè)月后,我?guī)蜗壬丶摇?/p>
父親甚是歡喜,拿出徒弟們孝敬他的茅臺(tái),和宋先生推杯換盞。
母親把我拽進(jìn)廚房,強(qiáng)忍著一臉的嫌惡,說出了這輩子我都沒法忘記的一句話:“我看他,和你爸一個(gè)德行!”
那一刻,我如遭五雷轟頂。“我爸有什么不好?他這輩子最錯(cuò)誤的事兒,就是娶了你!”
我氣憤地將一把綠油油的菠菜扔進(jìn)水池,憤然離開。
不管怎樣,我已經(jīng)長(zhǎng)大,我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說了算。
不久后,我和宋先生結(jié)婚。一年后,我們有了孩子。
伴隨孩子的到來,問題接踵而至,我終于一點(diǎn)點(diǎn)體會(huì)到:逃脫母親的“詛咒”,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

4
宋先生業(yè)務(wù)能力很強(qiáng),賺錢也不少,沒有不良嗜好,但他還是一次次把我逼進(jìn)崩潰的深淵。
孩子出生后,婆婆來幫我們帶孩子。我產(chǎn)后抑郁,婆媳矛盾讓我不知所措。
宋先生不會(huì)安撫婆婆,更不懂寬慰我,下班后索性躲到書房里,以加班之名玩游戲。
他甚至住在書房,對(duì)孩子的哭喊聲,女人的爭(zhēng)吵聲,置若罔聞。
孩子7個(gè)多月時(shí),我下班回來,發(fā)現(xiàn)孩子發(fā)高燒到41攝氏度。我抱著孩子一邊打車,一邊給他打電話,電話通著,他卻始終不接。
在醫(yī)院,我抱著孩子跑上跑下,又是輸液又是抓藥。
從醫(yī)院回來,推開門看見他躲在書房里,一邊吃外賣,一邊玩游戲。
我放下熟睡的孩子,跑進(jìn)書房抓起他的電腦,狠狠地摔在地上:“離婚!”
當(dāng)我清晰有力地說出這兩個(gè)字時(shí),竟然嚇到了自己。仿佛這兩個(gè)字,根本不是出自我的口,而是來自那遙遠(yuǎn)深刻的記憶,來自另一個(gè)熟悉又陌生的人。
那一刻,我看著沉默的宋先生,像個(gè)孤獨(dú)的影子,彎腰去撿摔爛的手提電腦,不回應(yīng),不反抗,不理會(huì),更不安撫。
我突然放聲大哭——他像極了我父親。
他和父親一樣,逃避一切矛盾,放棄所有反抗,害怕直面沖突,將兩個(gè)人的紛爭(zhēng)變成妻子一個(gè)人的抱怨;他和父親一樣,沉默、冷漠,而他的麻木和隱忍,讓妻子的抱怨顯得那么荒唐可笑。
他扮作受害者,卻是真正的殺戮者。他殺戮的不僅有我們的愛情,還有夫妻之間本該有的正向而健康的溝通。
時(shí)至今日,我活成母親的翻版,在疼痛的輪回里,被明晃晃的冷暴力,逼迫得無處躲藏。這時(shí),我才發(fā)現(xiàn):沉默,也會(huì)殺人,且殺人于無形。
5
我不想成為另一個(gè)母親。我決定和宋先生談?wù)劇?/p>
在某個(gè)深夜,孩子熟睡之后,我走進(jìn)宋先生困守的書房。
我從我的童年,聊到我的苦讀;從我的青春,聊到我的抑郁;從我父母相處的模式,聊到我和宋先生的結(jié)合;從我重蹈母親的覆轍,聊到宋先生和父親如出一轍;從我和我弟的逃離和哀傷,聊到我們孩子的當(dāng)下和未來……
我哭了,宋先生也哭了。
他的童年,并不比我好多少。他是在父母爭(zhēng)吵中長(zhǎng)大的孩子。不同的是,在他們家,父親是那個(gè)一言不合就動(dòng)手的人,而母親是那個(gè)被打罵的沉默者。
宋先生曾發(fā)誓今生絕不成為他父親那樣的男人。他活成了父親的反面,卻未能收獲想象中的幸福。
他對(duì)沖突的逃避,對(duì)矛盾的恐懼,對(duì)溝通的障礙,皆因?yàn)樗麅?nèi)心里住著一個(gè)害怕爭(zhēng)吵的小孩。
“我們都是受傷的小孩,但我們不能只當(dāng)受傷的小孩,因?yàn)槲覀円呀?jīng)有了自己的小孩。”我將宋先生攬入懷中。
一次溝通,無濟(jì)于事。
結(jié)婚5年,孩子4歲,我們終于找到了相處之道:可以吵架,可以發(fā)怒,可以互損,可以就事論事說問題,但誰都不許用冷暴力傷害對(duì)方。
話說開了,規(guī)矩立了,疙瘩解了,大部分需求都能得到回應(yīng),我們反倒越來越平和。
人前寡言的宋先生,開始在我面前喋喋不休。我也漸漸發(fā)現(xiàn),說話有人聽,吵架有人應(yīng),出招有人接,需求有人懂,是多么舒暢的一件事兒。
我漸漸放下對(duì)母親的怨憎,開始主動(dòng)給她打電話,聽她嘮叨。我從母親蒼老而沙啞的聲音里,第一次聽出了她的孤獨(dú),以及對(duì)愛的渴求。
6
2018年夏天,父親被確診患有甲狀腺癌。
我認(rèn)為這和他一貫逃避隱忍的性格有關(guān)。他看似從不回應(yīng)母親的詰難,但從未躲過他們之間的任何一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
父親手術(shù)后,母親嫌棄我們不會(huì)照顧,在醫(yī)院里和我大吵一架,然后逼著我們回到省城。
她一個(gè)人擔(dān)負(fù)起照顧父親的重任,包括之后的數(shù)次治療。我知道,母親怕耽誤我們的工作,怕孩子沒人照顧。我更知道,她離不開父親。
2020年夏天,父親身體逐漸康復(fù),我?guī)е⒆踊氐嚼霞摇?/p>
母親和父親從家屬院搬出來,在郊區(qū)買了一個(gè)院子。他們種了一些蔬菜,喂了10多只母雞,還養(yǎng)了一對(duì)鸚鵡。
“來這里,都是你媽的主意。”某個(gè)涼風(fēng)習(xí)習(xí)的傍晚,父親一邊給鸚鵡喂食,一邊對(duì)我說。
“爸,你恨我媽嗎?”我看著院子里新栽的幾棵果樹,還有“咕咕”叫個(gè)不停的母雞,突然問父親。
父親沉默了,就像他過去60多年里,一貫的模樣。
我站起來,準(zhǔn)備進(jìn)屋。
父親忽然說:“我對(duì)不起你媽,我以前不該那樣對(duì)她,我……”
我的淚,忍不住地往下掉,止都止不住。
正在廚房里做南瓜餅的母親,聽見我的哭聲,拎著搟面杖出來,對(duì)著父親一陣怒吼:“你造了什么孽?”
這一次,父親沒有沉默,而是說:“我給閨女道歉哩……”
我本來只想在家待3天,結(jié)果待了10天,用光了全年的公休假。
我?guī)е⒆踊氐轿倚r(shí)候生活的老廠區(qū)和學(xué)校,陪著父親回老家給爺爺奶奶上墳,還帶著母親去看望在縣城生活的小姨。
母親依然愛發(fā)脾氣,但父親開始反擊,明確提出意見,表達(dá)不滿和抗?fàn)帯?/p>
看著他們倆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我忽然感到心安。
不知道是不是父母的改變也影響了弟弟。35歲時(shí)還宣布獨(dú)身的弟弟,在36歲生日時(shí),忽然宣布要結(jié)婚。
我們經(jīng)歷了那么多紛亂爭(zhēng)吵、誤解傷害、病患疼痛,總算沒有走散。
我們學(xué)會(huì)了溝通,學(xué)會(huì)了回應(yīng),學(xué)會(huì)了傾聽,學(xué)會(huì)了訴說,也學(xué)會(huì)了理解和包容。
我們終于懂得,所謂愛,不過是:我在。我在聽。我愿聽你說。我想對(duì)你說。我們一起想辦法。
(熠 涵摘自微信公眾號(hào)“閑時(shí)花開”,李小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