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絲綢之路書法史”研究的倡啟
——評《從長安到敦煌:古代絲綢之路書法圖典》
◇ 徐清
2020年正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20周年,國內外學界紛紛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敦煌學”以及“絲路學”理應擁有更為開放的胸襟和視野,體現跨學科、多元化、綜合性的特征。張永強編著的《從長安到敦煌:古代絲綢之路書法圖典》作為浙江省主題出版規劃項目,在這一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出版,自然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絲綢之路書法史”研究:圖典背后的指向
《從長安到敦煌:古代絲綢之路書法圖典》是筆者所見的第一部以“絲綢之路書法”命名的圖典。作者在綜述文章《近代西北考察探險與絲綢之路書法史的構建》中,明確提出構建“絲綢之路書法史”的設想。該圖典在選題和立意上,已凸顯其學術價值。
20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十余年,“絲綢之路”研究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熱點,其下的分類研究如絲綢之路經濟史、貿易史、文化史等已取得諸多成果,藝術史領域如服飾、陶瓷、樂舞、音樂等也有專門的著述,相較而言,“絲綢之路書法史”的研究尚顯匱乏。王素先生在為該圖典所撰《序言》中特別肯定了這一選題的意義:“20世紀以來,絲綢之路一直受到關注,天馬之路、苜蓿之路、葡萄之路、金錢之路、白銀之路、香藥之路、法寶之路、書籍之路、寫本之路,各種研究不斷涌現,可惜未見有人提出書法之路。可見絲綢之路書法史是一個值得期待的選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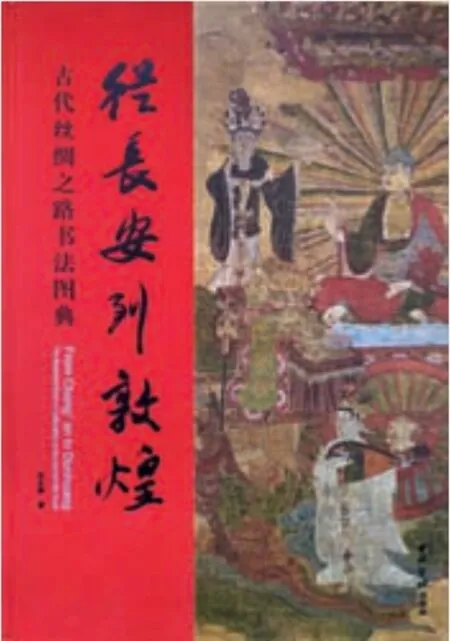
張永強著《從長安到敦煌:古代絲綢之路書法圖典》,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出版。
這部圖典以絲綢之路上的兩個重要交匯點長安、敦煌為紐帶,向西跨越關中、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和青海西藏地區,向東遠至日本、朝鮮等國,對周秦兩漢至隋唐宋遼的各類書法經典、遺跡,進行分門別類的整理,體現出充分的時空跨度和學科跨度,兼有人文、藝術的多重視野和多層次性。全書依據地域分塊和時間線索,劃分為七章,前四章重在長安及周邊地區的書法,后三章分別是河西走廊、西域和敦煌的書法,分量幾占全書之半。對書跡的選取和介紹,既有書體、書風、書寫者角度的考察,也有政治、宗教、民族、文字等層面的觀照。部分章節專列唐代的景教、祆教、摩尼教書跡,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書跡和留學生墓志,西夏文字碑刻和經卷等,還特別收入了反映中西文化交流和古代民族如“昭武九姓”等的在華石刻、書跡,以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寫本(含梵文、粟特文、焉耆文、龜茲文、突厥文、回鶻文等),體現出作者對古代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交融匯通、本土宗教和外來宗教的互為影響、中原地區與各少數民族的錯綜關系等重要問題的思考,內容豐富而具啟發性。
二、以圖鑒史:圖典本身的價值
關于絲路書法史的相關資料和歷史,作者有十數年的學術積累,前期已完成《敦煌莫高窟題記匯編》(合著,2014)、《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碑帖善拓集萃》(執行副主編,2015)、《中國書法全集·兩晉南北朝寫經寫本卷》(分卷副主編,2013)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書法全集·隋唐五代寫經寫本卷》(分卷主編)等成果,本可以自撰絲綢之路書法史的專著,但是作者卻不急于一時,而以圖典的方式呈現于讀者。對于“絲綢之路書法史”這一新研究領域而言,資料整理和圖錄出版尤為重要。圖錄的開放性、直觀性、資料性,為后續的研究奠定基礎,為更多學者的參與提供可能。
除了作為基礎文獻的重要價值之外,圖典中對各類載體、形制的書跡以及出土遺址、環境的直觀呈現,更切近于古代書法的實際存在和自身特性。古代絲路書法史不完全是“純藝術(書法)”的歷史,其間文字、書法的樣態和審美風尚不只存在于碑版、墓志、法帖、寫經,還大量通過各種生活用品、器物、壁畫題記、官私文書等得以呈現和傳播。絲綢之路的各種物質及物質交流,承載了文字書法和藝術元素,物的豐富性進一步促生了書寫的豐富性。
該圖典選用的圖版豐富、精良,說明文字簡練、嚴謹,圖文均寓含學術性,給讀者帶來賞與讀的愉悅。以第五章河西走廊書法為例,下設七節內容,涵蓋了漢晉簡牘、璽印,有“五涼書風”之稱的十六國石塔刻經、壁書、造像記,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珍貴文書寫本,以及與吐谷渾、吐蕃、西夏等政權有關的書跡,立體地展現了佛教東傳、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與漢唐文明交融的歷史印跡。下設各節也盡可能以最具代表性的書跡和圖像相配相輔,如第七節西夏遺蹤,共收列十二種資料(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文工匠監督印、西夏文首領印、力士志文支座像、靈芝頌殘碑、西夏仁宗李仁孝陵碑篆額、西夏王譯經圖、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草書佛經長卷、上師像唐卡、拜寺溝方塔塔心柱墨書題記、蓮池書院西夏文經幢),而所用圖版也是精心安排,突出感通塔碑的碑首(西夏文篆書)、碑陽(西夏文楷書)、碑陰局部(漢文楷書)、碑陰額字(漢文篆書)、2004年新發現的碑座,還增以涼州大云寺(即護國寺)舊影、清代學者張澍畫像,以及1909年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發掘出土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書影(1932年,羅福成參照這部骨勒茂才編的西夏文、漢文雙語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將感通塔碑的西夏文譯成漢文發表)。顯然,作者對感通塔碑的被發現和研究情況非常了解,選取的十二種實物資料也充分證明西夏文曾參照漢文創造了篆、楷、行、草書,這對我們考察漢文書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三、實物、史籍、新著三結合:篤志踐行的可貴
作者為編撰這部圖典,親自實地考察,熟悉典籍文獻,注重考古新發現和國內外研究成果。這三方面的結合,其實就研究方法本身來說并不新鮮。20世紀初期以來,王國維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的“一時代之學術,必有新材料與新問題”,治學之士需“預流”“入流”而非閉門造車的治史觀念和方法,已為學界所熟知,但是落到每一項具體的歷史研究,難度在于實際運用,在于研究者的篤志踐行。
圖典后附作者《沿著漢唐的足跡—絲綢之路書跡考察之旅》一文,敘述2018年炎夏的考察經歷,也僅是其十數年研究的冰山一角。為了收集大量第一手資料,作者先后數次對絲綢之路沿線的史跡進行實地考察,親自拍攝,記錄所見,足跡遍至新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吐魯番吐峪溝、阿斯塔那、海昏侯墓、青海湖海晏城遺址、雷臺漢墓、武威、敦煌懸泉置遺址、炳靈寺、麥積山、涇川南北石窟寺、莫高窟、西夏王陵、西安漢唐書法遺跡等。同時,作者參考了近百年來國內外敦煌學、書法學研究的大量著作和圖錄,及時跟進近年來的最新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聯系故宮博物院、陜西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多家機構,根據真跡、善拓、舊拓原件拍攝,在十余萬張圖片的基礎上進行篩選。其治學的虔誠和勤勉,令人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