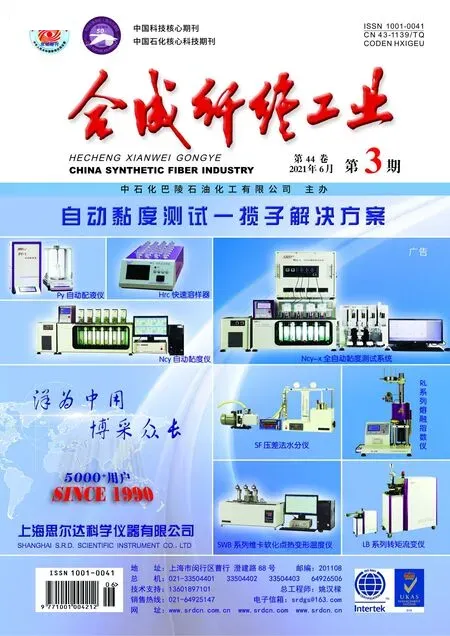建筑增強用聚丙烯腈纖維的抗凍融性研究
王艷麗,張 磊,鄒黎明,徐 靜
(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高性能纖維及制品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1620)
混凝土是世界范圍內使用量最大的土工建筑材料,具有強度高、剛度大、耐用性好、價格低廉等優點[1],因此被廣泛應用于橋梁[2]、公路[3]、堤壩[4]、高速[5]、隧道[6]等領域,但傳統的混凝土存在抗拉強度低、韌性差及脆性大等缺點,其應用前景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近年來利用纖維來提高混凝土的韌性,改善混凝土的抗滲、抗裂、抗沖擊及抗疲勞性能成為研究熱點[7-8]。目前,聚丙烯腈(PAN)增強纖維、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增強纖維和聚丙烯(PP)增強纖維常用來增強混凝土[9],但是相比于PET增強纖維和PP增強纖維,PAN增強纖維具有更強的力學性能、耐酸堿性能及更優異的耐日曬性能,在土工建筑領域的應用前景更加廣闊[10]。
高溫、凍融、海水侵蝕等多種特殊環境會直接影響纖維改性混凝土的耐久性。在我國許多嚴寒及高原等地區,潮濕、浸水飽和環境中的纖維改性混凝土受溫度正負交替變化的影響,其內部的自由水因溫度降低發生結冰并導致體積增大,當體積膨脹力無法緩解時其內部就會產生拉應力[11];纖維改性混凝土內部溶液隨溫度升高解凍,但由于結冰引起的膨脹仍存在,導致增大的空間吸收更多水分,其內部的孔隙水會產生滲透壓、靜水壓和水中鹽類結晶壓等;此凍融過程不斷循環和積累,從而引起混凝土疲勞應力,導致其表面剝落、內部疏松開裂,發生凍融破壞現象,所以增強纖維的抗凍融性是影響纖維改性混凝土耐久性能的一項重要指標[12]。
作者選用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試制的建筑增強用PAN纖維改性混凝土,模擬混凝土配置時的凍融環境[13],分析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凍融循環處理前后結構和性能的變化,并與PET增強纖維、PP增強纖維的抗凍融性能進行對比。
1 實驗
1.1 原料
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牌號為2018-05-#3,0.68 dtex,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產;PET增強纖維:3.27 dtex,江蘇恒力化纖股份有限公司產;PP增強纖維:6.97 dtex,江蘇耀華塑料有限公司產;純水:上海環琪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產。
1.2 設備與儀器
Nicolet 6700型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美國Thermo Fisher公司制; D/max-2550型18 kW轉靶X射線衍射儀:日本Rigaku公司制;TG 209 F1型熱重分析儀:德國耐馳儀器制造有限公司制;XQ-2型單絲纖維強伸度儀:上海新纖儀器有限公司制;ASK-DW-40-116型冷凍箱:深圳市艾斯科儀器設備有限公司制。
1.3 凍融循環實驗
參照GB/T 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長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試驗方法標準》中的方法[14],將纖維放入盛水的試樣盒中,置于溫度為(-20±2)℃的冷凍箱中冷凍12 h,然后取出在(25±2)℃ 的室溫環境中融化12 h,此為1次凍融循環過程;將纖維進行90次凍融循環,然后從試樣盒中取出纖維于50 ℃烘箱內烘干至恒重。
1.4 分析與測試
紅外光譜(FTIR)分析:利用傅里葉紅外光譜儀對凍融處理前后纖維的化學組成進行分析,掃描波數為1 000~4 000 cm-1,掃描次數為32,分辨率為0.09 cm-1。
X射線衍射(XRD)分析:利用XRD測試纖維的結晶度(Xc)和晶區取向度(fc)。光源為CuKα,電壓40 kV,電流150 mA,掃描速度20(°)/min。纖維的Xc根據分峰的譜圖按式(1)計算,fc按式(2)計算,晶粒尺寸(D)按Scherrer公式計算見式(3),晶面間距(d)根據布拉格方程計算見式(4)。
(1)
(2)
D=Kλ/Bcosθ
(3)
d=nλ/2sinθ
(4)
式中:ΣIc為結晶部分的總衍射積分強度;ΣIa為非晶部分的散射積分強度;B為譜圖中第i峰的半高峰寬;K為Scherrer常數,取0.89;λ為X射線波長,為0.154 1 nm;θ為入射X射線與相應晶面的夾角;n為衍射級數。
熱重(TG)分析:利用熱重分析儀對纖維的熱穩定性進行分析,測試在氮氣保護下進行,流量控制在20 mL/min,測試溫度為30~500 ℃。
力學性能:按GB/T 14337—2008《化學纖維短纖維拉伸性能試驗方法》[15]測試單絲的拉伸強度和初始模量。
抗凍融性:按GB/T 50082—2009 《普通混凝土長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試驗方法標準》方法,計算凍融循環處理后纖維的強度損失率(?Fc),見式(5)。以?Fc表征纖維的抗凍融性,?Fc越大,抗凍融性越差;?Fc越小,抗凍融性越好。
(5)
式中:FA為經凍融循環90次后的纖維拉伸強度;FB為未經凍融循環的纖維拉伸強度。
2 結果與討論
2.1 FTIR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凍融循環處理前,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FTIR中2 242 cm-1和1 732 cm-1處分別出現第一單體丙烯腈(AN)中氰基(—CN)的伸縮振動特征峰和丙烯酸甲酯中羰基(CO)的伸縮振動特征峰,其中—CN伸縮振動特征峰強而尖銳[16]。

圖1 凍融循環90次前后纖維的FTIRFig.1 FTIR spectra of fibers before and after 90 freeze-thaw cycles1—凍融循環90次;2—凍融循環前
從圖1還可以看出:經凍融循環90次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FTIR中未出現新的特征峰且主要吸收峰的峰強、峰形和峰位未發生變化,說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化學組成在經過凍融循環后未發生變化;凍融循環處理前,PET增強纖維的FTIR中1 250 cm-1和1 105 cm-1處出現C—O的伸縮振動峰、1 715 cm-1處出現強而尖銳的峰為酯基中CO的伸縮振動峰[17];經過90次凍融循環后,PET增強纖維的FTIR中主要吸收峰保持不變且未產生新的吸收峰;凍融循環處理前,PP增強纖維的FTIR中2 920 cm-1附近出現的多重吸收峰是由甲基和亞甲基的伸縮振動疊加作用導致的;經過90次凍融循環后,PP增強纖維的FTIR中未產生新的吸收峰且各特征峰峰形、峰位和峰強未發生變化。由此可見,建筑增強用PAN纖維、PET增強纖維和PP增強纖維的化學結構不受凍融環境的影響。
2.2 XRD分析
3種纖維在凍融循環處理前后的XRD圖譜如圖2所示,根據XRD圖譜計算得到3種纖維的Xc、D、d和fc見表1。從圖2和表1可知:凍融循環前,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XRD圖譜中在2θ為17°和29°附近出現兩個衍射峰,22°~27°處出現彌散峰,說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存在非晶結構,為兩相準晶結構[18],其中2θ為17°附近處出現較強的衍射峰是由PAN大分子鏈上的側基(—CN)規整排列引起的,2θ為29°附近處出較弱的衍射峰是由大分子片狀結構單元的等距離有序平行排列引起的[19];經過90次凍融循環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XRD圖譜中2θ為17°附近衍射峰的峰形趨寬,Xc和D略有增加,fc有所下降,Xc增加2.6%,fc下降0.8%;經凍融循環90次后,PET增強纖維的XRD圖譜中在2θ為17.4°,22.5°,25.7°處出現的衍射峰的峰強趨弱,峰形變寬,Xc和fc稍有下降,分別下降1.9%和0.9%,表明凍融循環90次后PET增強纖維的聚集態結構基本保持規整;而PP增強纖維經凍融循環90次后在2θ為14.1°,16.9°,18.5°,21.5°處出現的各衍射峰強度、峰形和峰位都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但Xc和fc略有下降。由此可見,凍融環境可使各增強纖維的超分子結構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進而影響纖維的力學性能。

圖2 凍融循環90次前后纖維的XRD圖譜Fig.2 XRD patterns of fibers before and after 90 freeze-thaw cycles1—凍融循環90次;2—凍融循環前

表1 凍融循環前后纖維的超分子結構參數Tab.1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fibers before and after freeze-thaw cycle
2.3 TG分析
混凝土容易在高溫環境下發生爆裂,這是由于混凝土內部較低的滲透性致使受熱時產生更高的蒸汽壓力而導致。因此,研究凍融環境對纖維熱穩定性的影響十分必要。3種纖維凍融循環前后的TG和微商熱重分析(DTG)曲線見圖3。

圖3 凍融循環90次前后纖維的TG和DTG曲線Fig.3 TG and DTG curves of fibers before and after 90 freeze-thaw cycles— —凍融循環前; --- —凍融循環90次
從圖3可知:凍融循環處理前,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最大熱分解溫度(Tmax)為305.3 ℃,此時失重率為5.0%,而經凍融循環90次后其Tma為300.3 ℃,失重率為3.5%,其原因是大分子鏈規整性較好,纖維的fc較高,所以凍融環境對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熱穩定性幾乎不產生影響;凍融循環處理前,PET增強纖維的Tmax為426.3 ℃,此時失重率為51.20%,而經凍融循環90次后其Tmax為423.1 ℃,失重率為49.36%;凍融循環處理前,PP增強纖維的Tmax為301.0 ℃,此時失重率為61.45%,而經凍融循環90次后其Tmax為300.5 ℃,失重率為60.44%。由此可見,建筑增強用PAN纖維、PET增強纖維和PP增強纖維的熱穩定性幾乎不受凍融環境的影響。
2.4 力學性能和抗凍融性
從表2可知,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經凍融循環90次后,其拉伸強度有所下降、初始模量有所增加,拉伸強度由1 269 MPa降至1 221 MPa,?Fc為3.8%,初始模量由17.2 GPa增至18.5 GPa,增幅為7.56%。這是因為經過凍融循環90次后,PAN纖維的晶區取向度有所降低,所以PAN纖維的拉伸強度略有降低。結合FTIR分析,相比普通PAN纖維,1 732 cm-1處的吸收峰峰強明顯偏弱[20],表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中的共聚單體含量少,PAN纖維大分子規整性好,剛性強,因此冷脆性效應明顯,大分子在外力作用下形變小,使纖維在低溫下可以保持力學性能[21]。根據文獻[22],PAN纖維同樣出現了隨著溫度降低而初始模量提高的現象,這是由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在(-20±2)℃的冷凍環境下分子鏈被凍結,在低于其玻璃化轉變溫度的(25±2)℃下融化,此時的大分子鏈還未來得及完全解取向,所以其模量有所提高[23]。

表2 凍融循環前后纖維的力學性能和抗凍融性Tab.2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freeze-thaw resistance of fibers before and after freeze-thaw cycle
從表2還可以看出:PET增強纖維經凍融循環90次后,其拉伸強度由原來的1 141 MPa降至1 121 MPa,?Fc為1.8%,初始模量基本未發生變化,這是由于PET增強纖維大分子鏈具有高度規整性,且含有苯甲酸基團,剛性大,經凍融循環90次后,超分子結構基本未發生變化,因此PET纖維初始模量在凍融循環后基本未發生變化;PP增強纖維經凍融循環90次后,其拉伸強度從原來的679 MPa降至653 MPa,?Fc為3.8%,初始模量由原來的6.1 GPa降至5.7 GPa,降幅為6.56%,這可能與PP纖維的結晶度和晶區取向度降低有關[24]。
綜上分析,經凍融循環處理90次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PP增強纖維和PET增強纖維的拉伸強度都有較好的保持能力,從評判耐抗凍融性能的?Fc看,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和PP增強纖維的?Fc大于PET增強纖維的?Fc,但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包括拉伸強度和初始模量在內的綜合力學性高于PP增強纖維和PET增強纖維。凍融循環90次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拉伸強度為1 221 MPa,約為PET增強纖維的1.1倍、PP增強纖維的1.9倍;凍融循環90次后其初始模量為18.5 GPa,約為PET增強纖維的1.4倍、PP增強纖維的3.2倍。由于PAN大分子鏈段在低于玻璃化轉變溫度的情況下不能運動,纖維表現出良好的剛性,因此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在凍融循環處理后具有突出的模量保持優勢,將使纖維混凝土在受荷時,作為增強體的纖維形變小,可有效提高混凝土受力后的應力傳遞效應,通過纖維與混凝土界面傳遞給纖維的應力高,從而可以更好地發揮纖維在混凝土受載時的應力分散作用,提高混凝土的耐受力[25]。
3 結論
a.凍融循環90次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PET增強纖維和PP增強纖維的FTIR中無明顯的新吸收峰出現,主要特征吸收峰的峰強、峰形和峰位基本未發生變化;凍融環境對3種增強纖維的化學結構和熱穩定性幾乎無影響,但可使3種增強纖維的超分子結構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進而影響纖維的力學性能。
b.凍融循環90次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包括拉伸強度和初始模量在內的綜合力學性高于PP增強纖維和PET增強纖維。凍融循環90次后,3種增強纖維的拉伸強度有所降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拉伸強度為1 221 MPa,約為PET增強纖維1.1倍、PP增強纖維的1.9倍;凍融循環90次后建筑增強用PAN纖維的初始模量有所提高,為18.5 GPa,約為PET增強纖維的1.4倍、PP增強纖維的3.2倍,而PET增強纖維的初始模量基本不變,PP增強纖維的初始模量略有降低。
c.從評判抗凍融性能的?Fc看,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和PP增強纖維的抗凍融性能相當,略低于PET增強纖維,但建筑增強用PAN纖維在低溫環境中具有優異的模量保持優勢,可以更好地提高混凝土在凍融循環環境中的耐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