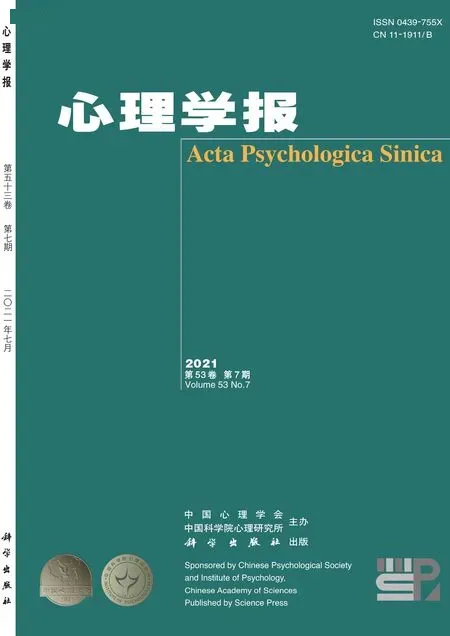攻擊動機對特質憤怒與反應性攻擊關系的中介作用:一項縱向研究*
李 芮 夏凌翔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認知與人格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重慶 400715)
1 問題提出
攻擊指存在傷人意圖的傷害行為反應或傾向(Anderson &Bushman,2002;Buss &Perry,1992)。根據動機的不同,可以將攻擊劃分為反應性攻擊和主動性攻擊(Dodge &Coie,1987;Wang et al.,2020)。反應性攻擊又被稱為敵意性攻擊,是個體用帶有敵意與憤怒情緒的傷害行為來對感知到的激惹或威脅進行反應的行為或傾向(Dodge &Coie,1987;Smeijers et al.,2018)。路怒、激情殺人和自衛反擊等是其典型表現。反應性攻擊給受害者(Hammock et al.,2015;Martinelli et al.,2018)和攻擊者(Babcock et al.,2014;Crick &Nelson,2002)都會帶來損害,而且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的危害、影響因素和形成機制都有明顯差異(Dambacher et al.,2015;Hubbard et al.,2010),因此很有必要專門探索其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攻擊產生的機制,發展攻擊理論,并做針對性的預防和干預。
人格是公認的影響攻擊的重要因素(Ferguson &Dyck,2012;Tackett et al.,2014)。其中,特質憤怒是一種受到廣泛認可的反應性攻擊的易感性人格因素,有學者還專門提出了特質憤怒與反應性攻擊的綜合認知模型(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ICM;Wilkowski &Robinson,2010)。但是到目前為止,特質憤怒對反應性攻擊的縱向預測作用及其背后的心理機制仍不是很清楚。因此,本研究嘗試在已有理論和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特質憤怒與反應性攻擊的縱向關系及其背后的中介機制。
1.1 特質憤怒和反應性攻擊
特質憤怒指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到憤怒的傾向,是一種相對穩定的人格特質(Spielberger et al.,1999)。橫斷面調查顯示,特質憤怒與反應性攻擊的相關顯著(Bondü &Richter,2016);實驗研究也發現,在低激惹且飲酒的條件下,特質憤怒可以顯著預測個體在泰勒攻擊范式中的反應性攻擊行為(Giancola,2002)。在總結以往研究和理論的基礎上,特質憤怒和反應性攻擊的綜合認知模型(Wilkowski &Robinson,2010)提出,敵意解釋、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是特質憤怒影響反應性攻擊的中介變量。
雖然已有研究在特質憤怒和反應性攻擊的關系方面做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工作,但仍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發展。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之前的研究多采用橫斷面調查法和實驗法,還缺乏對特質憤怒與反應性攻擊關系的縱向研究。第二,在中介機制方面,雖然綜合認知模型指出了特質憤怒引發反應性攻擊的認知路徑,但是目前尚未見到揭示特質憤怒引發反應性攻擊的動機路徑的理論和研究。如上所述,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的區別在于動機的不同,因此,從動機角度才能更好地揭示特質憤怒引發反應性攻擊的心理機制,并與人格影響攻擊的一般中介機制區分開。這對于揭示反應性攻擊產生與形成的基本心理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并對指導反應性攻擊的預防和干預具有實踐意義。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特質憤怒預測反應性攻擊的動機路徑。
1.2 反應性攻擊的動機
反應性攻擊的動機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敵意性動機,指個體在敵意、憤怒或恐懼等情緒的驅動下,想要通過傷害行為來報復激惹者、消除威脅或保護自己的需要或傾向。其是由威脅或激惹刺激引發的報復與防御性動機(Anderson &Bushman,2002;Smeijers et al.,2018),包括認知和情緒兩個基本成分。敵意性動機是反應性攻擊區別于主動性攻擊的特有動機(Crick &Dodge,1994,1996;Dodge &Coie,1987)。
敵意歸因偏向是敵意性動機的主要認知成分(Crick &Dodge,1994,1996;Dodge &Coie,1987),指在模糊情境中將他人的行為意圖解釋為有意傷害自己的認知反應或傾向(Crick &Dodge,1994)。社會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SIP;Crick &Dodge,1994,1996)提出,敵意歸因偏向是引發反應性攻擊的主要認知因素,且與主動性攻擊的關系不大,是反應性攻擊的特有動機。這一觀點已經獲得了大量研究的支持(e.g.,Babcock et al.,2014;Wilkowski &Robinson,2010)。據此可以認為,敵意性動機這種反應性攻擊的獨特性動機通常是個體在對他人的激惹意圖做敵意歸因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敵意歸因偏向可以作為敵意性動機的代表性因素。
反應性攻擊的另一種動機是道德準許動機(Lagerspetz et al.,1988;Lagerspetz &Westman,1980),指想要避免、減少或消除道德對攻擊等不道德行為潛在的或現實的抑制作用的需要或傾向。其通常是個體想要或正在從事傷害他人等不道德行為時,為了減少道德壓力和內部沖突而產生的一種道德性動機(Bandura,1999)。道德準許動機是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的共同性動機,因為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都會涉及傷人意圖及行為(Anderson &Bushman,2002;Wang et al.,2020),這通常與個體或社會的道德準則矛盾,就會引發心理沖突,為了恢復心理平衡,解除道德抑制,進一步驅動攻擊行為,個體就會產生道德準許動機。換句話說,道德準許動機就是一種想要避免、減少或消除攻擊行為帶給自己的道德壓力(如,因攻擊行為而受到良心或社會的譴責),想為自己的攻擊行為提供道德上的合理性的需要或傾向。
道德推脫是道德準許動機的主要認知成分,指將傷害行為認知重構為良好的或應當的,以幫助個體擺脫道德上的自我懲罰或控制(Bandura,1999,2002)。其既是一種道德認知,也是一種道德動機,個體通常都會通過道德推脫來獲得道德準許(Bandura et al.,2001;Caprara et al.,2014;Pornari &Wood,2010)。根據認知失調理論(Festinger,1957)和道德推脫理論(Bandura,1999,2002)的觀點,當個體因受到激惹而產生攻擊意圖時,就會出現諸如“傷害行為有必要”與“傷害行為不道德”的認知沖突,為了恢復認知平衡,幫助個體順利實施攻擊行為,人們就會出現道德準許的需要,并以道德推脫的方式表現出來。因此,道德推脫可以作為道德準許動機的代表性變量。
綜上所述,反應性攻擊產生的動機包括敵意性動機和道德準許動機兩種,兩者共同推動了反應性攻擊的產生和發展。敵意性動機和道德準許動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響。因為敵意性動機促使個體通過傷害行為來進行報復或防御,傷害行為通常都存在道德風險,這就可能會引發個體的道德準許動機,以減少道德壓力和內部沖突。與此同時,道德準許動機可能會幫助個體將自己的傷人意圖合理化,這可能就會增強個體的敵意性動機。
1.3 特質憤怒影響反應性攻擊的動機路徑假設
基于以上分析,首先,我們假設特質憤怒可以通過以敵意歸因偏向為代表的敵意性動機來推動反應性攻擊的形成與發展。這一假設涉及到了特質憤怒與敵意歸因偏向以及敵意歸因偏向與反應性攻擊的關系。
特質憤怒能夠促進敵意歸因偏向的觀點已經獲得了以往研究的支持(e.g.,Gagnon et al.,2016;Veenstra et al.,2017)。特質憤怒會影響敵意歸因偏向的原因可能有兩個。第一,特質憤怒會促使個體對環境和他人進行負性評價(Hazebroek et al.,2001),而對模糊的激惹情境中他人行為和意圖的敵意性解釋就屬于一種負性評價。第二,特質憤怒的個體在面對威脅相關的信息時會有感知偏見(Smith &Waterman,2003),特質憤怒也被發現與敵意性社會線索的選擇性注意有關(Wenzel &Lystad,2005;Wilkowski et al.,2007)。據此可以推測,特質憤怒會促使個體在模糊情境中更多注意到敵意性線索,并對他人做負性評價,因而也就更容易將他人的行為意圖解釋為敵意的。敵意歸因偏向會導致反應性攻擊是社會信息加工模型的一個重要觀點(即當個體認為別人對自己有敵意時,其就會試圖采用攻擊來報復他人),并獲得了不少研究的支持(e.g.,AlMoghrabi et al.,2018;Thomas &Weston,2019;Wilkowski et al.,2015)。例如,經過敵意歸因偏向訓練的被試在實驗任務中的反應性攻擊水平顯著提高(AlMoghrabi et al.,2018;Wilkowski et al.,2015)。可見,特質憤怒會增加個體對他人的行為或意圖進行敵意性解釋的可能性,敵意歸因偏向則會進而增加個體在遭遇激惹或威脅后進行反應性攻擊的頻率或可能性。
其次,我們認為特質憤怒可以通過增強以道德推脫為代表的道德準許動機來推動反應性攻擊的形成與發展。這個觀點包括了特質憤怒可以增加道德推脫和道德推脫可以促進反應性攻擊兩個推論。
一般攻擊模型(Anderson &Bushman,2002)指出,攻擊相關的人格因素如特質憤怒會影響個體的道德辯護和非人性化等心理活動。道德辯護和非人性化是道德推脫的兩種機制。這可能就是特質憤怒可以促進道德推脫的原因。我們認為道德推脫可以影響反應性攻擊是因為:第一,已有大量研究顯示,道德推脫會增加身體攻擊、言語攻擊和社會攻擊等多種形式的攻擊(Anderson &Bushman,2002;Wang et al.,2017),這些攻擊形式大多都涉及到反應性攻擊;第二,如前所述,道德推脫會減少道德系統對攻擊行為的抑制作用,因此也可以減輕個體在進行反應性攻擊時的道德壓力,從而利于個體做出反應性攻擊行為。可見,特質憤怒會促進個體進行認知重構,將自己的反應性攻擊合理化,以減少道德壓力和心理沖突,增強的道德推脫又推動了反應性攻擊的形成與發展。
綜上所述,特質憤怒可能會通過增強反應性攻擊動機(即敵意性動機和道德準許動機)來提高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反應性攻擊的可能性或頻率。敵意歸因偏向和道德推脫則是這兩種動機的代表性變量。
1.4 本研究
本研究擬通過對來自5 個省市的大學生的3 次時間間隔為6 個月的縱向調查來考察特質憤怒對反應性攻擊的縱向預測作用,以及敵意性動機(以敵意歸因偏向為代表)和道德準許動機(以道德推脫為代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此外,根據上述的敵意性動機與道德準許動機可以相互影響的觀點,我們假設敵意歸因偏向和道德推脫是相互預測的,是特質憤怒預測反應性攻擊的兩種中介因素。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一項大型的聯合追蹤調查。本研究變量的調查是基于反應性攻擊的動機模型。
該調查使用整群抽樣法,施測對象為來自北京、重慶、貴州、廣西和四川五個省市共5 所高校的本科生。初次施測共獲得被試1100 名,平均年齡為19.00 ± 0.99 歲,年齡在16.67~25.17 歲之間,每隔6 個月進行下一次施測,總共收集了3 次數據。最終獲得在本研究關注的變量上有效的被試1007人(71.1%為女性,28.9%為男性),保留率為91.55%。對流失與保留的被試在特質憤怒、敵意歸因偏向、道德推脫、反應性攻擊和主動性攻擊上的得分差異進行檢驗的結果表明,流失與保留被試在時間點1 的特質憤怒 (t
(1098)=–0.55,p
=0.583)、敵意歸因偏向(t
(1097)=1.16,p
=0.246)、道德推脫(t
(1098)=0.66,p
=0.510)、反應性攻擊(t
(1098)=–0.63,p
=0.532)和主動性攻擊(t
(1098)=1.11,p
=0.266)上的差異均不顯著,說明被試不存在系統性流失問題。該研究通過了西南大學心理學部倫理委員會的審核。2.2 研究工具
2.2.1 特質憤怒
采用Spielberger 等(1999)編制的狀態?特質憤怒量表(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STAXI-2)中的特質憤怒分量表測量特質憤怒。該問卷共10 個題目,如“我脾氣暴躁”。問卷采用李克特4 點計分,被試需根據自己的真實想法,選擇“1(幾乎從不)”至“4(幾乎總是)”。計算項目均分,分數越高代表特質憤怒水平越高。在國內研究中,該量表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侯璐璐 等,2017)。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該量表的單因素結構對本研究數據的擬合良好:χ=3.354~6.994,df
=2,χ/df
=1.677~3.497,RMSEA (90% CI)=0.026~0.050 (0.000,0.092),CFI=0.995~0.999,TLI=0.986~0.996,SRMR=0.008~0.012。在本研究中,該量表在3 個時間點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是0.78、0.82、0.83。2.2.2 敵意歸因偏向
采用Dillon 等(2016)編制的字詞句子聯想范式敵意量表(The Word Sentence Association Paradigm-Hostility Scale,WSAP-Hostility)的敵意歸因偏向分量表測量敵意歸因偏向。該分量表共有16 個題目,如“有人在你的面前摔門 侮辱的”,要求被試判斷每一個句子和后面出現的詞語的相關程度。量表為李克特6 點計分,1 代表“完全不相關”,6 代表“非常相關”。計算項目均分,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于進行敵意歸因。該量表已經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權方英,夏凌翔,2019)。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該量表的單因素模型對數據的擬合良好:χ=7.996~ 9.370,df
=2,χ/df
=3.998~4.685,RMSEA (90% CI)=0.055~0.061 (0.019,0.102),CFI=0.995~0.996,TLI=0.985~0.989,SRMR=0.008~0.011。在本研究中,該量表在3 個時間點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7、0.89、0.92。2.2.3 道德推脫
采用Caprara 等(2009)編制的公民道德推脫問卷(Civic Moral Disengagement Questionnaire,CMD)測量道德推脫。該問卷共有32 個題目,如“用強硬措施讓那些討厭的人安靜下來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被試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量表為李克特5 點評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計算項目均分,分數越高代表道德推脫的水平越高。該問卷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方杰,王興超,2020)。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該量表的單因素結構對數據的擬合良好:χ=6.458~7.935,df
=2,χ/df
=3.229~3.968,RMSEA (90% CI)=0.047~0.054 (0.009,0.096),CFI=0.997~0.998,TLI=0.992~ 0.994,SRMR=0.006~0.008。在本研究中,該問卷在3 個時間點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2、0.91、0.93。2.2.4 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
采用Raine 等(2006)編制的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來測量反應性攻擊和主動性攻擊。該量表共有23 個題目,其中11 個題目用于測量反應性攻擊(如“因為正當防衛而還手打人”),12 個題目測量主動性攻擊(如“為了顯得很酷而打群架”),要求被試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調查采用了李克特6 點評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6 代表“完全符合”。計算項目均分,分數越高代表攻擊水平越高。在國內研究中,該量表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權方英,夏凌翔,2019)。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該量表的二因素模型對數據的擬合良好:χ=3.235~7.117,df
=2,χ/df
=1.618~3.559,RMSEA (90% CI)=0.025~0.051 (0.000,0.097),CFI=0.997~0.999,TLI=0.992~ 0.998,SRMR=0.004~0.010。在本研究中,該反應性攻擊分量表在3 個時間點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4、0.87、0.87;主動性攻擊分量表在3 個時間點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0、0.95、0.95。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實驗主試為經過培訓的研究助理,在獲得了被試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施測,被試被要求完成包括上述4 個問卷在內的一系列問卷,之后填寫人口統計學變量。回答完全部問卷后由主試當場收回,被試獲得一定金額的報酬。相鄰兩次施測的時間間隔為6 個月,一共收集了3 次數據。
2.4 數據處理與分析
研究采用SPSS 20.0 和Mplus 7.0 對數據進行分析。未能參加全部的3 次調查,承認未認真作答以及規律作答的被試數據被刪除。首先,使用SPSS 20.0 進行描述統計、相關分析以及共同方法偏差檢驗。使用Mplus 7.0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為了簡化模型和提高模型擬合度,對題項進行項目打包處理,所有變量均使用隨機打包法。使用全息極大似然估計(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對非正態數據和缺失值進行處理。采用抽取5000 次的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方法檢驗潛變量模型的中介效應。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因為本研究的數據均為大學生的自我報告,因此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顯示,在3 次測量中,第一因子的解釋率分別為19.01%、21.06%、23.26%,均小于40%的臨界值,因此本研究的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2 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本研究涉及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皮爾遜相關結果如表1 所示。3 個時間點的特質憤怒、敵意歸因偏向、道德推脫、反應性攻擊和主動性攻擊兩兩之間均存在顯著正相關。

表1 特質憤怒、敵意歸因偏向、道德推脫、反應性攻擊、主動性攻擊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
3.3 交叉滯后模型分析
首先,我們構建了包含3 個時間點的特質憤怒、敵意歸因偏向、道德推脫和反應性攻擊的交叉滯后模型。在逐步刪除不顯著的路徑之后,最終獲得的交叉滯后模型可以擬合數據:χ=3652.634,df
=1091,χ/df
=3.348,RMSEA (90% CI)=0.048 (0.047,0.050),CFI=0.916,TLI=0.909,SRMR=0.056。圖1 的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性別后,特質憤怒(T1)可以預測敵意歸因偏向(T2) (β=0.10,p
=0.003)和道德推脫(T2) (β=0.12,p
< 0.001),敵意歸因偏向(T2) (β=0.11,p
=0.001)和道德推脫(T2) (β=0.09,p
=0.007)可以預測反應性攻擊(T3),道德推脫(T1)可以預測敵意歸因偏向(T2) (β=0.10,p
=0.001),敵意歸因偏向(T2)可以預測道德推脫(T3) (β=0.09,p
=0.005)。Bootstrap 分析的結果顯示,敵意歸因偏向(T2) (ab=0.01,p
=0.026,95% CI=0.001~0.020)和道德推脫(T2) (ab=0.01,p
=0.033,95% CI=0.001~0.021)在特質憤怒(T1)對反應性攻擊(T3)的預測中的間接效應顯著。
圖1 特質憤怒、敵意歸因偏向、道德推脫和反應性攻擊的交叉滯后模型
其次,我們將模型中的反應性攻擊替換為主動性攻擊后再次進行了交叉滯后分析,結果顯示,特質憤怒、敵意歸因偏向和道德推脫縱向預測主動性攻擊的路徑均不顯著。
最后,我們對道德推脫和主動性攻擊進行了3個時間點的交叉滯后分析,結果顯示,道德推脫(T1)可以顯著預測主動性攻擊(T2):β=0.08,p
=0.022。4 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在控制性別后,特質憤怒(T1)可以間接預測12 個月后的反應性攻擊,這一結果與以往的橫斷面研究(Bondü &Richer,2016;Wang et al.,2017)與實驗研究(Parrott &Zeichner,2002;Wilkowski et al.,2007)獲得的結果相符。不過,據我們所知,目前還沒有關于兩者縱向關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為特質憤怒和反應性攻擊的關系補充了來自縱向研究的證據。此外,我們還發現,道德推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縱向預測主動性攻擊,但特質憤怒和敵意歸因偏向則不能縱向預測主動性攻擊,這為相關變量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證據。
4.1 敵意歸因偏向的中介作用
圖1 結果顯示,特質憤怒可以預測6 個月后的敵意歸因偏向,這一結果與以往實驗研究發現的特質憤怒能夠預測敵意歸因偏向的結果相符(Gagnon et al.,2016;Hazebroek et al.,2001;Wilkowski &Robinson,2007),并支持了一般攻擊模型(Anderson &Bushman,2002)的基本觀點,即人格特質可以作為個體輸入變量影響攻擊相關的認知。據我們所知,未有研究揭示特質憤怒與敵意歸因偏向的縱向關系,因此本研究為該領域提供了新的證據。特質憤怒能夠預測敵意歸因偏向可能主要是因為特質憤怒會促使個體傾向于對事件進行敵意性的認知加工(Veenstra et al.,2018),因此,在模糊的情境中,特質憤怒可能會使個體傾向于從消極角度對感知到的激惹和挑釁進行解釋,將他人的行為或意圖解釋為敵意性的。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敵意歸因偏向能夠跨時間預測反應性攻擊,但不能縱向預測主動性攻擊。這一結果與之前的研究一致(Gagnon &Rochat,2017;Martinelli et al.,2018)。例如,敵意歸因偏向可以預測1 年后的包括反應性攻擊在內的長期性的攻擊行為(Dodge et al.,2015)。敵意歸因偏向能夠預測反應性攻擊可能主要是因為敵意歸因使個體傾向于采取攻擊反應來對感知到的激惹(如他人所致的傷害、威脅和挫折等)防御、報復或者反抗(Gagnon et al.,2016)。
本研究的結果還顯示,敵意歸因偏向(T2)在特質憤怒(T1)對反應性攻擊(T3)的預測中起到中介作用。這一結果支持了我們的假設,同時也符合一般攻擊模型(Anderson &Bushman,2002)和特質憤怒與反應性攻擊的綜合認知模型(Wilkowski &Robinson,2010)的基本觀點。這提示,特質憤怒會增加個體在模糊情境中對他人行為意圖進行敵意歸因的頻率或可能性,并進而導致個體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激惹或威脅情境時更頻繁或更傾向于做出反應性攻擊。
4.2 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
圖1 的交叉滯后模型分析的結果顯示,特質憤怒可以縱向預測道德推脫。這可能是因為特質憤怒會影響個體對不道德行為相關信息的認知加工,即促使個體改變道德標準,將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不道德行為解釋為合理或道德的。這一結果支持了我們的研究假設,發展了特質憤怒功能的研究,提示特質憤怒除了會影響情緒相關的心理因素還會影響個體的道德心理。
圖1 顯示,道德推脫可以預測6 個月后的反應性攻擊。此外,道德推脫與主動性攻擊的交叉滯后分析顯示,第一次測量的道德推脫可以預測第二次測量的主動性攻擊。雖然已有一些研究探索了道德推脫與攻擊的關系(e.g.,Hymel et al.,2005;Perren &Gutzwiller-Helfenfinger,2012;Wachs,2012),但是據我們所知,僅有一項橫斷面研究直接探索了道德推脫與反應性攻擊的關系(張棟玲,王美芳,2013)。目前還沒有研究探索過二者間的縱向關系。本研究的結果支持并發展了已有研究。道德推脫可以縱向預測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可能是因為它可以幫助個體緩解攻擊意圖或行為帶來的道德壓力,降低道德系統對攻擊行為的抑制作用,幫助或促進個體實施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
圖1 顯示,道德推脫(T2)可以中介特質憤怒(T1)對反應性攻擊(T3)的預測。這支持了我們的研究假設,并提示特質憤怒會促使個體對攻擊行為進行認知重構,將傷害等不道德行為感知為合適的或合理的,從而避免自責、內疚和輿論譴責等道德懲罰,被特質憤怒增強的道德推脫則會進而增加個體以攻擊來對激惹進行反應的行為頻率或傾向。
4.3 敵意歸因偏向與道德推脫的預測關系
圖1 的交叉滯后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道德推脫(T1)能夠顯著預測敵意歸因偏向(T2),敵意歸因偏向(T2)能夠顯著預測道德推脫(T3)。這些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敵意歸因偏向和道德推脫之間存在相互預測關系的假設。敵意歸因偏向與道德推脫之間存在相互預測關系可能是因為:第一,道德推脫使得傷害意圖合理化,這可能會增強和鞏固個體的傷害/攻擊圖式,并進而促進敵意歸因偏向的產生和發展。第二,對他人行為意圖的敵意解釋可以為個體的道德推脫提供依據和理由,使個體更容易將不道德的傷害行為重新解釋為合理的或不違反道德的,這些都會增強個體的道德推脫。此外,敵意歸因偏向也可以促進傷害/攻擊圖式的發展和強化,并同時促進道德推脫的增加。據此可以進一步推測,敵意性動機和道德準許動機會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預測。
4.4 特質憤怒縱向預測反應性攻擊的動機路徑分析
綜上所述,特質憤怒可以通過增強個體的敵意性動機和道德準許動機來增加個體反應性攻擊的行為頻率或傾向。其中,敵意性動機是反應性攻擊的獨特性動機,而道德準許動機則是反應性和主動性攻擊的共同性動機。本研究以敵意歸因偏向和道德推脫作為這兩種動機的代表性變量來考察該觀點。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們的假設,并提示敵意性動機和道德準許動機是特質憤怒預測反應性攻擊的兩條中介路徑。
除了通過增強敵意歸因偏向這種敵意性動機的認知成分來增強敵意性動機外,特質憤怒很可能還可以直接增強敵意性動機相關的情緒體驗。敵意性的認知與情緒這兩個敵意性動機的基本成分則會使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更多采用攻擊來應對激惹。因此,特質憤怒會通過增強個體的敵意性動機來增加其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反應性攻擊的頻率或可能性。特質憤怒是否會直接通過憤怒、怨恨等敵意性動機的情緒因素來預測或影響反應性攻擊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檢驗。
除了增強道德推脫外,特質憤怒對道德準許動機的促進作用可能還會表現在促進道德基礎與標準切換、增強道德清洗等,以減弱或消除個體的攻擊意圖或行為帶來的道德沖突和失調。增強的道德準許動機則會使個體在遭遇激惹時更容易做出反應性攻擊。至于特質憤怒還可以通過哪些道德準許動機的因素來預測反應性攻擊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探究。
4.5 研究意義
在理論方面,本研究從動機的角度提出了特質憤怒增強反應性攻擊的中介機制,建構了人格與反應性攻擊的動機模型。這一模型發展和深化了人格與攻擊關系的理論,為深入理解人格促進攻擊行為的動機機制提供了理論框架,不僅可以用于整合和解釋已有的人格影響攻擊的中介機制,還可以激發進一步的系列實證研究。
此外,本研究結果對于攻擊的預防和干預也具有兩個方面的實踐意義。一方面,本研究提示家長和教師應關注大學生的人格特征,特別是特質憤怒這類與攻擊相關的易感性人格因素。同時應注意對幼兒或兒童的人格培養,以避免形成諸如特質憤怒等攻擊性人格。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預防和干預學生的反應性攻擊動機(包括敵意性動機和道德準許動機)來減少攻擊,特別是高特質憤怒學生的攻擊。例如,可以采用認知矯正的方法,引導學生進行全面、合理的歸因,減少敵意歸因來抑制其敵意性動機以及通過加強道德教育,減少道德推脫來抑制其道德準許動機。采用這些教育措施利于降低學生在遭遇激惹時出現激烈的反應性攻擊的可能性。
4.6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和值得改進的地方。第一,特質憤怒縱向預測反應性攻擊的動機模型還沒有得到交叉滯后模型分析的完全支持。具體地說,特質憤怒(T1)到反應性攻擊(T2),特質憤怒(T2)到敵意歸因偏向(T3)和道德推脫(T3),敵意歸因偏向(T1)到道德推脫(T2),以及道德推脫(T2)到敵意歸因偏向(T3)的路徑均不顯著。出現這些不符合預期的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交叉滯后模型納入的變量較多,一些變量的縱向預測效應較低,某些預測效應可能會因為測量誤差和隨機誤差等原因變得不顯著。此外,本研究相鄰兩次調查的時間間隔不夠長,被預測變量的變化可能較小,因此某些預測效應就會相對較小,未來研究應該增加時間間隔。總之,特質憤怒預測反應性攻擊的動機模型還需要進一步檢驗。第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大學生,特質憤怒增強反應性攻擊的動機機制是否適用于其他群體有待進一步探索,未來研究應該考慮在兒童、青少年以及社區成人等其他群體中檢驗該中介機制。第三,本研究只使用了自我報告的方法,未來研究應該考慮將自我報告與他評以及實驗任務等測評方法結合起來檢驗該動機路徑。第四,本研究僅探索了敵意歸因偏向和道德推脫這兩個典型的反應性攻擊的動機因素的中介作用,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其他的反應性攻擊的動機因素,例如敵意、恐懼、憤怒、憤怒沉浸、道德標準切換、道德清洗等是否也具有(鏈式)中介作用。
5 結論
動機是界定反應性攻擊的核心概念,揭示人格預測攻擊的動機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通過3 次調查的縱向研究發現,特質憤怒可以通過兩種反應性攻擊動機(以敵意歸因偏向為代表的敵意性動機和以道德推脫為代表的道德準許動機)的多重中介作用來縱向預測反應性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