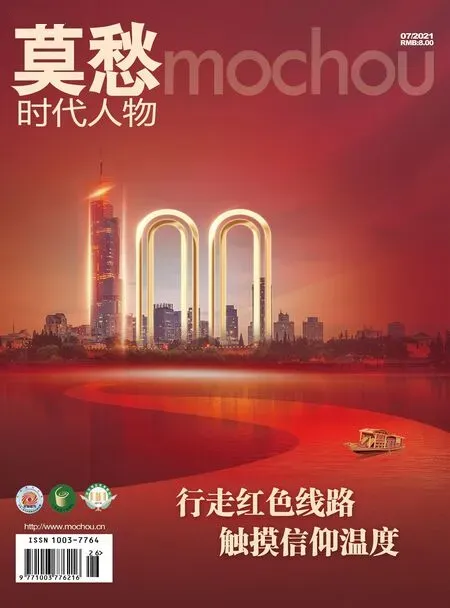南通博物苑:江海古韻,與鯨共舞
文/朱晨瑜

南通博物苑新館
南通博物苑位于風景秀麗的濠河之畔,是由愛國實業家張謇于1905年創建的一座公共博物館。比起傳統的博物館,南通博物苑更像是一座婉約秀麗的江南園林,南館、北館、中館三座主要展館掩映在花木叢中,形成一條南北中軸線,軸線之外散布有東館、藤東水榭、相禽閣等造型風格迥異的景觀建筑。2005年,南通博物苑在原址的基礎上擴建出第二軸線。新展館在設計中融入南通獨有的地域文化元素,古典與現代交融,形成了園館一體、寓教于樂的獨特風格。
江海古韻
進入新館廣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塊巨大的詩壁。當年張謇曾多次上書清政府要求興辦博物館,但不被重視,他只好在家鄉率先實踐。新館建成之后,南通博物苑特在這里建起一塊詩壁用來紀念張謇,上面篆刻著他當年寫下的《營博物苑》:濠南苑圃郁璘彬,風物駢駢與歲新。證史匪今三代古,尊華是主五洲賓。能容草木差池味,亦注蟲魚磊落人。但得諸生勤討論,征收莫惜老夫頻。


南通瀕江臨海,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這里很少發生自然災害,歷史上也少有戰事,因此保存下了許多歷史悠久的文物古跡。新館的“江海古韻”展廳以南通地域保存下來的文物為主,展示了南通先民與自然相互依存的歷史軌跡。
鹽棉興邑,南通人自古以來就擅“吃海”。西漢時期,南通先民就開始煮海為鹽,到唐朝時期,南通已經是全國四大產鹽地之一,為全國賦稅作出了巨大貢獻。盤鐵是古代人民重要的煎鹽工具。這里展出的清代盤鐵大約一丈左右,由數塊小盤鐵拼成一個大盆,稱為勞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造型各異的產鹽工具,展示了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
隨著沿海灘涂的淤漲,南通原有鹽場距海漸遠,制鹽業逐漸衰落,但是外移的海岸線帶來了大片豐饒的土地。自明代開始,南通的棉花種植業逐漸興盛,流傳著“家家紡線、戶戶織布”的說法。“閩粵人秋日抵通收花衣,巨舶千百,皆裝布囊,標記其上……”南通土布在當時遠銷海內外,頗受歡迎,是當時主要的經濟支柱之一。新館內收藏展示了九匹大小不一的南通土布,主要分為黃白二色,工藝高超,質地上佳,讓人不禁感嘆南通先民精妙的紡織技藝。
基于江海交匯的地理優勢,古代南通的棉紡業興旺發達,成為近代南通較早轉型發展的基礎,催生了近代工業文明的到來。以張謇為代表的先賢建設的模范縣,使一個輝煌的近代南通定格在歷史的時空,為今天的南通邁向新紀元奠定了基石。
巨鯨天韻
南通地處長江入海口與黃海黃金海岸交匯處的江海平原上,氣候溫和,土壤肥沃,水網密布,海涂遼闊。江海之濱還棲有國家重點保護珍稀動物等眾多生物種群。豐富的自然資源為南通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鯨類的身影在南通附近海域頻繁出現,由此也衍生出與鯨類同生息共命運、生機盎然的江海自然生態。
1911年2月,呂四灘涂挖出“海大魚”。張謇將其骨骼標本帶回,陳列于剛剛建成的南通博物苑北館。這條海大魚,學名叫長須鯨,是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也是南通博物苑獨有的標本之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南通博物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嚴重破壞,這套鯨魚骨骼標本也未能幸免,最終僅有頭骨殘存,現已被移至新展館妥善保存。除了長須鯨頭骨,還有兩副鯨類骨骼標本懸掛在展廳中央,在地面珊瑚的映襯下,仿佛在海底世界遨游。
再往前走,就是“濁海歡歌”單元,包括鯧魚、梅童魚、海鰻、馬鮫魚、烏賊等在內的二十余種海洋水產標本,不僅是大魚的食物,也是豐富人們餐桌的美味。拾級而上,展館二層打頭陣的則是沿海灘涂上的“蝦兵蟹將”,文蛤、青蛤、竹蟶等各種貝類穿插其中。“大江浪曲”單元展示了鰣魚、刀魚、長吻鮠、暗紋東方鲀等長江水產“四大名旦”為首的淡水魚類。“濕地鳥語”單元則被布置成了各種珍稀、野生鳥類棲居的快樂家園,這些鳥類的身影都曾在南通本地出現過。
“巨鯨天韻”展館內收藏了三百余件自然標本,通過將這些標本與大型場景的結合,讓游客身臨其境,感受江海南通與鯨共舞的民俗文化。展館內設介紹詞詳細介紹了中國鯨的種類、特征和習性,表達了南通博物苑對鯨類的關注與研究。展覽還設置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尾,通過提問的方式,引發游客思考如何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

博物情懷
穿過圍墻中間的大門,就從博物苑來到了濠南別業。別業是別墅的一種雅稱。濠南別業是融住宅與園林于一體的建筑群落,作為近代中國吸收西方建筑藝術、運用新型建筑材料的成功范例,已被載入中國建筑史冊。
別業的主體建筑是一座四層英式樓房,坐北朝南,氣宇軒昂,紅色鐵皮屋頂,設有氣窗;青磚墻面,白色灰縫均勻而又美觀;朱漆門窗寬闊敞亮,窗框上以紅磚砌成拱形裝飾;在二、三樓東、南、西三面有回廊,向南有突出的陽臺,東西兩側回廊上的紅柱頗為別致。大樓門前一紫一白的兩株巨大的紫藤樹是張謇當年親手植種,已有百年歷史,每年開花時節,一紫一白兩道瀑布傾瀉而下,蔚為壯觀,總會吸引眾多市民和攝影愛好者前來觀賞拍照。
別業二樓的中間大廳為議事廳,是張謇當年接待重要賓客和舉行儀式的地方。大廳兩側的廂房分別是議事室和書記室。大廳后部有推拉門,向內西面是會客室,東面是宴會廳,中間是木樓梯。在會客室里曾有一副張謇親書的對聯:“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與子方孝,與父言慈”,反映了他的處世態度。
張謇深知文物是博物館的基礎,毫不猶豫地捐出自己的所藏,而后于1907年刊印《通州博物館敬征通屬先輩詩文集書畫及所藏金石古器啟》,是中國最早的文物征集啟事。張謇對文物征集主張是“縱之千載,遠之異國者,而昭然近列于耳目之前”,希望“收藏故家,出其所珍,與眾共守”,而他自己也帶頭拿出文物交博物苑收藏。他在啟事中說:“謇家所有,具已納入。”
在今天看來,張謇的文物征集理念依然科學和實用。他注重地方文物的收集,是為了“留存往跡,啟發后來”。張謇憑借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廣泛的社會關系,為博物苑廣征博采,充實了苑藏品。因此,很多人將南通博物苑視為中國博物館的圣地,每到南通必至此處瞻仰先賢遺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