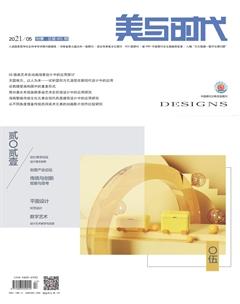殷商鳥獸造型與金文書法相結(jié)合的雕塑形態(tài)研究
摘? 要:中原地區(qū)是殷商文化的重地。殷商美術(shù)中的“合成式”鳥獸圖案展現(xiàn)出古人超凡的想象力和對神秘力量的崇敬。針對該地域性核心題材進(jìn)行研究,試圖找尋一種藝術(shù)實(shí)踐方式,用以深入挖掘一座城市的歷史文脈,并把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學(xué)習(xí)和當(dāng)代藝術(shù)語言的轉(zhuǎn)換,一并納入到日常的藝術(shù)實(shí)踐中去。
關(guān)鍵詞:殷商文化;金文書法;空間
中原是華夏文明的發(fā)源地,中華民族在母親河黃河的哺育下生生不息,創(chuàng)造了璀璨的中原文明,殷商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自2015年,筆者的工作和生活在河南這片土地上展開,隨著不斷地深入接觸和實(shí)地考察這里的人文和歷史,筆者對河南本土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并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
殷商美術(shù)中的“合成式”鳥獸圖案展現(xiàn)出古人超凡的想象力和對神秘力量的崇敬。在河南殷墟出土的虎頭觥、鸮尊、跽坐玉人、虎頭人身怪的造型中,“拼湊合成”的藝術(shù)造型法則,皆不是為了還原真實(shí)的動物、人物,而是為了創(chuàng)造符號式的藝術(shù)形象以供祭祀。通過塑造這類神秘形象,商朝藝術(shù)品形成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氣質(zhì),也直接促成了以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中國藝術(shù)造型的“東部傳統(tǒng)”。東部的造型傳統(tǒng)有別于西北,不以原始的自然審美為藝術(shù)準(zhǔn)則,而是追求藝術(shù)的禮儀精神力量。
自商朝末年開始,禮儀精神的表現(xiàn)不僅僅局限于“合成式”鳥獸雕塑的創(chuàng)造,在規(guī)制多樣的青銅器中,銘文開始用“書寫”直接闡釋藝術(shù)品的精神價值,從而形成了千姿百態(tài)的金文書體。金文不僅是用于記錄祭祀、戰(zhàn)爭、封賞等重要的歷史人文信息,還是一種獨(dú)立的藝術(shù)載體,它所傳遞出的審美價值被歷代藝術(shù)家視為創(chuàng)作的源泉。青銅器皿表面熔鑄出的金文“類物象形”,是抽象化、系統(tǒng)化的美學(xué)符號,在漢字標(biāo)準(zhǔn)化書寫之前,金文結(jié)體間所蘊(yùn)含的空間性、線條力度和組織結(jié)構(gòu),在展現(xiàn)了禮儀精神種種訴求的同時,更充滿了無限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由于古人使書法的藝術(shù)性達(dá)到了極致,因此當(dāng)面對傳統(tǒng)時我們會感到,先輩做得那樣完美,我們已無事可干。這時,一種新的空間觀念為筆者認(rèn)識和評價書法的創(chuàng)造性提供了新的參照系,這個參照系使筆者深刻地認(rèn)識到,路并沒有走完。
在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雕塑系的研究生學(xué)習(xí)過程中,導(dǎo)師李秀勤教授鼓勵筆者進(jìn)行“書法—雕塑”課題的研究,這是從二維書寫向三維雕塑的一種空間的轉(zhuǎn)換。“空間書寫”以及隨后跨越時空的“社會書寫”等系列理念的提出是具有突破性的,它打破了某些邊界,開啟了傳統(tǒng)與當(dāng)下相結(jié)合的通道,也使筆者的藝術(shù)生命得到延伸和拓展。
傳統(tǒng)書法理論典籍《歷代書法論文選》是一本較為全面的書論集,它包含從漢代至清代的歷代著名書法論文69家共計(jì)95篇,其中包括衛(wèi)夫人、王羲之、顏真卿、康有為在內(nèi)的大書論家和書家的書法論文。但這些書論家和書家大都只談書法的結(jié)體和章法,極少見“空間”字樣。即便是現(xiàn)代書法論著偶爾會談到空間,例如邱振中的《書法形態(tài)與闡釋》中,對空間觀念有突破性進(jìn)步的明代書家王鐸書作的論述:“他的作品每一行側(cè)廓的強(qiáng)烈變化、單字的多種承應(yīng)方式對字間空間的影響,使外部空間節(jié)奏和內(nèi)部空間節(jié)奏、線條運(yùn)動節(jié)奏都達(dá)到較好的統(tǒng)一……”或者是日本現(xiàn)代杰出的書法藝術(shù)家井上有一,他以一顆赤子之心從素材到技法上都勇于返璞歸真,并妥善處理書法內(nèi)部空間的包容與收斂、內(nèi)外空間的相互流動等問題……但他們提到的“空間”都僅限于書寫二維空間的線性分割。
為了從空間關(guān)系上超越古典作品的勢力范圍,上升到更高的形式層次,我們通過金文書寫刻意地去訓(xùn)練對所有空間的敏感性和把握能力,并開發(fā)大量的課程以尋求實(shí)踐的方法:比如書法與篆刻的結(jié)合、書法與中國古代建筑的轉(zhuǎn)化、東西方抽象雕塑對比研究等。結(jié)合這一系列具體課程,同時通過對中國書法的摹寫研習(xí),筆者開始意識到金文結(jié)體中蘊(yùn)含的三維空間結(jié)構(gòu)。這有別于西方雕塑幾何化的抽象創(chuàng)造法則,而擁有著不規(guī)則的形態(tài)、豐富的空間、極強(qiáng)的造型感和本土生命力。在書寫過程中,意念中的三維空間可以投射到二維的平面上。基于以上的感悟,筆者創(chuàng)作了《空間延伸》系列綜合材料金屬焊接作品,試圖用這種方式來表現(xiàn)金文書法在三維空間中的筆意、空間結(jié)構(gòu)、絞轉(zhuǎn)、點(diǎn)與線、勢與力等的特征。
隨后筆者將金文書法與中原地區(qū)殷商美術(shù)中的“合成式”鳥獸紋樣融合,進(jìn)一步思考金文書法與雕塑相結(jié)合這一課題。商代器物中的雕塑形象與金文書法共同具備同一種精神氣質(zhì):它們都源于具象(這通過尋根溯源可以考證),并經(jīng)由先輩們不斷地簡化、變形、拆解、組合、重構(gòu)而變得越來越抽象、越來越觀念。這種互通點(diǎn)使得商代器物中的雕塑形象與金文書法能夠通過雕塑造型的實(shí)踐方式予以銜接。此基于,筆者進(jìn)一步創(chuàng)作了《玄鳥生商》《嵩山如臥》《豫劇臉譜系列》等一系列抽象雕塑作品,試圖結(jié)合河南的本土地域文化和金文書法結(jié)構(gòu),尋求新的雕塑語言,開啟新的雕塑表現(xiàn)空間。
在當(dāng)代藝術(shù)實(shí)踐過程中,我們要分清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現(xiàn)階段致使藝術(shù)工作者在藝術(shù)實(shí)踐中舉步維艱的主要矛盾就是:知與行如何統(tǒng)一。隨著信息時代的發(fā)展,知識獲取的途徑越來越便捷,即便暫時不知曉也能通過網(wǎng)絡(luò)搜索迅速補(bǔ)充上欠缺的知識。但由于獲取的知識過于表象、片面或者不系統(tǒng)、不深入,這讓認(rèn)知只能達(dá)到感性階段(這也是大部分藝術(shù)工作者所處的階段)。如果用這種感性的認(rèn)識去指導(dǎo)藝術(shù)實(shí)踐,會導(dǎo)致藝術(shù)工作者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淺嘗輒止,藝術(shù)作品無法達(dá)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直至實(shí)踐難以延續(xù)最終放棄。只有當(dāng)感性階段碎片化的認(rèn)知和感覺經(jīng)過思考和梳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改造,形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tǒng),這樣感性認(rèn)識才能上升到理性認(rèn)識。這個階段是藝術(shù)工作者自我充實(shí)和能量蓄積的過程,也是藝術(shù)脈絡(luò)在思維上的成型,為后續(xù)的藝術(shù)實(shí)踐夯實(shí)了基礎(chǔ)。然而,認(rèn)識發(fā)展到理性階段,在唯物論的認(rèn)識運(yùn)動中也只完成了一半,倘若正確的理論只是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shí)行,那這種理論再好也沒有意義。這也是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家的一個普遍狀態(tài):說得多做得少,或是用話說作品而不是用作品說話。我們只有將系統(tǒng)的理論運(yùn)用于藝術(shù)實(shí)踐,通過實(shí)踐、認(rèn)識、再實(shí)踐、再認(rèn)識……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以至無窮,而實(shí)踐和認(rèn)識的每一次循環(huán),都要比之前進(jìn)到更高一級的程度,這樣才算達(dá)到知與行的統(tǒng)一,藝術(shù)生命才有可能延續(xù)下去。
理論上是如此,那么真正的藝術(shù)實(shí)踐如何能避免空談,落于實(shí)處?對于創(chuàng)作脈絡(luò)不清晰的藝術(shù)工作者是否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來指導(dǎo)實(shí)踐,從而更好地延續(xù)自身的藝術(shù)之路?這個關(guān)于殷商美術(shù)與金文書法結(jié)構(gòu)相結(jié)合的雕塑形態(tài)研究的課題,就是為實(shí)現(xiàn)解決這個問題,實(shí)現(xiàn)既定目標(biāo)提出的方法論。在此,筆者是這樣思考該課題的價值和意義:
(一)開發(fā)一種藝術(shù)語言,用以塑造殷商的精神氣質(zhì)。在商代,青銅器中的形象與銘文的線條美感,共同構(gòu)成了這一時期的精神氣質(zhì)。商朝的工匠把饕餮紋、蟠螭紋、鳥獸紋、云雷紋等塑造于“禮器”之上,驅(qū)趕螭魅魍魎,“用能協(xié)于上下,以承天休”。與此同時,歸納萬物形態(tài)的文字熔鑄在相關(guān)器物其內(nèi),用以進(jìn)一步體現(xiàn)統(tǒng)治者的意志和力量。這二者共同承載的裝飾觀念與審美意識,長久地流動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對后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應(yīng)該結(jié)合當(dāng)下并尋求一種藝術(shù)語言,用以統(tǒng)一、再現(xiàn)這兩種同時期出現(xiàn)的藝術(shù)形式。
(二)打破單一雕塑的團(tuán)塊結(jié)構(gòu)和構(gòu)成語言,追求線條的表現(xiàn)力。在雕塑專業(yè)的傳統(tǒng)教學(xué)中,蘇派、法派的教學(xué)模式對該學(xué)科的教學(xué)實(shí)踐影響深遠(yuǎn),“塑造”所形成的西式創(chuàng)作模式,構(gòu)成此學(xué)科的精神內(nèi)核。而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中,“線條”是獨(dú)特的造型媒介,它不僅僅用于勾勒形體、塑造輪廓,其本身停頓、轉(zhuǎn)折、延伸也充滿著無限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在殷商美術(shù)與金文書法結(jié)構(gòu)相結(jié)合的雕塑實(shí)踐中,筆者不僅致力于勾勒“神秘”圖示的影像,同時兼顧線條的張力與書法筆意,并試圖使二者融匯于殷商題材的雕塑創(chuàng)作中。
(三)“書法—雕塑”課題中藝術(shù)語言的拓展。當(dāng)代雕塑的藝術(shù)實(shí)踐已經(jīng)存在不少針對書法形態(tài)的三維藝術(shù)嘗試,這些作品觀念側(cè)重點(diǎn)不同,藝術(shù)語言各有優(yōu)勢。作為后學(xué),在思考書法文字直觀的形態(tài)向雕塑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中,同樣側(cè)重于書法核心精神性的表現(xiàn)。與此同時,筆者試圖把書法抽象的形態(tài)和造型規(guī)律,應(yīng)用于具體形象的塑造中,如殷商傳說中的鳥、獸、人、物等。通過再現(xiàn)這些饒有趣味的形象,激發(fā)創(chuàng)作的想象力,并利用書法線條的抽象表現(xiàn)力,使其“神似”。
(四)對歷史性、地域性雕塑題材實(shí)踐方式的再思考。在中原地區(qū),藝術(shù)題材問題一直是本土雕塑家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探討的重點(diǎn)。一方面,中部藝術(shù)題材涵蓋量巨大,單就鄭州一地,“黃河文化”3600年的歷史痕跡彼此覆蓋,要找出核心的內(nèi)容予以表現(xiàn),難免心志縹緲。另一方面,在層出不窮的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表現(xiàn)題材、新興藝術(shù)語言、另類表現(xiàn)方式的沖擊下,傳統(tǒng)題材的當(dāng)代實(shí)驗(yàn)極難納入雕塑藝術(shù)的視野,往往備受冷落。而以上兩點(diǎn),共同表現(xiàn)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鄭州地區(qū)的現(xiàn)狀——針對地域性核心題材創(chuàng)作,固守具象,拒絕拓展;在當(dāng)代雕塑語言的探索上一味追逐新穎,甘做“無源之水”。因此筆者認(rèn)為,現(xiàn)在迫切需要找尋一種藝術(shù)實(shí)踐方式,用以深入挖掘一座城市的歷史文脈,并把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學(xué)習(xí)和當(dāng)代藝術(shù)語言的轉(zhuǎn)換,一并納入到日常的藝術(shù)實(shí)踐中去。
迄今,我的殷商鳥獸造型與金文書法相結(jié)合的雕塑形態(tài)研究,這項(xiàng)藝術(shù)實(shí)踐工作一直在沿著殷商鳥獸造型和中國金文書法造型相結(jié)合的這條主脈絡(luò)發(fā)展。在實(shí)踐探索的過程中,會有很多新的發(fā)現(xiàn),進(jìn)而產(chǎn)生新的嘗試,致使這條主脈又不斷生發(fā)出新的旁枝,這也讓這個雕塑形態(tài)研究的體系更加充盈和豐滿。
參考文獻(xiàn):
[1]金學(xué)智.中國書法美學(xué)[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459.
[2]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diǎn).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21-23.
[3]朱志榮.夏商周美學(xué)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87.
[4]邱振中.書法的形態(tài)與闡釋[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131-148.
[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297.
作者簡介:肖彩,鄭州市環(huán)境雕塑建設(shè)研究所專業(yè)技術(shù)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