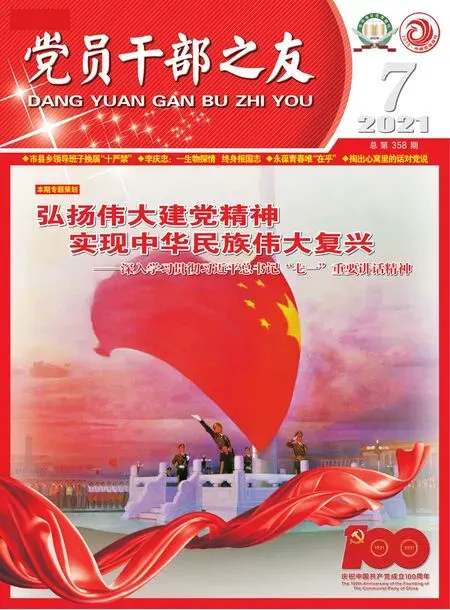掏出心窩里的話對黨說
□ 吳永亮
1968年秋季開學第一天,我第一次走進鄉村那四面透風撒氣的教室,只見作為老師的我叔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寫著: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天天在耳邊響起比較好懂,但“共產黨”就不太好解了。我們就問:“共產黨是什么?”叔叔用粉筆頭頂頂頭皮說:“我們村里老隊長就是一名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就是頂呱呱的好人,就是替別人著想的人,為別人做事的人。”
從那,在我幼小的心靈里就埋下“共產黨就是替別人著想的人,為別人做事的人”這顆種子。由于老隊長在村里威望最高,我就想我長大了也要做一名共產黨員,讓別人也一樣尊重我。
小學五年級,我與另外3 名同學一起戴上紅領巾。當時一種自豪、驕傲感油然而生。可以說我是唱著蹦著回到了家,晚上睡覺的時候也舍不得把紅領巾摘下來。我常常想起老師對我們說的話: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紅領巾是無數共產黨員用鮮血染紅的。戴上紅領巾就意味著你就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雖說當時有許多話聽不太懂,但有一條,我離黨組織近了一步我是明白的。
高一那年秋天,學校團支部組織委員會的戴樹榮找到我,鄭重地對我說:“你寫的入團志愿書,團支部已經討論過了,準備吸收你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戴樹榮把一份入團志愿書交到了我的手里。這是我第一次填寫表格,從此表格伴我走天下。當我將自己紅色的手印摁在表格自己名字上的時候,一種責任、一種榮譽感陡然升起。當時,我真想大喊一聲:我是一名共青團員,我離黨組織又近了一步。

1980年9月,經過激烈高考,我被原濟南軍區步兵指揮學校錄取。緊張的三年軍校生活錘煉了我,直線加方塊的韻律陶冶了我,從此我懂得了什么叫組織,什么叫紀律,什么叫命令,什么叫服從,什么叫直線加方塊的韻律。由于我是來自農村中學,加之自己身體素質不高,因此軍體課的成績一直在良好與及格之間徘徊。作為軍校,軍體這方面的要求又非常高,我自感離黨組織的要求還差一定距離,雖眼望組織的大門但沒有邁入的膽量。我感到苦惱、感到灰心,情緒受到極大影響。這時董教導員及時找我談心,讓我放下包袱,振奮精神。董教導員說:“即使在軍校解決不了組織,到基層部隊也可以解決。”最終由于名額等限制,三年軍校我未能加入黨組織。當我離開軍校的時候,我感到滿足但也有深深的遺憾,那就是我未能投進黨組織的懷抱。
1983年7月,我來到某邊防部隊警衛排。一放下隨身攜帶的包袱,也同時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與戰士打成一片,虛心向干部和戰士們學習,較短時間便完成了一名學生干部向基層干部的轉變,較好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半年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團司令部支部(警衛排屬于司令部直管)決定吸納我加入光榮的中國共產黨。38年過去了,但我清楚地記得當我舉起拳頭向黨旗宣誓的情景。那一刻,年輕的心和火熱的血交織在一起,內心發出最強烈的聲音:“黨啊,我終于成為您的一分子,我的一切都是屬于您的,我愿為您奉獻一切。”
1985年,正當我在黨的教育下為部隊建設努力工作之時,百萬大裁軍開始了。王參謀長征求我的意見。我說:“我是一名從地方到軍校的學生,這些年受黨的教育,我想把自己所學到的一切在部隊大熔爐里進行錘煉再鑄造,從內心來講我不愿離開部隊。但是我理解裁軍的意義以及一名共產黨員在組織面前應如何選擇。”當組織將我與其他數十名干部納入編余時(編余就是暫不安排位置,等待下一步或調到別的部隊或轉業到地方工作),我能夠正確對待。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屬于黨的,黨現在讓我編余,我還有什么話要說,我應當積極配合組織做其他人的工作。編余期間,我一直保持旺盛的工作熱情,協助編余辦公室做好善后工作,并在團部連續值了一個月的班。在這種情況下,團黨委認為我編余期間人心不散、工作不減,給予我榮記三等功一次。這是我第一次立功,其喜悅的心情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最終根據我的能力和表現,我被調到煙臺警備區后勤部政工科擔任干事。事后,有人問我“你是走的誰的后門”時,我笑笑說:誰的后門也沒有走。只要你聽黨的話,一心一意為黨分擔你所擔負的工作,主動替組織分憂,組織就不會忘記,也不會讓你吃虧的。
1987年底,我從煙臺調到原濟南軍區衛生學校工作。在軍區衛生學校,我先后擔任政工科干事、學員隊副教導員、政治教研室教員。每一次調整,我都愉快服從組織安排,從不講條件。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名山村的孩子,小的時候是在牛背上長大,我的一切都是因為有黨才有我的今天,我只有對黨奉獻的份,絕對沒有講條件的資格。1992年開始,香港、澳門回歸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我以一名政治教員應有的敏感,決定悉心研究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來龍去脈。我先后到省圖書館、省委黨校閱覽室、新華書店等,查閱大量資料,并做了百萬字的讀書閱報筆記,還自己動手制作了十幾幅布制地圖、上百張投影片。1997年,我應邀到軍隊院校機關、地方企事業單位、大學等演講香港回歸近百場,受到廣泛歡迎。濟南人民廣播電臺、濟南電視臺、齊魯電視臺、山東衛視、《聯合日報》、《齊魯晚報》等新聞媒體對我的演講都做了報道,就連香港鳳凰電視臺也做了介紹。我被學校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并榮記三等功一次。面對榮譽,我保持了清醒頭腦。我想,我終于為黨做了一點事,我在用自己的演講技能報答黨組織多年對我的關懷。
1997年,學校因裁軍面臨停辦。當時,一家省直報社要我,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親朋好友都勸我趕快打報告申請轉業。可我想,十幾年軍旅生涯中,我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兩次榮立三等功、多次評為優秀教員,這一切都鑄造了我服從組織聽從組織安排的黨性觀念。學校周政委找到我,問我有什么打算。我說作為個人發展來說,我希望組織讓我轉業,但我絕對聽從組織的命令。學校考慮到還有兩個年級學生沒有畢業,希望我留下送走學生再說。我愉快地留下了。
1998年6月,我以省直機關筆試前十、面試第一的成績前往山東省新聞出版局報到,從事全省報刊管理工作。從此,我完成了為國站崗到為黨的新聞出版事業站崗角色轉變。
轉業后,我努力學習相關法律法規,刻苦鉆研業務,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由門外漢到“專家”的轉變。工作上兢兢業業,對報刊社提出的問題耐心解答,熱情為他們服務,堅決杜絕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現象在我身上發生。上班時間,我辦公室門會一直敞開,就這點小事,就贏得了許多贊譽。
正當我越干越帶勁的時候,局里準備出版《新聞與出版》連續性內部資料。局黨組考慮到我對撰稿、編輯等業務較熟悉,于是想調我去協助一名老處長做這項工作。同事聽說后,紛紛私下對我講堅決不要去,去了就邊緣化。我笑笑說,什么叫邊緣,什么叫中心,只要黨叫干的工作就不存在這些。最終我還是愉快地離開了許多人羨慕的報刊管理工作,從事《新聞與出版》約稿、編輯、校對、出版工作。
幾年后,我又到了農家書屋辦公室,后來又到數字出版處,再到出版管理處。每一次調動,我都是二話不說,收拾收拾就去報到。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農村出來的孩子,在省政府大院(后機構改革到了省委大院),能三個人共一個辦公室,一人有把辦公桌,足矣。”知足,自然就會笑對每一天。
我轉業時就是技術九級,享受副處級待遇,新聞出版局任職命令為主任科員,但人們習慣地喊我吳處,我都是含笑點頭不作答。轉業后很長時間,一直在原地踏步,熟悉的朋友叫我吳處,我自嘲說:“‘吳’處不在。”2012年2月3日,省局選拔干部,我走上講臺樂呵呵地說:“從剛才我坐的位置到現在的演講臺,只有區區十五步,但我卻走過漫長的十五個年頭卻無怨無悔。”最終,我競爭上了剛剛成立的數字出版管理處副處長這一職位。
這些年,我干好本職工作之余,在《青年記者》等專業期刊上開辟《讀報札記》《我讀〈現漢〉》《編校雜談》等欄目。我被推薦為全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校對專業委員會專家庫成員。
多年來,我先后到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大學等高校,在全省圖書報刊編輯培訓班、濟南中小學和青島書城等地講課,在省圖書館大眾講壇上發表《敬畏漢字——從中國漢字聽寫大會說起》演講,均引起較好反響。我的授課,激情滿滿,通俗易懂,風趣幽默,常用故事開道,用身邊最近發生的例子說理。
2019年4月4日,我主講的《出版工作者應遵循的漢字規范》(上、中、下)在國家新聞出版署繼續教育網站正式上線,成為全國圖書、期刊編輯繼續教育課程。
回顧我走過的路,梳理我取得的成績,黨啊,在您誕生一百周年之際,我掏心窩的話就是:人們常說滴水之恩定要涌泉相報,可是面向您——各級黨組織對我的教育、引導、關懷、幫助,把一個從牛背上長大的放牛娃最終培養成省委宣傳部一名處級干部,我畢其一生都無法報答,唯有踏踏實實、任勞任怨永遠跟著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