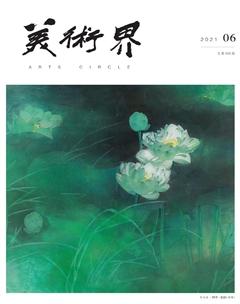蘆仙山下的有才
孫曉楓

蘆仙山在廣西藝術學院的西北邊。每次從酒店的窗外望過去,總是可以看到蘆仙山綽約的影子。蘆仙山虛虛實實的天際線,一方面來自于天氣的陰晴枯濕;另一方面來自眼睛的物理性限制,即是“目力所及”所描述的意思;再則是個人屬于高度近視,看萬事萬物總會被這一個前提所限定。
去歲十二月初,和少鵬兄、旭旻、有才、志軍上蘆仙山,那日的天氣較為濕冷潮潤,山上的空氣挾帶各種植物的氣息,青澀中隱透一絲甘甜,人的神氣也爽朗舒邁。山上的植被生態非常多樣,有許多叫不出名字的雜草和樹木,對于我們這些畫畫的人,似乎也不必去窮究這些植物的名目。感受它的色彩、空間、形態、構成等與視覺有關的元素也就足夠了,視覺思維也是解讀世界的一種方式,做力所能及的事未必不是正理。誠如蘆仙山下的四聯村,那里的生態、歷史、宗法與安靜地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村民,他們生存的空間或許不用太大,只要有生存之地和解決溫飽的基本生活資源,也就足夠了,即使他們一直追索先祖來自于福建莆田,但那種越發模糊的家族背景提供了一個血緣和故鄉的想象并建立起基于血緣宗法的秩序與認同感,其他并沒有賦予更多的可能與改變現狀的力量。這是一種最為卑微而帶有遷徙記憶的生活,對于“故鄉”的情感既無法宗教化,也無法現實化,因為“故鄉”只是一個傳說,一個近似于“創世”的傳說而已,現實中的故鄉卻一無所知、一無所是。
廖有才的工作室就在蘆仙山下的四聯村里,他的創作必然和四聯村的傳說有了某種呼應的鏡像關系。有才是從武宣來到南寧求學、成家落戶并成為廣西藝術學院的一名教師,他同樣帶著家鄉的記憶駐留在南寧,南寧的省城生活和家鄉的經歷和情感不時地交纏在一起,成為他藏匿在作品背后的情感底色。而四聯村那種和家鄉相仿的調性,恰恰讓有才獲得某個層面的舒適感和歸屬感。
在有才的自述中他講道:“我生長在武宣縣周邊的一個小村莊,村里有很多惡霸,他們打群架、偷雞摸狗的事干得不少。村里有出去做建筑工的,也有到廣東進廠做苦力的……我父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從小就不讓我跟不良少年一起玩,怕我被別人帶壞或跟別人打架,我的童年很少有時間跟同齡人玩耍,大多時間不是放牛回家就是在去放牛的路上,這一放就放到小學畢業。”他后來想當兵,愿望落空后輟學跑出去打工,后來也因為父親發現他的天賦才讓他回到高中讀美術專業班。而這一決定影響了有才以后的軌跡,從此他到廣西藝術學院求學,碰到了眾多給予他幫助的師長,特別是他的碩士研究生導師黃菁老師,更是傾注了亦師亦父的啟迪與關愛。黃菁老師是有才的貴人,終于讓他成才并成為了具有較高社會身份的大學教師。從小到大,這種巨大的落差讓有才更珍惜他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在慶幸和感恩之中同時夾雜著某種不安和欠缺感。他的種種努力與生活工作中的忍讓,正是憂慮所有的會失去。


有才的作品,無論是在遇龍河或是陜北的寫生,還是他苦心造詣的《衣錦》系列(這批作品或許是來自一種典型的規訓想象),第一感覺就是他具有極強的對畫面的控制力,才情與品位并重,在筆觸與材料相互交疊而壓制的張力中保留著某種全力以赴的忘我和毅力,在高度精神集中的狀態中毫無保留地把情感和潛意識中的恐懼揉砌在厚重的泥漿和如錐的筆觸之中。廖有才在古典主義和構成主義中尋找折衷的安全的表達區域,畫面古樸而典雅的同時又攜帶泥土(材料)的腥味,作品具有野性和厚重的時間感。這是藝術家“移情”的明顯表征,他的成長期所遭遇的困難和磨煉,轉化為創作中的狠勁,他只有在繪畫過程焦灼的痛苦中才能感到一絲輕松和極度壓抑后回報的快感和不事張揚的快樂。
生活中的無根感是藝術家不斷折返尋找傳說中寄托和皈依的重力。他只能在被承認的那一部分歷史中尋找某種話語的依托,他甚至會懷疑自己的才華以及噴涌而出的靈感。因為個人的原創之力有時是不明覺厲并且似乎不具備說服力的。在挫敗的時刻,甚至會憎惡自己的出身以及經歷過的所有痛苦。黃菁老師對于有才的意義不僅僅止于一位良師的諄諄善誘,還有父親般溫暖的照料,更重要的是黃菁老師作為廣西藝術語境中最重要的話語先導者對他的肯定,這份肯定讓他找到了個人創作的“合法性”和“必然性”,也擺脫了他執著于家鄉的想象鏈條。

廖有才當下所要做的,是獲得擺脫外在因素制約的自覺,包括他的過去,回到天賦中對天地萬物的敏感度和捕捉力,在經驗中提純出適應當下表達方式的語言系統,進而讓自己成為一個面對個人的過去的觀察者和研究者。重置展開作品的角度,把困擾于自身的情感方式及夾帶其中的不良情緒歸置為一種明確的文化取向(指向),有針對性地展開表達。這條路徑或許可以促使自我精神肖像的顯現,那個被壓抑的、被對抗的“廖有才”方能釋然地在作品中強化個人的主體性表達。
蘆仙山即是有才的鏡像,寧愿野草叢生,也不愿被速生林模式化,寧愿生猛而無序地瘋長,也不愿保持那種毫無生氣的謙遜,真正的謙遜并不在沉默中實現,有時也需要表現為打群架時的手下留情和網開一面。一個藝術家身份的成立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現在還能做什么,他未來所實踐的目標,他的成功和失敗才是最為重要的部分。
為什么我們不能在藝術和生活中露出獠牙?質疑即是一個新的開端。而我相信有才的蛻變已經開始。
蘆仙山在一場風暴后那些放肆而不明覺厲的枝柯劃破天宇。


廖有才
曾用名:廖有米。1985年出生于廣西武宣,壯族。2010年畢業于廣西藝術學院美術學院油畫系,獲學士學位。2013年畢業于廣西藝術學院美術學院,獲碩士學位。2014年于首都師范大學表現性油畫高研班進修。2015年至今工作于廣西藝術學院美術學院油畫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八零油畫學社成員。
2013年作品《椅子之十五》入選2013年全國油畫作品展,2015年作品《石桌與傘》入選2015吳冠中藝術館全國油畫作品展,2017年作品《物語》入選色彩中華——2017·中國百家金陵畫展(油畫),2018年作品《孤枕》入選最繪畫——第三屆中國青年油畫作品展,2018年作品《物語》入選第六屆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2019年作品《物語》入選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2019年作品《物語》獲第九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