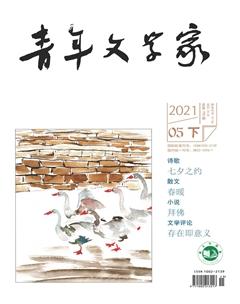李白詩歌中的憂患意識研究
李晨曦
談及對李白的評價與印象,總離不開“浪漫主義”四個大字。事實上,李白并非如眾人想象的一般,心中只有無盡的想象與豪情,他同樣也有心思細膩、心懷家國的一面。他的政治抒情詩,一方面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抱負,想在政壇上展示一番作為,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當權者與弄權者的諷刺與嘲弄。豪放、雄奇固然是詩人在天才創作上的表現,但是結合詩人的時代閱歷,其政治抒情詩則深刻地反映出詩人對于家國、時代的憂患。
一、李白詩歌憂患意識的時代背景
李白一生都處于唐朝盛世,這正是封建社會發展到高峰的頂點,唐朝政治軍事強大、文化繁榮昌盛,放眼世界也是“萬國來朝”的存在。盛世之下所誕生的李白,其浪漫主義與時代背景和社會風氣極其契合。另外,在繁榮的背后,封建社會也隱藏著各種社會危機、階級矛盾和潛在問題,而當時能夠敏銳發現這一點的人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李白作為一個天才型的創作者,他比別人更為敏銳地發現到了王朝可能走向衰敗的跡象,因此他開始創作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詩,對當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社會景象進行直觀呈現。而這也是詩人對人民、對家園憂慮關切的深層次原因。相較于他人而言,李白看問題的角度更為奇特,所反映出的時代問題與矛盾也更為深刻、更加接近本質,他的政治抒情詩其實就是整個封建社會開始逐漸走向沒落的預言詩。
二、李白詩歌憂患意識的產生
李白出身在富裕家庭,少年時便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二十歲便在詩壇中嶄露頭角,因此他自幼就有建功立業的政治理想,具有較高的政治抱負。他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寫“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即體現了自己的遠大抱負。李白在性格上有自負、輕狂的一面,因此他不愿意通過科舉出仕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隨后他做出了一個“仗劍去閣,辭親遠游”的驚人決定。此后,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他走遍大江南北,廣泛結交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通過漫無目的游歷來提升個人見識、開闊個人視野,也讓他對社會百態、民生百事有了一個清醒而完整的認識,其政治思想也逐漸變得成熟了起來。
天寶元年,即公元742年,四十二歲的李白終于得到了貴人相助,經推薦被皇帝招至長安供奉翰林。初入仕途的他當時還對封建統治者抱有一定的幻想,天真地認為自己能夠一展遠大抱負,但此時已經接近時代動蕩變革的轉折點,統治者昏庸無能,對李白這樣的人才根本不看重,在認識到現實情況之后,詩人失望地離開了,并繼續自己的游歷生活。正是這次入奉翰林的經歷,讓他對封建統治者徹底失望,也讓他開始認識思考當下社會和國家可能正在遭遇的危機。
三、李白詩歌憂患意識的具體體現
(一)揭露黑暗的社會現實
開元二十三年,李白游歷至東都洛陽,在客居期間,他親身目睹了統治階級的腐朽與驕奢,這讓他感覺非常的憤慨,由此寫下了一系列政治諷刺詩歌。在《古風》十八中,他寫“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通過寫老百姓對封建官僚避之不及,從側面反映出官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如此之低,人們對其是何等懼怕。官僚回家后,家中的景象是“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統治者們在外作威作福,在家則沉迷于尋歡作樂、紙醉金迷之中。詩人通過寫實的筆法表達了對統治階級荒誕無度生活的無情批判。此外,在《古風》四十六中,“斗雞金宮里,蹴鞠瑤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詩人通過寫宮廷內部的斗雞、蹴鞠的游戲,將其作為統治者腐敗的具體表現,王公大臣成天沉迷于這種于國無益、于民無助的游樂之中,逐漸沉淪至腐朽的深淵。此外,當朝統治者唐玄宗偏愛弄臣李林甫,而李林甫為了壯大勢力不斷地排除異己,陷害打擊正直人士,李白的好友張九齡、李邕、裴敦復等均遭受牽連。這件事讓詩人進一步地看清了當權者的真面目,進一步揭示了封建王朝腐朽統治的罪惡本質。在《古風》五十一中,他寫“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女媭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通過寫歷史上殷紂和楚懷王兩個昏君,暗指當時的社會現實,意圖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這里要注意的是,殷紂和楚懷王在歷史上都是亡國之君,李白此刻已經敏銳地發覺了形勢十分危急,如果不及時采取行動,唐朝很有可能步前朝后塵,自己可能淪為亡國之民。這已經是極其嚴重的警告了,而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詩人寫“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在哀悼好友李邕、裴敦復的同時,又毫不留情地怒斥了李林甫等奸佞小人。在當時小人得志的環境下,詩人直指統治者,體現出極大的勇氣。
(二)批判禍國殃民的權臣
李林甫死后,楊國忠掌握了國家大權,安祿山掌握了大部分兵權,皇權旁落,禍迫眉睫。面對即將發生的歷史劇變,詩人通過作品進行了提前預測。在《遠別離》中,詩人寫“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通過借用娥皇、女英的傳說典故,表達了詩人對于政壇小人得道、權勢熏天的擔心與焦慮。面對即將到來的風暴,處于風暴中心的唐玄宗卻渾然不知,只有詩人自己在“雷憑憑兮欲吼怒”,在痛苦中“慟哭兮遠望”。安祿山在發動叛亂前,已經權傾朝野,而卻鮮有人能夠揭露他的真面目。李白深知安祿山權力太大,勢力日益壯大,必然有叛亂的傾向,因此他在詩中寫“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較為隱晦地點出了安祿山的狼子野心,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正是當朝者養癰成疾、養虎為患的結果。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李白對高力士的不滿與揭露,在《古風》二十四中,詩人寫“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云開甲宅。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宦官們氣焰囂張、只手遮天,統治者沉淪玩樂之中,棄才不用,反而一味重用高力士等阿諛奉承的小人。《古風》五十四中寫“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以蒼榛作為喻體來比喻當朝小人,諷刺奸佞小人把持朝政、胡作非為,而有才有智的“瓊草”在黑暗現實中只能被迫隱居在深谷之中,甚至居無定所、無所依靠,整個社會已經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境地。面對如此情況,詩人不由得發出“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憤慨,這種憤慨既是在表達個人的憤怒,同時也代表著整個士人階層郁郁不得志的悲哀無助。
(三)反對非正義性戰爭
在斥責奸佞弄臣的同時,李白還在詩歌中體現出鮮明的反戰傾向,直接揭露了戰爭的殘酷和非正義性。對于唐玄宗窮兵黷武的軍事政策,詩人認為這是一種破壞民族團結民主平等的不義戰爭。對于直接參與軍事行動的軍事將領哥舒翰,詩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寫“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赤裸裸地指出了哥舒翰的加官晉爵,是用千萬在邊境戰斗的寶貴生命、千萬無辜老百姓的鮮血所換來的。事實上,在唐朝的開放的社會思潮中,戰爭并不會招致人們的憤恨,然而由統治者所主動挑起的不義之戰,將會受到像李白這樣的有志之士的無情批判。天寶十三年,楊國忠為一己私利,不顧犧牲將士,持續發動戰爭。對于這種草菅人命、自私自利的行為,李白在《古風》三十四中寫“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描寫了將士在戰場的凄慘景象,而這一切都是當朝者一手造成的。唐玄宗的窮兵黷武,一方面削弱了唐朝大國的整體國家實力,造成內防空虛,讓安祿山有機可乘;另一方面也直接導致民族關系惡化,讓國家與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而當時能夠看到這一點的,只有包括李白在內的寥寥數人。直至安史之亂正式爆發,一切的走向都與詩人的擔心憂慮不謀而合。
四、結語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曾經繁榮昌盛的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走上了衰敗的道路。安史之亂是封建王朝歷史上由盛轉衰的重要轉折點,而動亂的產生有其時代必然性,由于統治者的麻木不仁,由于奸佞弄臣的肆意妄為,由于眾多有志之士無法為國家為人民做更多貢獻,直接導致整個國家命運的改變。詩人李白在詩歌中的憂患終于變成了現實,這既是詩人利用事物發展規律所做出的科學預測判斷,也是結合自身人生經歷在觀察社會洞悉人性上所做出的努力。作為時代巔峰的弄潮兒,李白在王朝最繁榮的時候,能透過表面的假象深刻認識到背后的政治腐敗本質,進而覺察出封建社會盛極必衰的歷史發展趨勢,這就讓李白比同代詩人在思想上境界上要高出一個層次,也在追求浪漫主義的同時,進一步展示出自己詩歌具有現實性與批判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