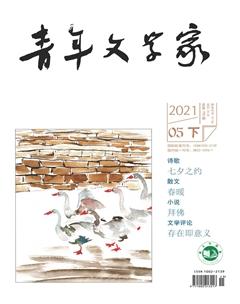語言與文本的突破
羅薇
西方思潮從柏拉圖開始就將語言問題視為和哲學、藝術等諸多領域密切聯系的重要問題。推翻形而上學的統治,解除精神危機,反思存在的意義,追尋安身立命的根本,這一切都需要通過解決語言問題來實現。法國近代思想史上,雅克·德里達是一位頗具爭議的哲學家、思想家。1967年德里達開始了他對語言的解構。在哲學和文學雙重涵養的助力下,德里達勇敢嘗試,在后現代主義思潮下,開展對語言與文本的交織、互動研究,實現了文學與哲學的跨界,使得他的理論和影響不僅在大西洋彼岸掀起了巨浪,也對歐洲的人文學科產生了綿延不斷,惠及后來的學者和研究領域的積極效應。
一、語言問題和身份之“他者”
雅克·德里達是阿爾及利亞人,卻操著一口流利的法語。德里達捍衛法語的純正,也捍衛了語言背后承載的意義。他對于語言的本質抱有很大的興趣,對語言的要求也甚為苛刻。這跟德里達的生存處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對語言的追尋,也可以說是對自我身份認同的求索。他極少回憶過去,對自己的身份問題保持警惕,在法國他成為了別人眼中的他者,他擁有“他者”的語言。對他者的搜尋將語言他者的范圍擴大化。相似的情況發生在德里達談論“未來民主”時,“未來民主是一種用‘仿佛(as if)、‘也許(phehaps)、‘可能(might, would, could)等微弱話語表達的一種許諾,一種祈禱,一種期待,一種責任,它指向他人、面臨他人以及應答他人。”(胡繼華,2019,13)這個他人他者,可理解為可能性的第三者。這跟后現代主義的特征契合,可能便是突破了語言的界限,走向更具變數的未知之路。再看解構,如同德里達的理解,“解構是他者的語言,是事件的如實發生,是既定結構的消解。”(陸揚,2008,403)這便回到了結構主義走向解構主義的旋律,在后現代主義的席卷下重新審視一切觀念的主旨。
二、后現代主義的語言和跨界的文本
后現代語境下一切遭到否定,實現了不破不立。這是由“語言”所引發的哲學思辨和文學行動。有學者評論德里達的學說“解構主義反映了后現代主義精神并構成了他的底色”。(李世濤,2015,2)在《論文字學》的第一章開門見山地將語言問題宣告給讀者:“不管人們如何理解,語言問題也許從來就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問題。但與今天不同的是,它過去從未像現在這樣滲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領域以及在意向、方法和思想體系方面千差萬別的話語之中。”(德里達,2015,7) 這是德里達的重要觀點,也是他研究鋪設的起點,通往討論文學和哲學主要路徑,他并不止步于過去的探尋挖掘,而是將語言坐標投遞到未來,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以語言的論述作為焦點,并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德里達在文學和哲學之間的盤旋,使得他對文本的場域也不囿于傳統的認知。在德里達看來,文本可表達的內容已經超越了文本自身。這是一種主觀的活動,卻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就像在文學和藝術史上,盡管有些人并沒有處在后現代思潮的場域里,也不屬于所謂的“后現代主義者”,但他們同樣具備了后現代的特征—尋求跨界表達,看似凌亂的表層,實則有不拘一格的深刻內涵。他們通過文本來表達的不僅是作者的所思所想,更多的是啟迪了新的意象。
三、德里達的后現代文本觀
德里達后現代文本觀首先受到的滋養源自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引導他走向了思辨的道路。而身處后結構主義的他,也受到了語言學家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影響。索緒爾通過差異性來辨析語言系統,通過能指和所指,繼承了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二元對立的傳統,這使得他自己無可避免地肯定了邏各斯中心主義。這正是德里達批判和解構的核心。德里達否定了索緒爾的固定范式,“被索緒爾視為文字專有特征而加以抑制的距離性、說話人不在場、容易引起誤解曲解、含混不清且查無對證等性狀,德里達認為說到底正是語言本身最為本質的特征。語言并不那么透明溫順。它的實質與其說是直傳邏各斯的言語,莫若說是蒙障重重的文字。”(陸揚,2018,24)德里達的文本理論在美國得到廣泛傳播,影響了一批文學理論家。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米勒視德里達的“解構說”就成為文學批評的一個新走向。德里達在自己多部作品中針對各位大師進行了解構活動,甚至“在通過文學技巧促使我們了解語言的物質性的時候,德里達迫使我們去留意我們的閱讀行為”。(K.馬爾科姆·理查茲,2016,82)針對文本的解構,可以看作是他對閱讀行為的定義,因為他的文本理念從不局限在文本的內部。“德里達將文本與傳統意義上的作品區分開來,將文本變成解構的網絡,變成延異的場所,以此進入文本以及文本之外的文本當中,在追尋詞語間和文本間蹤跡的過程中了解得更多。所以,在他看來,寫作其實就是一種嵌入和增生的過程,它引起更多的詞語和文本,文本就是各種不同的聯結和嵌入的產物,充滿巫術的蹤跡和延異。而閱讀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活動,讀者必須把這些無限的蹤跡作為閱讀的前提和焦點,從中去找尋嵌入的其他文本和詞語所擴張的意義,閱讀的真諦便在其中。”(劉象愚等,2002,288)
四、語言與文本突破的終極目標
德里達曾試圖不斷擺脫形而上學和二元對立的圈套。當德里達趕赴德國沿襲胡塞爾的現象學時,卻被喬伊斯的另類文本所深深吸引,喬伊斯給德里達以深刻的啟迪,與其說“沒有喬伊斯,就沒有解構”,不如說“沒有喬伊斯的創作角度,就沒有德里達的文本理念”。喬伊斯的創作手法“通過‘隱喻性語言、歧義和修辭的堆砌,讓世界在自己的文本中保持其無限的復雜性”。(李永毅,2016,13)德里達認為突破語言的方式應該是放棄它本來說話的方式,就像喬伊斯的作品那樣抽象、斷裂、接續,而具備濃厚的后現代主義特征。德里達后來的寫作文本晦澀、難以理解,但他堅信可以通過語言打破西方的二元對立,在《白色的隱喻》中他將文學從二元對立的桎梏中解救出來。采取解構傳統路徑—語言,破除了歐洲白種人自居為人類中心的神話。不過想要擺脫形而上學也并非易事,德里達曾坦言最好的辦法同時也是最難的方法,則是“在語言形式上放棄它的說話方式,不再利用任何形而上學的概念,但是德里達像列維·斯特勞斯一樣承認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尚杰,2008,312)而后現代主義思潮席卷之時,德里達的語言問題獲得契機。語言成為一個靈活可變的問題,它是社會晴雨表,更是文學溫度計。而依靠著語言所產生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體現了諸多思想的共存和文學文本形式的多樣。“后現代社會的各種語言游戲,不但不會導致傳統社會的統一性和有利于統治階級進行控制的那種共識,而且有利于促進和推動社會中的各個成員的特殊性,有利于社會的多元化發展。”(高宣揚,2016,42)
五、結語
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在本質上是一個語言存在物。海德格爾也曾將探討語言視為探討把人“帶到語言的本質的位置”。德里達則通過語言問題來給后現代主義定了基調,是文學與哲學的雙重謀劃者。他的論述不僅滲透到了人文社科領域,同時以自己獨特的視角,敏銳的觀察,生發出自己獨特的理論。語言問題使得他從學科的局限中解脫出來,同時形成了具有明顯后現代意味的文本觀。該文本觀結合了語言游戲和解構策略,十分具有德氏個人的特點。德里達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傳統文本的認識,也改變了文學作品的閱讀和詮釋方式。他的思想不僅影響了西方人文社科的走向,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疆域變得更為廣闊。
基金項目: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資助,項目編號:19GWCXXM-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