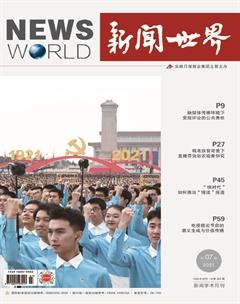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困境、機制與價值捍衛
○付詩迪
新媒體時代,網民圍觀的力量日益凝聚,價值取向、利益意志、文化層次等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可以在網絡空間中合理發表自己的觀點,網民的話語權顯示出愈發強大的力量。有學者認為,新興媒體逐步普及后,互聯網的平民精神使得“人人皆是媒體人”,傳統由職業媒體人掌握“媒體話語權”的格局被打破……“人人皆媒”的時代來臨。近年來的網絡熱點事件,如“山東高考冒名頂替事件”、“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等,大多是通過微博、微信、抖音、公眾號等網絡平臺發聲、發酵成為熱點,促進了事件的發展和解決。
傳統媒體(報刊、廣播、電視等)已經面臨著“內憂外患”。然而,面對網絡帶來的影響,傳統媒體試圖通過調整新聞生產機制來適應變化,而且逐漸把握了主動權。本文對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現實困境與機制調整進行分析,探討傳統媒體在新媒體的沖擊下健全機制、捍衛價值、與時俱進的可能性與發展空間。
一、傳統媒體的困境:新媒體的挑戰和話語權的消解
自網絡誕生以來,關于新媒體與傳統媒體關系的討論就不絕于耳。隨著網絡傳播影響力的擴展,消解了傳統媒體信息壟斷的權利和信息發布的權威性,改變著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機制,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競爭也越發激烈。傳統媒體的現實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傳統媒體的保守性
西方傳播學研究傾向于認為,大眾傳播具有相當的保守性,而網絡公民傳播則更具解放性,能拓展大眾傳播的視角和觀點,使報道更加與普通公民相關。
在《草根媒體》(We The Media)一書中,丹·吉爾默對大眾傳媒的保守性加以詬病:“我絕對肯定的是現代新聞業的機制正在被一種危險的保守主義培養著——而商業影響更甚于政治影響”。部分西方學者認為,主流媒體的運作有固步自封的傾向,政治立場、商業利益等影響下的傳統媒體,似乎一直忽視普通公民的聲音,而網絡傳播則更為包容和多元化,甚至迫使傳統媒體關注邊緣話題。
研究者熱情洋溢地宣告著網絡時代的公民記者對傳統大眾傳播壟斷權的消解力量、對主流媒體的改造力量,似乎在發表自媒體時代公民記者的“獨立宣言”:“媒體已經變得沒有網絡那么重要,而互聯網正變成人們信息來源的關鍵”。這種新媒體取代傳統媒體的說法,在學界并不鮮見,“由于網絡,大眾媒體把關人的角色不復存在,信息變得自由,媒體的壟斷被無情的拋棄”。
(二)傳統媒體報道的模式化
傳統媒體報道的“模式化”所帶來的問題同樣得到學者的關注。學者蓋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在對傳統媒體“新聞網”(News Net)的研究中曾指出,記者慣于用一些非常嚴格的框架去建構新聞,對議題形成一些“報道模式”,而這些模式可能會使記者獲得錯誤的結論,從而成為報道的阻礙。英美的新聞學研究者不斷指出,新聞機構為了有效率地生產新聞內容,沿用一套既定的模式、常規和框架來報道議題,這種報道具有一定重復性,所以,新聞機構對處于社會邊緣位置的人群的聲音,或是社會和文化的轉變的觸覺并不一定很敏銳。
這種模式化的報道在我們的傳統媒體中并不鮮見,模式化有利于記者面對新聞迅速撰稿進行報道,操作性強,不易出錯,但缺乏創新,且部分報道中的“日報體”“八股文”“官話”“套話”的反復使用也經常被公眾詬病。與之相反,網絡傳播的議題更多帶著強有力的情感動員和如臨其境的觀察視角,充分調動網民愛、恨、憤怒、悲傷等情緒,所以有觀點認為,“公民新聞帶著一種強有力的感情深度和第一手的經驗,比模式化、遠距離觀察的主流媒體報道要有力的多。”
(三)傳統媒體技術相對落后
部分學者更加關注新技術本身的力量,即新技術對舊技術的取代可能。他們從技術決定論的視角認為,“與傳統媒體技術相比,新興媒體技術有著強大的更新迭代能力,如新近出現的AR、VR、人工智能技術、5G 技術、區塊鏈技術、物聯網技術等,這些新興技術時常都是對原有技術的重大推進甚至是顛覆性創新”。在新媒體時代,智能手機廣泛普及,從博客、微博、微信到抖音、快手,新模式新技術層出不窮,可供個人表達的網絡平臺不斷拓展,傳統媒體早已不再是公眾唯一的選擇。部分研究者不但對傳統媒體的技術落后進行批判,甚至已經開始為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形式的消亡預寫訃聞,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學界對傳統媒體面臨危機的肯定態度。
(四)記者和自由撰稿人之間的界限被打破
網絡時代用戶也可以成為作者,同時新聞被報道的速度越來越快,已經能夠同步報道、實時直播,這體現了傳統媒體權力的分散和網絡用戶被賦予更多的話語權。傳統媒體記者感受到來自新媒體的競爭壓力,受眾日益增長的信息獲取需求與傳統媒體內容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顯現。在這種趨勢下,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保持著一種競爭的態勢——發布時間的競爭、受眾的競爭、話語權的競爭,乃至公民權利的競爭。網絡的互動性使更多人能夠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于是,自網絡興起后,“新聞”儼然已經變成全民的事業。

(五)傳統媒體在網絡熱點事件中處于滯后狀態
熱點事件大多起源于網絡,通過網貼、微博、視頻、公眾號等傳播,形成一次次網絡狂歡。在“山東高考冒名頂替事件”中,普通人上大學的機會多年前被冒名頂替,被頂替者一般為普通群眾,缺乏話語權,他們多選擇在網絡發聲,逐步引發網友的關注,進入熱搜榜,以尋求政府部門的重視,進而引發有關部門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和問責,收獲“遲到的正義”。傳統媒體在這一事件的報道中處于相對滯后狀態。有研究認為,新媒體改變了傳統媒體在議程設置方面的權威性,甚至開始獨立設置自己的議程。
這很像是一種新的競爭,勢單力薄的個人可以通過網絡所賦予的話語權來制造表達空間,甚至引發廣泛關注的網絡熱點事件。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媒體對新聞議題的介入落后于新媒體,網絡傳播使以往不易被關注的議題進入傳統媒體的視野,擴展了公眾言論表達的空間。
由以上分析,可以歸納出部分研究者面對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關系時的態度: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權威性和話語權正在被不斷挑戰,使以往被邊緣化的民間議題重新進入公眾視野。由此,網絡賦予了普通公民新的角色,互聯網越來越成為民意表達的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個過程中,新媒體不僅是傳統媒體的補充,甚至已經對保守化、模式化的傳統媒體的權利起到了消解作用,兩者呈現一種競爭關系。
二、完善新聞生產機制:傳統媒體的介入、調整與改變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和對網絡熱點事件傳播規律的不斷總結,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等都紛紛開通微博、微信、客戶端、頭條官方號,開始向網絡傳播拋出橄欖枝。傳統媒體逐漸適應了新媒體時代的信息傳播趨勢,推動自身融合發展,進行內部新聞生產機制的調整和改變。
(一)堅持把關人機制
網絡賦予了普通民眾話語權,同時也帶來了公眾的“信息焦慮”——“不斷增長的社會信息量遠遠超出了個人或系統信息處理能力的極限,這是產生信息焦慮的根源”。有學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公民記者對新聞作品的制作與傳播行為就容易出現因專業知識的缺乏導致客觀性缺失的現象,新聞事實的真實性逐步受到質疑,這也成為目前公民記者最為人詬病之處。流傳于網絡的信息,易陷入非理性和真假難辨的境地。在部分情況下,網民的情緒表達類似于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述的“群體”——“聚集成群的人(即群體)擁有一些普遍特征:易受慫恿、輕信、易變,把良好或惡劣的感情加以夸大、表現出某種道德感等……”可以說,在群體中“同感情對抗的理性往往蒼白無力”。在一般情境下,網民面對一則涉及公權濫用的網絡新聞時,往往會表現出憤怒和輕信,拒絕理性的分析;而一旦出現某種證據顯示“受害者作假”或“信息有誤”,輿論又迅速轉向,攻伐謾罵的對象即刻改變。
網絡發布的信息易陷入混亂和非理性的情境,不具備傳統媒體的可信度,傳統媒體的把關人機制意義凸顯。網絡海量的信息使人感到焦慮而難以集中注意力,有觀點認為,“現在權力不是掌控在那些生產信息或者保有信息的人手里,而是掌握在那些能鑒別并驗證信息的人手里”。傳統媒體通過信息的篩選、核實、把關,對網絡議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為公眾撥開迷霧、呈現事實的真相,對消解“信息焦慮”起到了不容小覷的作用。所以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把關人角色依然舉足輕重。
(二)主動調整新聞生產流程
隨著網絡熱點事件被報道次數的增多,傳統媒體應對網絡事件的挑戰時,不再一味的被動,在特定的情境下,傳統媒體開始吸納網絡傳播,調整其新聞生產流程來適應變化,以便更好地引導輿論。
傳統的新聞生產流程包括新聞策劃(尋找線索)、采訪、編輯制作和播發,記者發現或接受新聞線索是其中重要一環。以往的新聞線索來源受限于記者的經驗和渠道,網絡無法成為新聞生產的參與者。然而,在對網絡事件的觀察中可以發現,經過短暫的適應期后,傳統媒體形成了對網絡事件的快速吸納機制,使網絡成為傳統媒體的新聞線索來源,被納入傳統媒體常規化報道。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逐漸掌握了網絡傳播的規律,通過調整自身新聞生產流程,在網絡熱點事件苗頭初現之時,傳統媒體記者便已經枕戈待旦,介入網絡議題的報道。網絡成為傳統媒體的常態化新聞來源。另一方面,網絡熱點事件的傳播也在悄然適應大眾傳媒時代的信息傳播規律,信息發布者往往從被動等待傳統媒體的關注,轉換為主動吸引媒體的目光、為媒體提供信息源,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也成為促成網絡熱點事件的關鍵步驟。
這更像是大眾傳播對網絡的“馴化”,使來源于網絡的信息符合大眾傳播的報道框架和議程,將原本具有能動性的網絡熱點事件納入傳統媒體的模式化報道框架。在這場博弈中,傳統媒體開拓了報道議題的范圍,將網絡信息源轉化為傳統媒體新聞生產的一部分,可謂傳統媒體對網絡新聞進行了“收編”。
(三)完善融合傳播機制
面對新媒體的沖擊,傳統媒體依托資源、人才、平臺的傳統優勢,開始建設自身的新媒體平臺。開通微博、微信和客戶端,創立新聞網站,傳統媒體逐漸實現從單一發布平臺到綜合性發布平臺的轉化,并針對不同平臺特點進行分眾化、差異化傳播,不斷完善自身的融合傳播機制。通過這種主動調整來實現對網絡新聞更實時的關注、更快速的審核、第一時間的發布,使傳統媒體能夠沖在網絡熱點事件的報道一線。
有研究者肯定了“媒體循環”或“媒體共鳴”在網絡熱點事件發展中的重要性。所謂媒體循環,是指“當媒體互相引用對方的內容時,產生的便是一種雪球效應,推動著事件的發展和膨脹”。與之類似,媒體共鳴是“在一些關鍵議題中,媒體報道則可能形成‘共鳴’,由專業主義傾向媒體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對這兩個概念的研究,表明了在網絡熱點事件的發酵過程中,傳統媒體介入的時機和媒體融合報道的程度有重要影響。在“山東高考冒名頂替事件”、“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等議題中,均可見“媒體循環”和“媒體共鳴”效應,起源于網絡的新聞熱點,被傳統媒體關注和進一步報道,實現網絡、報刊、電視、廣播等多渠道融合傳播,同時由專業媒體作為“意見領袖”,從而獲得更高的社會關注度。傳統媒體的介入和融合傳播大大提高了網絡事件的公共知名度,從而使議題影響的范圍從網絡拓展到全社會。
綜上,傳統媒體通過堅持把關人機制、主動調整新聞生產流程、完善融合傳播機制等方式彌補著自身不足,從內部對傳統的新聞生產機制進行改革,使其適應網絡傳播特點,并開始探索在新媒體時代的更多可能。
三、捍衛主流媒體價值:傳統媒體調整轉變的現實意義
與部分研究者認為傳統媒體具有保守性、落后性、模式化不同,本文認為,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機制在調整適應中與時俱進,他們并未忽略來自民間的聲音,也不曾面對網絡熱點事件的沖擊而無能為力,反而積極發掘議題、拓展議題,主動利用網絡,給“民間表達”創造更多的機會。通過自我調整,使傳統媒體在這場競爭中實現角色轉變,掌握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主動權。傳統媒體,尤其是改革中一馬當先的中央級主流媒體,能夠在新媒體時代進一步做強做大主流輿論,推動自身融合發展,捍衛作為傳統主流媒體的價值。
(一)身份轉換:為新媒體設置議程
新媒體議程設置的能力存在一定局限性。雖然由網民發布的涉及權益維護、不文明現象的微博、網貼、視頻等會獲得網友的支持和關注,但由于缺乏媒體介入、無法自行判斷真相、網友熱情減退以及網民力量不足等原因,最終大多議題將沉寂于網絡,網友對此情況有過形象而無奈的表述“一直在圍觀,從未有力量”。而傳統媒體的介入彌補了這一缺憾,傳統媒體將網絡作為新聞源成為一種新聞機制后,就可以于浩瀚的網絡議題中挖掘有價值的信息,甚至以往錯失的議題。部分議題經由傳統媒體發掘、報道,在網絡引發熱議,如2020年7月的網絡熱搜議題“央視曝光刷單兼職騙局”:刷單騙局由來已久,關注度不足,其線索來源于網絡,一經央視報道,微博閱讀量迅速過5 億,相關討論微博6 萬余條,獲得高度關注,成為傳統媒體設置的“網絡熱點”。經統計,2021 年1-3 月,由央視報道引發的微博熱搜話題近100 個,亦佐證了主流媒體發掘網絡議題、為新媒體設置議程的主動性。
傳統媒體通過機制調整實現了身份轉換,從被動追逐網絡議題變為主動設置議程,挖掘網絡線索,使之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甚至已經將網絡作為固定的新聞來源,開拓了傳統媒體常規化報道的新空間。
(二)流程調整:深度介入網絡議題發展
本文并不否認網絡新媒體在擴大“民間表達”空間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網民用持續的關注所形成的合力,同樣可以形成強大的網絡議題。大眾傳媒機構“不再控制和決定公眾的知情權,這是大眾媒體和公眾關系上發生的主要變化”。對于一些在介入前已經在網絡引起熱議的議題,傳統媒體的報道重點從新聞的發布轉移到新聞的解釋,對事實的核實、對真相的解讀、對官方回應的尋求,通過種種途徑,深度介入議題的發展。在“山東高考冒名頂替事件”等網絡議題中,網絡議題已經炒得火熱,而傳統媒體大多在議題的上升期介入其中,通過持續跟進的報道帶來“媒體共鳴”,參與到推動議題成為輿論熱點事件的過程中。
面對網絡謠言,傳統媒體同樣被期待通過核實并放大理性的聲音,消除網絡不理性的因素,澄清謠言,將議題的真相呈現給公眾。這也是傳統媒體面對網絡傳播時,被認為扮演最多的一種社會角色。調查核實于新聞報道并不鮮見,但涉及到網絡議題時,“轉載”似乎成為更普遍的報道策略——單純的轉載網貼、抄襲網文,或者播報網絡上的“口水之爭”,如名人之間的罵戰等,不需要采訪取證。時至今日,依然有自媒體是如此操作的。網上的真假之辨,觸目驚心;網上理性的聲音,被淹沒在不理性的謾罵攻伐中,海量的信息使人焦慮,真假難辨,這就需要一個信息窗口來告訴公眾哪些信息更為可靠。傳統媒體的客觀公正和專業性符合公眾的期待,這也是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時代實現自身價值的有效方式。
(三)內容定位:擺脫娛樂化傾向,注重新聞價值
目前,騰訊、新浪、今日頭條等大型網絡媒體參與報道網絡議題的嘗試并不鮮見,甚至引起的關注足以與傳統媒體抗衡。但在對議題的選取中,他們大多呈現出一種娛樂化的傾向,這類似于關注網絡“八卦隱私事件”的范圍,關注明星、性、八卦、隱私,通過“標題黨”“擦邊球”吸引受眾的點擊。為了吸引眼球,其他媒體中類似的涉及網絡八卦隱私領域的報道也不在少數。這些議題關注娛樂化和窺私欲,但對拓展公共領域和言論空間毫無價值。傳統媒體的介入,能夠走出關注隱私、娛樂八卦的誤區,為拓展社會公共領域服務。傳統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主動參與報道的網絡議題,更多是關注權益維護、經濟訴求、社會問題的民間表達的聲音,這類議題最有可能成為“網絡熱點事件”,引起社會的關注,對于社會發展、媒體本身的專業性都有裨益。
(四)受眾引導:依托公信力穩定網絡輿情
部分網絡熱點事件中,傳統媒體的及時介入可促進事態的解決,引導網友理性思考,消除輿情的不穩定因素。傳統媒體的介入,一方面向社會公眾表示了對議題的關注和態度,如在“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中,《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守住公共安全底線”和“嚴肅問責問題疫苗”的態度;另一方面依托傳統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促進有關部門的回應,并對有關部門的介入和調查結果進行持續跟進,推動網絡熱點事件的最終解決。這對網民的情緒具有安撫的作用,有利于輿情的穩定。
(五)平臺拓展:搭建技術領先的新媒體平臺
在搭建自有新媒體平臺方面,傳統媒體早已不甘人后。2019 年,三臺合并后的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建立了綜合性視聽新媒體平臺“央視頻”,也是中國首個國家級5G新媒體平臺,在新聞報道中使用“5G+4K/8K+AI”技術的嘗試更是站在了新技術應用的前沿,一舉改變了公眾過去對傳統電視平臺的認知。2021 年2 月1 日,中國首個8K 電視超高清頻道CCTV 8K 成功試驗播出,央視春晚也首次采用8K 直播,更體現了傳統媒體進軍新領域的決心。
這與以往研究中“新技術取代舊技術”造成傳統媒體被取代的觀點完全不同,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技術的應用方面同樣可以走在前列,亦有可能通過其自身的全媒體采編播發平臺、技術資源優勢和專業報道方式去深度影響網絡熱點事件的走向。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未否認新媒體傳播對整個媒介生態體系改變的力量,只是探討在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新聞生產機制的調整和適應過程。我們不必過于強調新媒體本身的力量,或者將兩者作為對立面而強調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和消解的能力,在對網絡熱點事件的觀察分析中,很少看到傳統媒體完全缺位的例子。傳統媒體已不再是被動地適應,而是與時俱進、主動調整,健全自身新聞生產機制,避免網絡傳播非理性和娛樂化的缺陷,促進網絡熱點事件的發掘、發展和穩妥解決,甚至可能走在技術革新的前列,捍衛著身為傳統主流媒體的價值。可以說傳統媒體的主動適應和機制調整,推動了自身的融合發展,切實提高了在新媒體時代的傳播力、引領力、影響力、公信力,已經顯現出其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