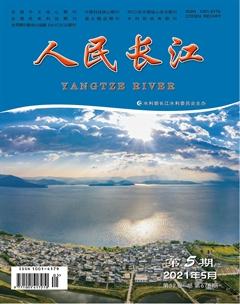贛江尾閭碟形湖水體季節性分布特征
劉星根 譚志強 范宏翔



摘要:碟形湖是鄱陽湖濕地的一類重要組成部分。贛江尾閭(中支)碟形湖分布廣泛,地形和鄱陽湖水位變化共同造就了水體空間分布的季節性差異。為進一步了解碟形湖的形態特征和水體的空間分布情況,基于湖區5 m分辨率的數字高程模型提取了碟形湖地形,構建了主要碟形湖的水位-面積-容積曲線,以汛后期潴水型典型年2014年為例,基于Landsat 8遙感影像分析了典型水文時期贛江中支三角洲的碟形湖水體分布變化。結果表明:三角洲上游和下游的碟形湖形態差異明顯;碟形湖四周高、中間低、深度較淺的地形特征導致其可以容納的水量不及2億m3;在秋季退水期和冬季枯水期,碟形湖水體占三角洲水體覆蓋的70%~90%,是越冬候鳥棲息的重要濕生環境。
關 鍵 詞:
碟形湖; 形態特征; 水位-面積-容積曲線; 遙感影像; 鄱陽湖; 贛江
中圖法分類號: P343.5
文獻標志碼: A
DOI:10.16232/j.cnki.1001-4179.2021.05.011
0 引 言
碟形湖是鄱陽湖主湖區周邊分布的許多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碟形洼地,高水位時與主湖區水面連成一片,為通江水體的組成部分;低水位時被周圍較高的自然淤地、人為圩堤等與主湖區隔離,成為暫時獨立的小水體,也稱為季節性內湖、小湖或湖中湖。碟形湖的自然形成與入湖水沙變化、湖水位漲退有關[1]。河流攜帶水沙進入平坦的三角洲平原,分汊水系把流域來水來沙輸送到出口,分汊河道之間的洼地在洪水季節承納洪水,流速緩滯,泥沙在河道兩岸天然堤淤積,河道往下游延伸發展;當分汊河道在下游匯合或者在湖區趨向封閉,洼地形成封閉的碟形湖[2-3]。
碟形湖是鄱陽湖洪泛區的重要組成。季節性的流域來水、長江干流水位對鄱陽湖的頂托和拉空作用,共同導致了鄱陽湖水位的季節性變化,平均變幅達到10 m,從而在湖區形成面積約3 000 km2的洪泛區[4-5]。鄱陽湖洪泛區由五河入湖河道、灘地和近百個碟形湖組成[1]。贛江中支尾閭、贛江南支位于湖區西南側,地形開闊、平緩,泥沙進積空間大,分汊河道和幾十個碟形湖構成三角洲景觀,河床深約3~8 m,碟形湖地形高程11~14 m,共同組成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碟形湖是在自然與人為活動雙重作用下形成的重要生境,其水位受到人為調控,形成了不同于通江水體的水位變化過程,為濕地植被發育、越冬候鳥棲息提供了良好的生境條件。碟形湖在維護鄱陽湖濕地生態系統完整性和物種多樣性上起到了十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鄱陽湖濕地草洲總面積約2 200 km2,碟形湖區占到23.09%,全湖沉水植被的54%分布于碟形湖中[1]。在水環境方面,碟形湖是入湖水流進入常年積水區的過渡帶,對鄱陽湖水環境具有一定的凈化作用。碟形湖滯納的洪水在退水后期自然或人為排泄到鄰近河道或湖盆,延緩了鄱陽湖水面萎縮速率,而且經過碟形湖調蓄的湖水中營養鹽、污染物濃度可能比三角洲頂端更低[6-8]。碟形湖群也加劇了鄱陽湖洪泛水文的復雜性[4-5]。已有研究表明,因湖泊水位季節性漲退,碟形湖與主湖水體在湖泊高水位時連通,在湖泊低水位時地表水體斷開聯系[9]。另外,贛江尾閭分汊河道是水沙輸移的重要通道,但在高水位時,碟形湖容納了大部分的洪水,同時碟形湖的流速可能遠遠小于河道流速,有可能是泥沙沉積的優先區域。
碟形湖的形態特征和水體的空間分布是進一步認識其在鄱陽湖洪泛水文中的作用,以及碟形湖生態服務功能的基礎。本文根據鄱陽湖區的地形、遙感影像和湖區水位以及文獻調研信息,探討贛江尾閭碟形湖的形態和地形特征,估算碟形湖的水位-面積-容積關系,分析典型時期碟形湖的水體分布,以期為碟形湖生態水文研究和鄱陽湖濕地管理提供支撐。
1 研究區域
贛江在外洲站以下分4支入湖,其中贛江北支和贛江中支在朱港農場匯合,本文研究區為贛江北支和中支匯合后形成的贛江中支尾閭區(以下統稱贛江尾閭,見圖1)。研究區氣候特征為熱量豐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氣溫17.7 ℃,最冷月1月平均氣溫5.1 ℃,最熱月(7月)平均氣溫29.6 ℃;多年平均降水量1 450~1 550 mm,主要集中在4~6月[10]。研究區土壤類型為草甸土、草甸沼澤土和水下沉積物。地形高程約為11~14 m。受流域來水和長江水位的雙重影響,贛江尾閭具有年內季節性高變幅的水情。豐水季節水草豐盛,是魚類天然產卵場和育肥地,枯水季節洲灘出露,形成的碟形湖、發育的草洲為越冬候鳥提供了優良的生境。研究區優勢植被群落為苔草群落、蘆葦群落、蓼群落等[10]。
3 結果分析
3.1 碟形湖分布與地形特征
贛江尾閭的主要碟形湖共14個(見圖1與表2),主要分布在干流河道右側,其地形平坦,地勢開闊,泥沙易于淤積;干流左側為圩堤(成朱聯圩),河道分汊少,泥沙淤積空間受限。碟形湖主要分布在分汊河道之間,研究區右側的分汊河道從上游往下游依次是雙嶺河、明溪河、龍譚里,研究區分汊河道更為發育。雙嶺河與明溪河之間發育大沙坊湖、邊湖、泥湖3個碟形湖,明溪河與龍譚里之間發育銘溪湖、門池洲,其他9個碟形湖分布在龍譚里以下的三角洲平原上。
贛江尾閭的地形、泥沙淤積和水文情勢共同構成了碟形湖發育的基礎,上游和下游的碟形湖在形態上存在顯著差異(見表2)。贛江尾閭上游河道附近的碟形湖面積較大,平均為11.6 km2,平面形態接近圓形或橢圓形,如大沙坊湖、泥湖、上段湖;而下游的碟形湖面積偏小,平均為3.2 km2,平面形態趨向狹長形,以草魚角湖、飯湖和贛江尾閭最明顯(見圖1)。
碟形湖的平均高程在10.7~13.5 m(見表3),上游河道附近的碟形湖高程高于下游的碟形湖。岸堤的平均高程在11.8~15.1 m,比碟形湖平均高程高出約1.6 m,碟形湖的深度較淺,大約在0.7~2.5 m。碟形湖四周高、中間低,由于岸堤較矮,碟形湖的容積非常小,其中大沙坊湖的容積最大,達4 495萬 m3。贛江尾閭碟形湖可以容納的最大水量僅有1.78億 m3。
3.2 碟形湖水位-庫容曲線
碟形湖面積占贛江尾閭的42%。基于各個碟形湖的DEM數據,可以估算不同水位下的碟形湖面積和容積。考慮到14個碟形湖的地形特征類似,選取了4個碟形湖分析其庫容曲線,分別是大沙坊湖、泥湖、上段湖和飯湖。
碟形湖的水位-面積-容積曲線呈現共同的特征。以大沙坊湖為例,水位低于11.5 m時,水面面積極小;水位在11.5~12.5 m時,水面積隨水位上升而迅速增加;當水位上升到13.5 m時,水面達到最大值,當水位在14.5 m時,水量幾乎達到最大值,可見大沙坊湖湖盆高程主要在11.5~14.5 m。泥湖湖盆的高程主要在11.0~13.0 m,上段湖、飯湖的湖盆高程與泥湖類似(見圖3)。根據DEM對碟形湖的高程-面積結構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表明碟形湖的高程在10~15 m之間,其中12~13 m范圍的面積最大,約占所有碟形湖總面積的35%。
水位-面積-容積曲線顯示,當水位低于13.0 m時,碟形湖水面面積與水位呈正相關,湖泊呈現河相特征;當水位高于13.0 m時,碟形湖面積與水位相關性極差,此時呈現湖相。這種關系在湖泊大斷面圖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見圖4)。圖4可見碟形湖的湖底最低高程一般在10~11 m之間,碟形湖圍堤高程一般在13~15 m之間。由于地形差異和鄱陽湖的水文節律,碟形湖有著不同于鄱陽湖通江水體的水文過程特征,與鄱陽湖的水位關系總體表現為“高水位相連、中水位相關、低水位分離”的特點。
3.3 典型水文時期碟形湖水體景觀
贛江尾閭位于鄱陽湖洪泛區,水體的空間分布受鄱陽湖季節性水位變化控制。鄱陽湖水位呈現漲-豐-退-枯的階段性特征。春季漲水使湖水位上漲、入湖河道水面拓寬,贛江尾閭分汊河道的水文連通性增強,碟形湖水體也受降水和地下水影響而逐漸增長,碟形湖與河道的連通性逐漸恢復。夏季的高水位狀態下,河道-灘地-碟形湖共同承納湖水,融為一體。秋季后的湖泊水位快速下降導致地形較高的灘地和碟形湖岸堤出露,水文連通性減弱。枯水期,碟形湖與河道阻隔,碟形湖的水位變化主要受當地漁民調控。
以2014年5幅影像為例,分析贛江尾閭碟形湖和河道水體景觀的變化(見圖5)。漲水前(2014年以1月25日為例,星子水位7.7 m),碟形湖水面面積占研究區水體的70%(見表4),河道水體局限在干流和部分支流。碟形湖水深較淺、水面寬闊,維持了枯水季節的濕生環境,3個較大的碟形湖水體均位于贛江尾閭的上游,包括銘溪湖、大沙坊湖和泥湖(見圖5(a))。春季贛江中支入流增加,導致河道水面擴張,同時鄱陽湖水位整體上升,下游和末端的灘地和碟形湖被淹沒,與枯水季節相比,下游的碟形湖水體數量明顯增加(見圖5(b)),碟形湖水體面積由枯水季節的約26 km2增加到43 km2左右。夏季鄱陽湖水位持續升高,河道、碟形湖、灘地均被湖水淹沒(見圖5(c))。秋季退水期,鄱陽湖水位快速削落,灘地整體性出露,河道水體漸窄,碟形湖岸堤出露(見圖5(d)),由于碟形湖四周高、中間低的地形特征,此時碟形湖容納的水體與河道水體斷開了地表水力聯系,碟形湖的水量變化主要取決于當地漁民的調控。與漲水期相比,此時碟形湖水體數量更多,水體覆蓋面積更大。2014年枯水季節(見圖5(e)),碟形湖水體面積仍然維持在50 km2(見表4),碟形湖水體數量與退水期(2014年10月24日)相當。總體上,碟形湖與鄱陽湖主湖表現為低水阻隔、高水連通的水體景觀特征。圖6記錄了碟形湖與星子站2015~2016年水位變化,水位變化也反映了碟形湖與鄱陽湖主湖的水體連通關系:1~3月和9~12月水位較低,碟形湖與通江水體不連通;4~8月水位較高,碟形湖與通江水體連通。
4 討 論
4.1 碟形湖的形態差異
碟形湖分布在贛江尾閭分汊河道之間。分汊河道岸堤不斷往前延伸,當兩股分汊河道再次相遇時即可形成碟形湖。在贛江尾閭上游,碟形湖的形態多呈近似圓形,面積較大,而下游碟形湖面積較小,多呈狹長形。原因可能是贛江尾閭上游河道分汊少,分汊河道間灘地空間較大;下游河道分汊頻繁,分汊角更小,分汊河道間灘地空間受限;另外自上游往下游,分汊河道不斷把干流水沙分配到各支流,減少了贛江尾閭下游河道岸堤的泥沙補給,不利于碟形湖形成。贛江尾閭上游和下游的碟形湖的形態差異還表現在形狀因子上,上游各碟形湖的形狀因子較小,而靠近贛江尾閭末端的幾個碟形湖,飯湖、草魚角湖(見圖1) 的形狀因子均較大,表明下游的碟形湖與周圍水體的接觸比上游碟形湖更大。
4.2 碟形湖水體分布與候鳥棲息
碟形湖的地形特征表現為四周高、中間低。這種“淺碟型”特征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碟形湖岸堤平均高程與湖底高程之差僅有約1.6 m,碟形湖的平均深度約為0.7~2.5 m,碟形湖水面面積和容積的變化范圍局限在特定的水位區間(見圖3)。針對候鳥的野外調查發現,碟形湖是候鳥棲息和覓食的主要場所之一[17-19],這可能與碟形湖的地形特征有關。贛江尾閭大部分碟形湖湖底高程在10.0~13.0 m,碟形湖岸堤高程約為11.0~14.0 m。星子站的水位一般在4月達到14.0 m,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碟形湖與湖盆水體逐漸連通,9月末碟形湖開始與湖盆水體斷開了地表水流聯系。由于大部分碟形湖平均深度較淺,碟形湖在退水期和枯水季節維持了面積寬闊的濕生環境,10月份初越冬候鳥開始遷入南磯濕地,適宜的水深、豐富的濕地植物根莖、淺水湖泊中的魚蝦為候鳥覓食提供條件。
碟形湖作為候鳥棲息和覓食的適宜生境可能與水位變化過程密切相關。據前人研究,枯水期碟形湖水位逐漸下降,碟形湖向下漸次形成淺水和泥灘帶,不斷滿足候鳥取食的需求,是冬候鳥維持棲息和覓食的重要條件[2]。10月初至10月底或11月初,最佳棲息水位為星子站14.0~13.0 m;11月初至12月初,最佳水位為12.0~10.0 m;此后至候鳥飛離,水位不低于8.0 m,或短時間(3~5 d)低于8.0 m,不影響候鳥棲息[20]。2014年退水期的水位變化過程與上述吻合,10月平均水位13.5 m,大部分碟形湖出露,11月份平均水位11.6 m,12月份平均水位9.7 m,碟形湖維持了一定比例的濕生環境。據報道,2014年越冬候鳥數量達到53萬余只[21]。
碟形湖受到人為活動的影響較大,比如湖區漁民的水產養殖(中華絨毛蟹)對水生植被破壞極大,經調查:養殖3 a以上中華絨毛蟹的水體,高等水生維管植物幾乎完全被破壞,沉水植物幾乎滅絕,嚴重影響了湖泊生態功能[1]。碟形湖的水位也與人類活動相關。南磯濕地保護區內的20多個碟形湖均已承包給漁民[22]。漁民對碟形湖水量的調控可能是部分碟形湖水體覆蓋變化的關鍵,進而影響候鳥棲息和覓食環境。斬秋湖漁民承包者基本上從10月份開始每天打開閘門放水捕魚,湖池的水經壕溝排往大湖區,魚被截留在閘扣的魚網內。當水位放到一定位置時,形成新的泥灘和水陸交替地帶為越冬候鳥覓食和棲息提供了條件。隨著斬秋湖的繼續放水,水位過低可能導致水鳥賴以為食的水生植被、浮游、底棲微生物等資源的衰竭,使有效的覓食面積減小。至1月份左右碟形湖水體覆蓋最少,魚蝦等餌食消失,濕地根莖等資源耗竭,越冬候鳥數量較少[22-23]。
盡管如此,碟形湖對鄱陽湖濕地生物多樣性保育仍然具有重要作用,通過江湖關系研究成果[14-15,24],可以看出三峽水庫蓄水后面臨低枯水位加劇,歷時延長的水文情勢,但鄱陽湖生物多樣性受影響不大,越冬候鳥數量變化并不明顯,原因是碟形湖承載了81%的冬候鳥[1],其地形特點決定了這一性質。比如文獻[25-26]研究表明,鄱陽湖中部湖區濕地植被呈現顯著的旱生化趨勢,而碟形湖的植被群落結構變化相對較小。碟形湖以及臨近的稻田、水塘等是近10 a來越冬候鳥頻現的熱點區域[22,27]。長江與鄱陽湖存在顯著的江湖相互作用,這種作用對鄱陽湖主湖區通江水體影響較大,尤其是三峽水庫運行后秋冬季長江水位偏低、鄱陽湖出流增強,導致主湖區通江水體快速萎縮;由于碟形湖的地形特征,秋冬季碟形湖水體與主湖區通江水體暫時隔離,江湖關系變化對碟形湖的水文過程影響相對較小,此時碟形湖是越冬候鳥棲息的重要生境。因此江湖關系調控應該充分考慮碟形湖的水文和生態功能,比如秋冬季碟形湖維持一定比例的濕生環境對越冬候鳥棲息具有重要意義。
5 結 論
贛江尾閭是鄱陽湖洪泛區的重要組成。通過文獻調研、遙感技術、地理信息技術等分析了贛江尾閭碟形湖的形態、地形和水體分布特征。
研究結果表明,碟形湖地形特征和湖泊水文節律共同決定了碟形湖水文過程的獨特性:高水位時碟形湖與通江水體連通,低水位時與通江水體隔離。考慮到三峽水庫運行以來,湖泊秋冬季干旱開始時間提前、持續時間增加等趨勢,碟形湖作為鄱陽湖重要組成部分和獨特的水文系統,是延緩湖區干旱對濕地生態系統威脅的重要地帶,對維持穩定的植物群落和越冬候鳥種群具有重要意義。今后應進一步深入研究面向碟形湖群和濕地生態保育的江湖關系調控,為鄱陽湖濕地保護和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參考文獻:
[1] 胡振鵬,張祖芳,劉以珍,等.碟形湖在鄱陽湖濕地生態系統的作用和意義[J].江西水利科技,2015,41(5):317-323.
[2] 胡振鵬,葛剛,劉成林.越冬候鳥對鄱陽湖水文過程的響應[J].自然資源學報,2014(10):1770-1779.
[3] YAO J,ZHANG Q,LI Y L,et al.Hydrological evidence and causes of seasonal low water levels in a large river-lake system:Poyang Lake,China[J].Hydrology Research,2016(47):24-39.
[4] ZHANG Q,WERNER A D.Hysteretic relationships in inundation dynamics for a large lake-floodplain system[J].Journal of Hydrology,2015(527):160-171.
[5] ZHANG X L,ZHANG Q,WERNER A D,et al.Characteristics and causal factors of hysteresis in the hydrodynamics of a large floodplain system:Poyang Lake (China)[J].Journal of Hydrology,2017(553):574-583.
[6] 王小玲,高柱,余發新,等.鄱陽湖南磯水生植物年周期變化及重金屬污染現狀分析[J].北方園藝,2014 (24):57-62.
[7] 劉倩純,胡維,葛剛,等.鄱陽湖枯水期水體營養濃度及重金屬含量分布研究[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2,21(10):1230-1235.
[8] 杜彥良,周懷東,毛戰坡,等.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對水質環境影響研究[J].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學報,2011(4):249-256.
[9] 馮文娟,徐力剛,范宏翔,等.梅西湖與鄱陽湖水位變化關系及其水量交換過程分析[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43(4):83-88.
[10] 紀偉濤.鄱陽湖:地形、水文、植被[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50.
[11] LIANG M,VAN DYK C,PASSALACQUA P.Quantifying the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river deltas under conditions of steady forcing and relative sea level rise[J].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Earth Surface,2016,121(2):465-496.
[12] 譚胤靜,于一尊,丁建南,等.鄱陽湖水文過程對濕地生物的節制作用[J].湖泊科學,2015,27(6):997-1003.
[13] ZHANG Q,YE XC,WERNER A D,et al.An investigation of enhanced recessions in Poyang Lake:Comparison of Yangtze River and local catchment impacts[J].Journal of Hydrology,2014(517):425-434.
[14] LIU Y,WU G,ZHAO X.Recent declines in Chinas largest freshwater lake:trend or regime shift?[J].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2013,8(1):014010.
[15] LIU Y B,WU G P,GUO R F,et al.Changing landscapes by damming:the Three Gorges Dam causes downstream lake shrinkage and severe droughts[J].Landscape Ecology,2016,31(8):1883-1890.
[16] 劉元波,吳桂平,柯長青.水文遙感[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17] WU G,LIU Y.Seasonal water exchanges between China's Poyang Lake and its saucer-shaped depressions on river deltas [J].Water,2017,9(11):884.
[18] 齊述華,張起明,江豐,等.水位對鄱陽湖濕地越冬候鳥生境景觀格局的影響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14(8):1345-1355.
[19] 胡斌華.鄱陽湖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越冬候鳥調查與分析[D].南昌:江西農業大學,2013.
[20] 戴星照,胡振鵬.鄱陽湖資源與環境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
[21] 劉芝毅.鄱陽湖:逾57萬只候鳥來了[N/OL].江西日報,2017-12-30[2020-05-03].https:∥ijx.ifeng.com/6268930/nens.shtml?srctag=Pc2m&back.
[22] 郭恢財,李琴,胡斌華,等.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建設對自然保護區候鳥棲息地的影響[J].環境科學與技術,2016 (9):181-186.
[23] 李琴,郭恢財.鄱陽湖“斬秋湖”水位調控方式對湖泊濕地的影響及啟示[J].濕地科學與管理,2017 (3):27-31.
[24] 邴建平,鄧鵬鑫,張冬冬,劉昕.三峽水庫運行對鄱陽湖江湖水文情勢的影響[J].人民長江,2020,51(3):87-93.
[25] HAN X,CHEN X,FENG L.Four decades of winter wetland changes in Poyang Lake based on Landsat observations between 1973 and 2013 [J].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2015(156):426-437.
[26] HAN X,FENG L,HU C,et al.Wetland changes of China's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and their linkage with the Three Gorges Dam [J].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2018(204):799-811.
[27] 何文韻,邵明勤,植毅進,等.鄱陽湖三個墾殖場的水鳥多樣性[J].生態學雜志,2019,38(9):2765-2771.
(編輯:江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