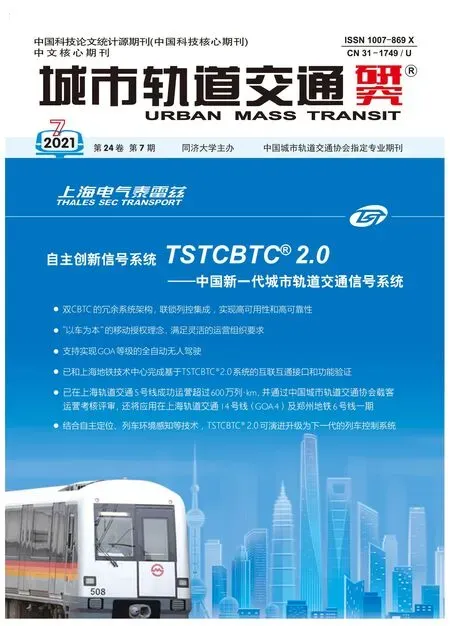深圳市居民出行結構演變特征分析及公共交通發展政策啟示
周 軍 馬 亮
(深圳市規劃國土發展研究中心, 518040, 深圳∥第一作者, 高級工程師)
1 研究對象及數據來源
深圳市2010年、2016年2次居民出行大調查[1-2]結果表明,大規模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并未明顯提升公共交通(以下簡稱“公交”)分擔率,城市軌道交通在促進公交優先、緩解交通擁堵上的作用受到質疑。如圖1所示,相比2010年,2016年深圳市的城市軌道網絡規模達到285 km(增加了263 km),公交分擔率(圖1中城市軌道交通、道路公交的比例之和)基本穩定在38%左右,而私人小汽車的出行分擔率不降反升。

圖1 2010年和2016年深圳市居民出行結構對比
公交分擔率是考核公交優先的重要指標[3],但僅從深圳市域范圍統計得到的單一數值變化來推導城市軌道交通在城市公交發展中的作用有失偏頗,應掌握不同空間尺度的居民出行結構演變特征,以客觀評估城市軌道交通的作用。本文基于深圳市2010年和2016年2次居民出行大調查的數據,從宏觀、微觀2個層面研究該市居民出行結構的空間演變特征。
本文的研究以深圳市域為研究對象,覆蓋了全市10個行政區,其中:羅湖區、福田區、南山區為中心城區;鹽田區、寶安區、龍崗區、龍華區、光明區、坪山區、大鵬新區為外圍區。研究數據源自該市2次居民出行調查數據,分別獲取了2010年9.8萬戶居民(共計22.0萬人)及2016年6.5萬戶居民(共計15.4萬人)的工作日出行數據。數據字段包括出發地、到達地、出發時間、到達時間、出行目的、出行方式,以及居民家庭收入、家庭擁有的私人小汽車數量、個人職業、個人年齡等信息。2次交通調查的分區不同,2010年將深圳全市域劃分為532個交通小區,2016年劃分為1 134個交通小區。為便于比較,本次研究統一采用2010年劃分的532個交通小區予以分析,如圖2所示。

圖2 深圳市行政區劃及交通小區劃分
2 深圳市居民出行結構演變特征
在宏觀層面,對深圳市中心區、外圍區分別分析區域內部、區域之間的居民出行結構演變特征;在微觀層面,以居民1次出行的出發地為準、以交通小區為單位進行研究,分析各交通小區的出行方式結構及變化,并采用核密度法分析各種交通方式出行分擔率的空間演變特征。
考慮到機動化交通出行數據精度較高,本次研究不考慮慢行交通,并將機動化交通方式分為城市軌道交通、道路公交、私人小汽車、出租車、班車、摩托車/助動車等類別。其中,班車指企業接送員工上、下班的車輛。
2.1 宏觀層面的出行結構演變特征分析
1) 中心區內部呈現出私人小汽車與公交均衡發展的特征。如圖3所示,私人小汽車分擔率、公交分擔率基本穩定,但公交內部的出行結構變化較大。與2010年相比,2016年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由1.1%增長到17.2%,道路公交分擔率則由39.8%下降至24.6%。這主要是由于城市軌道交通基本覆蓋中心城區,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小汽車的發展。

圖3 2010年和2016年深圳市中心城區居民內部出行結構對比
2) 外圍區內部呈現出以私人小汽車主導的發展特征。如圖4所示,與2010年相比,2016年私人小汽車分擔率由41.0%增長到48.7%,道路公交分擔率則由34.4%下降至26.3%,而城市軌道交通的分擔率僅為5.4%。這主要是由于該市的發展重心逐漸向外圍區轉移,外圍區內部出行需求總量、居民收入、私人小汽車的擁有量均快速增長,而城市軌道交通在外圍區的發展較為緩慢,道路公交在運行速度、舒適性方面無法滿足居民不斷提高的出行要求,導致私人小汽車快速發展。

圖4 2010年和2016年深圳市外圍區居民內部出行結構對比
3)中心區與外圍區之間呈現出以城市軌道交通為骨干、公交主導發展的特征。如圖5所示,與2010年相比,2016年公交分擔率由42.3%增長到47.4%,尤其是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由0大幅增長至28.7%,成為公交出行的主要方式;相應地,私人小汽車的分擔率由46.2%下降至39.3%。這主要是由于在聯系中心區與外圍區的交通設施能力整體不足的背景下,城市軌道交通設施持續增加,而道路設施未明顯增長且道路擁堵加劇,公交相比私人小汽車在運輸能力、速度上取得一定優勢。

圖5 2010年和2016年深圳市中心城區與外圍區之間居民出行結構對比
2.2 微觀層面的出行結構演變特征分析
本文按交通小區尺度對比2010年和2016年的道路公交、城市軌道交通、私人小汽車分擔率變化情況,并結合圈層分析深圳市居民出行方式的空間演變規律。如圖6所示,一圈層指羅湖區、福田區、南山區3個原特區內的行政區;二圈層指外圍地區鄰近一圈層分布的街道;其它地區定義為三圈層。采用核密度法分析城市軌道交通、道路公交、私人小汽車這3種交通方式在出行分擔率上的空間演變特征,研究結果表明:出行分擔率演變在空間上整體呈圈層分布特征,但受各交通方式自身特點、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布局、居民交通出行需求等因素的影響,出行分擔率還呈現出差異化的變化趨勢。
2.2.1 道路公交分擔率分析
如圖6所示,一、二圈層的道路公交分擔率呈整體下滑趨勢,尤其是位于二圈層的民治、坂田等街道,其道路公交分擔率降幅超過40.0%;而在三圈層城市軌道交通尚未覆蓋的部分區域,道路公交的分擔率仍在增長,如沙井、觀湖、平湖、葵涌等街道的道路公交分擔率增幅基本在15.0%以上。通過分析道路公交明顯增長地區的居民收入和私人小汽車擁有量,發現這些地區的戶年均收入增長率、私人小汽車擁有量增長率分別為132.0%、7.4%,明顯低于全市155.8%、16.3%的平均水平,說明該類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普遍較慢,道路公交方式對于收入較低人群仍有較大的吸引力。

圖6 深圳市道路公交分擔率空間演變特征
2.2.2 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分析
如圖7所示,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的增長在空間上與全市軌道交通網絡布局高度耦合,并與城市軌道交通的線網密度正相關,呈由內向外逐圈層遞減的特征。一圈層中的羅湖區和福田區的軌道線網密度最高,其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平均增幅為18.9%,南山區的軌道線網密度低于羅湖區和福田區,其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平均增幅為16.0%;二圈層主要通過軸向放射的城市軌道交通線路與外圍的城市軌道交通5號線(環線)進行服務,其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平均增幅為13.1%;三圈層中軌道交通3號線沿線的分擔率相對較高(約為10.0%),軌道交通11號線在本文開展研究時剛開通不久,其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增長較少。此外,在城市軌道交通線路尚未覆蓋的地區,通過道路公交與城市軌道交通接駁,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略有增長。

圖7 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空間演變特征
2.2.3 私人小汽車分擔率分析
如圖8所示,私人小汽車分擔率的增長在空間上基本分布在與城市軌道交通線網距離較遠的區域。一圈層的軌道線網密度較高,私人小汽車分擔率普遍下降,但在福田中心區、南山科技園等主要就業中心區域,私人小汽車分擔率仍有小幅增長;二圈層人口密度高、出行需求大,城市軌道交通設施的供給相對不足,私人小汽車分擔率普遍增長;三圈層居民收入、私人小汽車擁有量增長較快,且有城市軌道交通未覆蓋的區域,私人小汽車分擔率增長較快。

圖8 深圳市私人小汽車分擔率空間演變特征
3 交通分區發展評估
本文綜合考慮各種出行方式在空間上的演變特征,對深圳市分區交通發展進行評估,以掌握不同區域交通發展的差異化特點,為制定公交發展政策提供參考。
3.1 兩步聚類分析法
聚類是按照事物間的相似性進行區分和分類的過程。兩步聚類法是一種綜合的層次聚類方法,能自動選擇聚類數[4]。將2010年和2016年的城市軌道交通、道路公交、私人小汽車分擔率分別兩兩相減,按交通小區尺度獲得這3種交通方式分擔率的變化情況。將數據輸入統計軟件后進行兩步聚類分析,得到貝葉斯(BIC)算法結果如表1所示。表1是得到深圳市交通方式最佳聚類的分析過程,其中:第1列表示聚類分析后的類別數量,即分析過程提出了10個備選方案;第2列的BIC值是基于貝葉斯準則對每個分類計算聚類判據;第3列BIC變化值是當前的BIC值減去前1個序號的BIC值得到的差值;第4列BIC變化率是當前BIC變化值與二類聚類BIC變化值(表1中的-217.987)的比率;第5列是距離測量比,主要用于衡量分組間的差異程度,其值越大,表明分組間差異越大,分組效果越好。

表1 深圳市交通方式自動聚類分析過程
最佳的聚類結果要求BIC值較小,且BIC變化率和距離測量比較大,因此最佳方案確定為4類,如表2所示。

表2 深圳市交通方式最終聚類分布結果
3.2 評估結果
根據兩步聚類分析結果,如表2和圖9所示,深圳市交通分區發展可以分為4類:
1) 城市軌道交通優勢發展區。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平均增長率為26.3%,道路公交、私人小汽車分擔率均下降,這類區域主要分布在城市軌道交通線網密度較高的城市中心地區,以及鄰近一圈層的民治、布吉等街道區域。

圖9 深圳市交通分區發展評估
2) 道路公交優勢發展區。道路公交分擔率平均增長率為18.1%,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略有增長,私人小汽車分擔率下降較多,這類區域主要分布在三圈層城市軌道交通未覆蓋且經濟發展較慢地區,在全市空間分布最少。
3) 私人小汽車優勢發展區。私人小汽車分擔率平均增長率為23.4%,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略有增長,道路公交分擔率下降了17.9%,這類區域主要分布在二圈層交通出行強度較大地區,以及三圈層城市軌道交通未覆蓋但經濟發展較快地區。
4) 交通平衡發展區。道路公交、城市軌道交通分擔率略有增長,私人小汽車分擔率略有下降,交通出行結構基本維持穩定,這類區域主要分布在南山區城市軌道交通未覆蓋地區,以及三圈層城市軌道交通沿線地區。
4 對深圳市公交發展政策的啟示
4.1 現狀政策的不足
4.1.1 公交發展目標“一刀切”
公交發展目標“一刀切”、政策分區劃分較籠統,未體現該市不同地區交通發展的差異性。市內不同地區的交通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性,應制定差別化的交通發展目標,如上海市在2002年制定的《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書》中針對城市的中心區、外圍區、郊區提出了差別化的交通目標值[5],而深圳市僅在全市層面提出了在2020年實現客流高峰期機動化公交分擔率65%的目標[6]。
在政策分區劃分方面,深圳將全市劃分為6大公共交通分區,但各分區的交通發展特點不突出。此外,同一個分區內部還存在著居民出行強度、公交發展水平不同的區域,部分分區的交通發展特點又較為類似。例如,西部濱海分區橫跨城市軌道交通優勢發展區、私人小汽車優勢發展區、交通平衡發展區3類地區;東北分區、西北分區比較類似,主要包括私人小汽車優勢發展區、交通平衡發展區2類地區。
4.1.2 外圍區城市發展較快,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相對滯后
在城市軌道交通方面,深圳市提出要在2020年前完成城市軌道交通三期工程建設,大幅提升外圍區城市軌道交通的線網密度。但是,實際的城市軌道交通線路建設相對滯后,導致未能按預期引導外圍區出行結構向以城市軌道交通為骨干的公共交通轉移,而較快的經濟發展使私人小汽車得到普及,私人小汽車分擔率持續增長,公交分擔率下降。
4.2 公交發展政策建議
1) 建立適應當前深圳市交通發展特點的精細化交通政策分區。結合全市交通分區發展評估結果,全市分為城市軌道交通優勢發展區、私人小汽車優勢發展區、道路公交優勢發展區、交通平衡發展區等4類交通政策分區,分區單元面積為2~5 km2。為便于政策的具體落實,可進一步將空間單元進行合并與重新劃分。
2) 制定全市及分區層面的公交發展目標。不同分區的空間區位、出行強度、軌道交通線網密度、道路條件等差異較大,在全市總體公交發展目標的基礎上,應制定分區層面的差異化發展目標,引導公交有序、穩定發展。
3) 建立適應分區特點的公交體系結構。一、二圈層與三圈層在經濟發展、出行強度、交通發展要求等方面差異明顯。二圈層以內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交通出行強度高,城市軌道交通基本覆蓋,但在軌道交通線網密度較低的區域私人小汽車仍發展較快,公交優先的關鍵是能否提供足夠的城市軌道交通服務能力。因此,一、二圈層應確定城市軌道交通的主體地位,在高密度居住區、就業區與主要客運走廊應提高城市軌道交通的線網密度,在空間上做到全覆蓋;道路公交作為補充,主要為大運量城市軌道交通喂給客流。三圈層的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交通出行強度一般,在城市軌道交通未覆蓋的區域,道路公交在與私人小汽車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城市軌道交通沿線地區公交與私人小汽車基本平衡發展,公交優先的關鍵是是否有城市軌道交通。因而,三圈層應構建以城市軌道交通為骨干、道路公交為主體的一體化公交體系,通過公交接駁間接實現城市軌道交通在空間上的全覆蓋。
4) 建立適應分區特點的公交發展路徑。針對分區公交體系構建目標,并結合城市軌道交通的發展水平,一二圈層應主要通過加密城市軌道交通線網、改善慢行接駁環境等措施提升城市軌道交通的服務能力和服務品質;三圈層主要通過新建城市軌道交通線路、加強公交接駁等方式提高城市軌道交通的覆蓋范圍。
綜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深圳市4類交通發展區的公交發展政策建議,如表3所示。

表3 深圳市4類交通發展區的政策建議
5 結語
掌握居民出行結構的空間演變規律有利于客觀認識不同交通方式在綜合交通發展中的定位與作用,科學指導公交發展政策制定。本文從宏觀、微觀2個層面分析了深圳市2010年和2016年居民出行結構的空間演變特征,發現城市軌道交通、道路公交、私人小汽車分擔率演變在空間上基本呈圈層差異化分布。基于兩步聚類分析法,將深圳市劃分為4類交通發展區,在分析現狀公交發展政策不足的基礎上提出現階段公交發展的政策建議。由于公交發展政策制定涉及因素較多,本文主要是從現狀交通發展評估的角度進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議,下一步應結合用地開發、交通設施發展等規劃因素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以滿足公交的近遠期發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