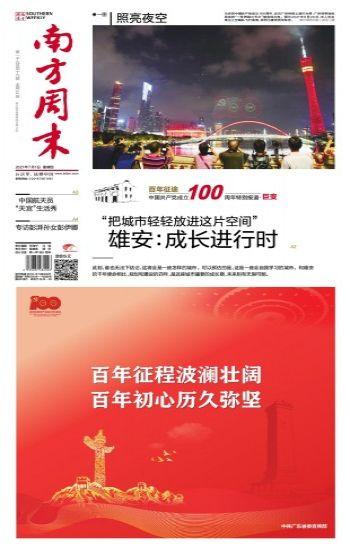被日本“拉黑”,小龍蝦無辜嗎?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易永艷 魏翠翠 南方周末記者 黃思卓

2020年中國小龍蝦產業總產值約為3448.46億元,超過2020年青海省的GDP。
視覺中國?圖
★20世紀初,小龍蝦第一次離開原生區域美國后,一條路線入侵日本、中國等亞洲地區,另一條路線入侵歐洲、非洲等地區。
盡管小龍蝦早被列為外來入侵物種,但關于小龍蝦對生態環境的利弊之爭從未停止。一派認為,應加強小龍蝦等入侵物種生態防控,尋找有效控制小龍蝦種群的方法;一派認為,小龍蝦已融入本地生態系統,應從外來入侵物種名單上剔除。
下一步應該思考如何既保持小龍蝦產業的發展,又采取適當的措施防控生態危害的出現,在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間尋找平衡。
對于很多人而言,唯有來上一份鮮香可口、汁水四濺的小龍蝦,才算不辜負這個夏天。
但日本恐怕無法認同這個觀點。2021年7月7日,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日本環境省于7月6日召開了一次專家會議,基本同意將小龍蝦定為外來入侵物種,2022年日本環境省將向國會提交修改法案,可能2023開始正式監管,屆時日本將禁止進口、銷售和野外放生小龍蝦。
截至7月20日,南方周末記者尚未在日本環境省官網查詢到與該提案相關的正式文件。不過,日本擬將小龍蝦指定為外來入侵物種的消息已在中國引起熱議,新浪微博的相關熱搜話題閱讀量接近1.8億。
外來物種入侵已成為頗受關注的全球性環境變化問題之一,隨著人類活動范圍擴張,一些物種隨之擴散到自然分布范圍以外的地方,并對當地的生物多樣性、人類健康和經濟構成威脅或損害。
此前,歐盟于2016年把小龍蝦列入入侵性外來物種名單,限制其飼養、進口、銷售、繁衍和養殖。
日本環境省此次將要“拉黑”的小龍蝦是克氏原螯蝦,因原產地在美國,也被稱為美國小龍蝦。據《朝日新聞》報道,外來的克氏原螯蝦在日本多地擴散泛濫,威脅日本的本土物種,對農作物等也有明顯損害。
中國夜宵之王小龍蝦也主要是克氏原螯蝦,2020年中國小龍蝦產業總產值約為3448.46億元,超過2020年青海省的GDP。
一邊是蓬勃發展的產業經濟,一邊是入侵物種的防控壓力,亦正亦邪的小龍蝦正陷入尷尬的境地。
為什么被“拉黑”
這不是日本第一次動議將小龍蝦列為外來入侵物種。
2015年3月,日本環境省和農林水產省編制的《防止生態損害的外來物種名單》中,小龍蝦就被定為“需要緊急應對的外來入侵物種”,并規定公眾在飼養小龍蝦時,需要遵守三項原則——不隨意放生、不隨意棄養、防止小龍蝦進一步擴散。
一位在湖北武漢留學的日本學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日本小孩子會把小龍蝦當作寵物飼養,所以日本家庭很少吃小龍蝦。“不過目前在日本也有一些年輕人吃小龍蝦,像日本的中華料理店里面就會賣小龍蝦。”
2019年,專注于海洋與淡水生態領域的英國期刊《Freshwater Biology》發表了一篇論文,論文勾勒了小龍蝦在全球范圍內的入侵路線——20世紀初,小龍蝦第一次離開原生區域美國后,一條入侵日本、中國等亞洲地區,另一條入侵歐洲、非洲等地區。
日本的小龍蝦最早作為牛蛙食物從美國引進,牛蛙養殖場關閉后,小龍蝦逃竄到野外繁衍。20世紀30年代,小龍蝦已傳播到東京、埼玉和千葉等地,1960年代擴散到除北海道以外的所有縣。
據日本環境省官網發布的一份解釋性文件《有什么問題嗎?砍掉所有水草》,小龍蝦造成的危害大致分為三類:對包括水生植物和水生昆蟲等在內本土物種的直接影響,通過種間相互作用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影響,以及將疾病傳播給本土物種。
舉例來說,由于美國小龍蝦入侵,日本石川縣金澤市海螯蝦棲息的池塘中,植被消失,海螯蝦滅絕;石川縣泥鰍養殖場里,小龍蝦的攝食直接導致泥鰍幼魚產量下降。
“生物之間存在生態位,特別像食物鏈上存在的競爭關系。外來入侵物種肯定會對本土物種生存產生影響。有的比本土的更強勢,就會使本地物種的生存受到威脅,甚至使得本土物種滅絕。”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魏開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一個外來物種在一個國土繁衍了近100年,應該屬于外來物種本土化了。”湖北省水產科學研究所正高職高級工程師舒新亞并不同意入侵之說,他數年前已經從單位退休,但從未停止關注小龍蝦的身份認定。
日本將小龍蝦列為外來入侵物種,亦在民間引發爭議。日本版雅虎新聞的評論區,即有日本網友擔憂:“如果禁止吃小龍蝦,反而會給人一種在保護它的感覺”。
前述《朝日新聞》報道,雖然到目前為止,將小龍蝦列為外來入侵物種這一規定還在討論之中,但是專家討論商定時并沒有很大異議。
如果此次小龍蝦被正式列入名單,不僅在進口、銷售環節會被嚴格監管,連飼養也需要得到國家許可。
被重創的小龍蝦產業
中國對小龍蝦的重視要更早。2010年,在原環保部和中科院制定的《中國第二批外來入侵物種名單》(以下簡稱“《名單》”)中,小龍蝦赫然在列。2019年《云南省外來入侵物種名錄》中,小龍蝦更被列為Ⅱ級嚴重入侵類生物。
《名單》指出,小龍蝦可通過搶奪生存資源、捕食本地動植物、攜帶和傳播致病源等方式危害土著物種。同時,《名單》還稱:“有研究發現,小龍蝦在預知和躲避敵害方面表現出比土著螯蝦更高的適應性。另外它喜愛掘洞筑巢的習性對泥質堤壩具有一定的破壞作用,輕則導致灌溉用水流失,重則引發決堤洪澇等險情。”
小龍蝦泛濫甚至威脅到自然保護區。據《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8期報道,在貴州威寧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小龍蝦的泛濫已成為一種災難。在保護區,小龍蝦打洞、吃魚蝦、水草、爛泥,多只小龍蝦聚在一起能夠吃掉近一尺長的魚類,水中各類蝦都逃不過小龍蝦的侵蝕,各種水草也淪為小龍蝦螯鉗下的食物。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江西省政協副主席李華棟建議長江禁漁期間加強小龍蝦等入侵物種生態防控,尋找有效控制小龍蝦種群的方法。實行養殖準入制,將距離江河、湖泊較近的養殖區搬遷等。
對于防治方法,《名單》規定,可通過投放野雜魚捕食克氏原螯蝦幼苗,以控制其種群規模。在尚未引種的地區,應展開其環境風險評估和早期預警,對已廣泛分布地區,加強養殖管理。
“相關管理部門有一些指導意見,對于小龍蝦的養殖量上有一定的限制,來控制可能的生態危害。養殖時不盲目追求規模,要考慮養殖區域的生態承載量,特別是養殖量和生態承載量之間的關系,以及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經過評估之后有計劃地投放。”魏開金解釋道。
2010年《名單》發布后,中國小龍蝦產業受到重創。一大批原本設在江蘇的小龍蝦加工廠開始倒閉,或搬遷到湖北。而《2019年中國小龍蝦產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2003-2010年,全國小龍蝦養殖產量穩步上升,只有在2011年顯著下降,養殖量從2010年的56.33萬噸直接降至48.63萬噸,同比下降13.67%。直到2013年,小龍蝦養殖量才恢復到《名單》發布前的情況。
“口腹之欲”vs“生態保護”
盡管小龍蝦早已被列為外來入侵物種,但國內關于小龍蝦對生態環境的利弊之爭從未停止。
在中國,小龍蝦基本以人工養殖為主,80%以上的小龍蝦被養殖在稻田里。一位家住湖北荊州的小龍蝦養殖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家從2012年開始養殖小龍蝦,并沒有覺察到外來入侵物種的負面影響,“銷售一年比一年好,有地方來瘋狂搶購,對農民來說是很不錯的收入”。
“作為人工養殖的商品或者食品,小龍蝦經濟效益頗高,人工也能干預控制數量,以防泛濫。但是從生物安全的角度來說,還是要把它列入外來入侵物種的管理當中,因為風險還是存在的。”魏開金也承認,現在小龍蝦養殖、餐飲市場的火熱和外來入侵物種的生物防控形成了一個“相對矛盾的局面”。
“你們聽說過哪里因為養殖小龍蝦而造成物種爆發或者水利農田、漁業資源的破壞沒有?”作為一個堅定的“保蝦派”,70歲的舒新亞認為很多國家和地區把小龍蝦當作敵害來應對,是在認識上還不夠全面深入。
“跟河蟹、大閘蟹等其他水產動物比起來,它們的破壞性并不是特別強,而且可以采取人為措施規避和消除不利影響,包括寬田埂、深蝦溝、低平臺的農田改造技術,田埂上還可設置防逃網以防小龍蝦跑出去。”舒新亞強調,小龍蝦在中國“安家”近百年,已經融入了本地生態系統,應該從外來入侵物種名單上剔除。
江蘇省淡水水產研究所養殖與裝備研究室主任許志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小龍蝦對稻田生態環境也有正面影響,一方面它可以捕捉稻田里面的一些害蟲,另外一方面它產生的糞便對稻田土壤有一定的肥沃作用。
“像土豆和玉米一樣,我們對小龍蝦這個外來物種的接受,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和相處。”許志強推測。
代理過系列人工繁育鸚鵡案的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鄭曉靜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原環保部聯合中科院制定的《外來入侵物種名單》既非法律,也非行政法規,其效力相對有限,現實中鮮有因小龍蝦被列為“外來入侵物種”而對小龍蝦養殖戶進行處罰的案例。
“如果需要從境外進口或者出口小龍蝦,也需要遵守相關檢疫規范、貨物進出口規范,否則可能構成行政違法,甚至觸犯走私罪、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等刑事罪名,并承擔相應刑事責任。”鄭曉靜說。
同時,鄭曉靜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國家對生物安全的重視程度顯著提高,甚至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并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該法至少有四個法條直接與外來物種入侵防治直接相關,于2021年4月15日開始生效。
魏開金認為,對政策制定者來說,下一步應該思考如何既保持小龍蝦產業的發展,又采取適當的措施防控生態危害的出現,在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間尋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