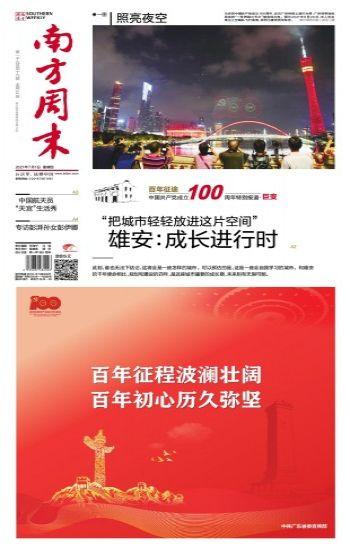反職場性騷擾,公司可通過《員工守則》渠道發力
劉遠舉
重中之重在于,對職場性騷擾行為作出明確的定義,才能清晰地界定、警示、禁止相關行為。比如,在工作時間在工作場所(包括加班與在外出差)通過口頭、書面、信息、網絡或其他方式向同事表達下流語言或展示淫穢內容
一家國際貿易公司的銷售總監,每月工資5萬多,在與同事共進午餐時,挨個問女同事的婚戀情況、初戀是誰,而且讓大家做“找老公”游戲,還多次使用不當的性暗示言語冒犯女同事,甚至損害女同事的聲譽。女同事投訴到總公司,公司調查后認為,該總監多次對同事體貌進行猥褻評價,臆測同事私生活,依據《員工手冊》中“性騷擾的表現”列舉的“針對性別的不得體的玩笑或戲謔”等行為,認為其嚴重違紀,解除勞動合同。這名總監不服,提起訴訟,日前,法院最終支持了公司的決定。
中國對“性騷擾”行為的法律適用散見于法律法規。性騷擾以及比性騷擾更惡劣的行為,在婦女權益保障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兒童權益保障法、青少年權益保障法、民法典、刑法中都有規定。
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婦女的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受法律保護。第四十條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
不過,在現有法律體系下,輕微的性騷擾的定義仍然不明確。不過,這一問題也正在逐步解決之中。北京、上海等地都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對構成性騷擾的具體形式作出界定。比如上海《上海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草案)就規定:“禁止以語言、文字、圖像、電子信息、肢體行為等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有關部門和用人單位應當采取必要措施預防和制止對婦女的性騷擾。”
值得注意的是,從婦女權益保障法到地方法規,都不同程度地規定了,遭受性騷擾的婦女,在報警、直接向法院起訴等救濟渠道之外,也可向本人所在單位、行為人所在單位、公共場所管理經營單位、婦女聯合會和有關機構投訴,而這些單位應當根據情況采取措施,預防和制止對婦女的性騷擾。
某種程度上,這就意味著法律要求用人單位盡到預防、制止性騷擾的義務。
現階段我國的反性騷擾立法中,用人單位應負的法律責任并不明確。很多人覺得,這些條款仍以宣示性為主,缺乏強制執行力和明確的罰則。
在歐美的司法實踐中,一般要求雇主設立預防和糾正性騷擾行為的合理機制,并且,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性騷擾行為的存在,要采取及時、恰當的糾正措施,否則,就要承擔替代責任。此外,公司還要為具有管理職能的雇員對其下屬實施的性騷擾承擔替代責任。
不過,基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勞動保護、個體權利等方面的現實,如果一味增加公司的替代責任,這個規則就可能被濫用。因為性騷擾面臨的處罰并不大,比如拘留,但如果單位賠償額很大,那么,以輕微的拘留,甚至都不用被拘留,就可以獲得單位高額的替代責任賠償的話,那么,合謀索取單位賠償,就變得非常容易,也非常劃算,單位或雇主就面臨較大的風險。
用人單位畢竟不是權力機關,在個人隱私、個人權利面前,必須止步,這就使其沒有萬全之策預防性騷擾。一般來說,只要不是故意放任,充耳不聞,用人單位責任都不該太大。
與此同時,當要用人單位承擔責任,其必然也由此具備某些權利。用人單位為了免除自己的風險,可以也應當在《員工手冊》或其他規章中,規定詳細完善的反性騷擾規則,嚴禁職場性騷擾行為發生,并將有關行為列入違紀情形,明確相應處罰細則,表明公司可以以違反法律法規,或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為由對其進行處分,直至解除勞動合同,并向員工公示。只有這樣,公司才有懲處職場性騷擾行為的制度依據,并免除自己的替代責任。對于員工手冊中的此類規則,法院通常都會支持。
這類規則中,重中之重就在于,對職場性騷擾行為作出明確的定義,才能清晰地界定、警示、禁止相關行為。比如,在工作時間在工作場所(包括加班與在外出差)通過口頭、書面、信息、網絡或其他方式向同事表達下流語言或展示淫穢內容,利用職務之便提出與工作無關要求作為工作的交換條件,進行不恰當的身體接觸,在朋友圈、公司群發布內容不當的公告材料等。這樣的詳細規定,就可以有效地針對所謂的開玩笑的托辭。
所以,在反性騷擾問題上,一方面,用人單位難以承擔過度的責任;但與此同時,用人單位也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用人單位做好反性騷擾工作,既是對女性的尊重,維護了單位的道德形象,同時,也是在日漸嚴密的法律法規之網下,對自身的保護。(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