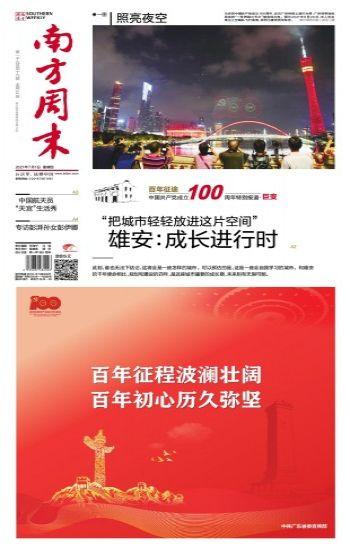探尋安樂死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
?上接第18版
雖然法案已經通過,現在已經生效,但我不太確定西班牙人是否知道伴隨這項法律而來的會是什么。理想和現實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該法案雖然已經在議會中進行了討論,但沒有在公民中進行討論。
安樂死法案看起來很美,但是,據我調查所知,讓人死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別是精神病患者,總有人會后悔的。我不知道西班牙人是否認識到這一點,但未來肯定會出現艱難的局面,他們肯定會回來討論。
南方周末:在你的書中能看到你對安樂死的態度的幾次轉變:從一開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再到后來更深地思考日本的情況也許并不適合安樂死的合法化。你是如何有了這樣的轉變?
宮下洋一:我的調查總是從零開始。我是一名記者。當我開始寫一本書時,我盡量不對我所看到的東西有任何定型的想法。如果我有,我肯定會失去平衡,無法保持中立。我的目標是與我的讀者一起旅行,一起學習東西。
我的想法一步一步地改變,一章一章地改變,這很正常,但我認為這很好,包括犯錯誤。我所希望的是誠實,寫出我所看到的、談論的和感覺到的,不給事實著色。
就我的轉變而言,我想說的是在美國俄勒岡州,當我遇到史蒂文斯博士時,他告訴我,有很多病人不應該安樂死,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迫”死亡。你遇到的醫生不同,你到達的目的地也會不同。人們通常相信醫生所說的,并試圖遵循他的指示——危險就在這里,只要允許安樂死,你就可能比預期的更早結束自己的生命。“拒絕治療之時就是終末期”,他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他問我為什么沒有人關心貧窮國家的安樂死時,我不知道該說什么。
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帶著一個疑問:你的死亡意愿真的是你的意愿嗎? 難道你不是被某人鼓勵或逼迫選擇安樂死的嗎?這是我不同意日本安樂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接受的教育不是自己決定事情,而是和大家一起決定,換句話說,自我決定不被認為是美德。在個人主義社會,安樂死可能更適合,但相反,在集體主義社會,它更復雜。
南方周末:本書出版已經過去了四年,這期間你對安樂死的看法有什么變化嗎?
宮下洋一:當這本書出版時,我認為安樂死只適合歐美人,但隨著我收到大量讀者的來信和留言,我開始更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我對日本社會的總體看法并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我慢慢覺得,意志非常堅定的人,或許更有可能赴瑞士安樂死。我認識到,這取決于病人,哪怕他生活在日本。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說,“日本缺少圍繞死亡的交流”。你認為造成這種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呢?
宮下洋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亞洲的教育是不同的。我們不是個人主義者。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總是在一起工作生活。我完全沒有冒犯西方社會的意思,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不認為我們更忌諱談論死亡,我認為我們只是沒有歐洲式的恐懼,即認為死亡是孤獨的,我們反而有更強烈的感覺,當涉及死亡時,我可以得到家庭的保護或支持,所以我們對“如何死亡”的擔憂比西方國家少。
南方周末:《安樂死現場》出版之后,日本醫療界對此有產生討論嗎?他們討論的方向和重點在哪里?
宮下洋一:這本書之后我出的一本書是關于一個在瑞士進行安樂死的日本女人——就是《安樂死現場》引發了她的意愿。她的故事引起了全國的討論。不僅醫學界,大眾媒體和公民也一直在提高他們的聲音,以期可以打開全國性的辯論。我的書在中國出版就是這種呼應的結果。
2020年8月,兩名日本醫生被捕,被指控在京都謀殺了一名ALS患者(記者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即漸凍人癥)。這名婦女本來想要死在瑞士,生前還給我寫了一條信息。兩名醫生之前從未見過她,但他們卻想實現他們的“理想結局”。由于日本沒有安樂死法案,這被認為是謀殺,我同意這一點。
但當這種令人震驚的新聞發生時,醫學界感到緊張并停止了討論安樂死這個問題。可是我是一名記者,我一定會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調查,并重新展開辯論,這樣人們就可以獲得信息,至少他們可以思考寶貴的生命——同時也是他們寶貴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