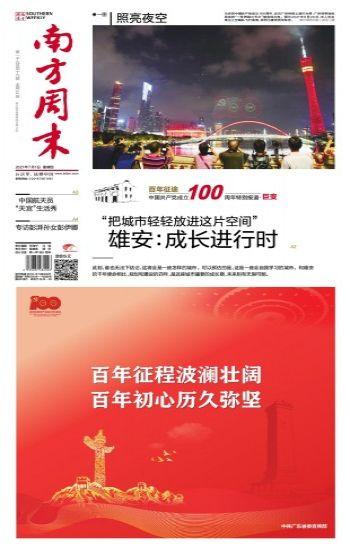“皇權不下縣”的鄉村治理矛盾
魏光奇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21。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邱捷。
★杜鳳治在晚清同治、光緒年間曾在廣東廣寧、四會、南海、羅定等州縣做地方官,是一位干練且“有心”的官員。他在廣東做州縣官的十幾年中,始終沒有中斷寫日記,字數達數百萬,且以記述公務為主。邱捷先生的《晚清官場鏡像》,發掘利用杜鳳治日記中大量真切、生動的資料,對晚清時期的廣東社會、“官場眾生相”、州縣公務、賦稅征收、州縣財政、官紳關系等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高度創新性的展示和研究,是一部晚清政治社會史研究的力作。
一部晚清政治社會史研究的力作
邱捷先生對《杜鳳治日記》的研究已有二十年的歷史,由于學術研究領域相近,我始終關注他這一研究的進展,認真拜讀過他陸續發表的相關論文。一個多月前,他的《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出版,我得到書后立即研讀,真是有所謂“先睹為快”的沖動。
杜鳳治在晚清同治、光緒年間曾在廣東廣寧、四會、南海、羅定等州縣做地方官,是一位干練且“有心”的官員。他在廣東做州縣官的十幾年中,始終沒有中斷寫日記,字數達數百萬,且以記述公務為主。邱捷先生介紹這一時期杜鳳治日記的內容說:“舉凡與上司、同僚、士紳的對話,處理公務、案件的過程,祭祀祠廟,科舉題目,典禮儀式,與他人的爭論、矛盾,多有詳細記述,對公文、信函往往也摘要抄錄。”邱捷先生還指出:“在當時,幾百萬字的日記絕無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記中有大量對上司、同僚、下屬甚至至親好友刻薄的評論及若干個人隱私,也說明杜鳳治寫日記時并不打算把日記示人。”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這可以有力地證明日記基本內容的真實性。毫無疑問,對這部日記進行細致的研究,乃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工作。
杜鳳治這一數百萬字的日記系用較草的行書書寫,且正文中間多有蠅頭小字的補寫、插寫,對它做研究,首先必須克服文字辨認方面的巨大困難。僅此一點就決定了,一個學者如果不具有充沛的學術熱忱,很難下決心投入這一工作。對杜鳳治“日記”的研究還需要克服“內容”角度的各種困難。“日記”所記述的杜鳳治官宦經歷和公務活動,是在清代一整套復雜的典章制度框架之內鋪展和進行的,如果在清代官員銓選任職、刑罰司法、治安捕盜、賦稅征解、州縣治理等重要制度領域缺乏知識積累,對這部“日記”就無法透徹理解,更不用說研究。研讀邱捷先生的這部著作,時時都能感到他對清代各種典章制度都下過研究功夫,都比較熟悉;而他對“日記”的研究,反過來也加深了人們對于這些制度實際運行情況的了解。
邱捷先生在給我的信中說:他的這部關于杜鳳治日記的著作“大致上是一部讀史札記,對任何問題都沒有做全面系統的研究,只求對前人研究做些有價值的補充”。這體現了他的謙虛。其實,學術研究的發展進步,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體現在所謂“全面”,而恰恰體現在“補充”,“補充”往往就是深入,就是拓展。這部著作,發掘利用杜鳳治日記中大量真切、生動的資料,對晚清時期的廣東社會、“官場眾生相”、州縣公務、賦稅征收、州縣財政、官紳關系等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高度創新性的展示和研究,是一部晚清政治社會史研究的力作。這部著作在“州縣官與士紳的合作與沖突”一章以及其他章節中,都關注到晚清時期的鄉村治理問題,而這個歷史問題與近代中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問題也存在關聯。針對這個問題,談談我研讀這部著作后的感想和受到的啟發。
從鄉官、鄉吏到鄉役
中國自秦代開始在全國范圍實行郡縣制,以縣為國家的初級政權,縣以下不設政府機構,即現在有人所謂的“皇權不下縣”。但毫無疑問的是,不設政府機構不等于不實行統治,相反,朝廷必須通過一種機制將自己的“政教”“下于民”,這也就是今人所謂的“鄉村治理”。在中國歷史上,“鄉村治理”機制既有歷時態的前后變化,也有共時態的地區差異。大致說來,自秦至隋唐在郡縣以下設立“鄉官”以及由縣派出而分管鄉里事務的“鄉(亭、里)吏”,秦漢時期的三老、嗇夫、游徼、亭長,晉代的里吏、嗇夫,北魏的“三長”等均屬之。這種鄉官、鄉吏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他們具有“長人之責”,任職須經國家承認(或由國家直接委任),甚至有祿秩或給職田;另一方面,他們又屬于本鄉里的社會人士,鄉官任職須得到地方社會某種形式的推舉,鄉吏也須在本地有一定地位或名望。他們履行的職能也具有雙重性質:一部分屬于政府行政職能,包括賦役征收、治安捕盜乃至訴訟審理等;另一方面屬于鄉里“自治”職能,包括勸農、教化、民事調解、公益建設、互助救濟等。對于這兩者,鄉官、鄉吏以一身兼任之。
至隋唐時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隋初每五百家設一名“鄉正”,“令理民間詞訟”,但遭到許多官員的反對。他們擔心,使鄉官審理自己“閭里親戚”的訴訟,必不能公正;而且,治民的權力也不應放給國家之外的地方人士掌握。隋文帝采納了他們的意見,廢除了這種具有理民、聽訟權力的鄉正制度。此后,隋唐兩代雖然置有族(黨)正、里正,但他們管戶不過百家,職能以催驅賦役等“負擔性”工作為主,而沒有“權力性”的執掌。唐中葉后,鄉官制度徹底蛻變。里正催驅賦役,經常受到貪官污吏的勒索虐待,無人愿意承當,只好改為“輪差”,“鄉官”從此淪為“職役”。
所謂“職役”,其性質乃是一種徭役。中國皇權時代,人民須通過從軍作戰、工程勞作等方式為國家服徭役,可稱“夫役”。“職役”與“夫役”都是“以民供事于官”的徭役,所不同者僅僅在于,前者是以在縣在鄉“任職”的方式來服役。隋唐的里正和宋元明清的里正、戶長、主首、里長、鄉保、地方等,都屬于“職役”,他們在鄉承役,故被稱為“鄉役”。這些人負責催征賦稅徭役、報告刑事和治安事件、遞送傳票等工作,可以說,官府對于鄉村統治秩序的維持——鄉村治理,主要就是依靠這種鄉役系統。
“紳治”并不美好
明清時期,在這個鄉役系統之外還存在著另外一種社會力量,這就是士紳。“士”者,取得科名后沒有離鄉出去做官的各類科舉士人;“紳”者,因退休、養病、丁憂等各種原因而在籍居住的官員(民國時期,被稱為“士紳”的群體范圍擴大了)。清代士紳在地方社會沒有經常性的組織,也沒有政治性權力,遇有鄉里急需辦理之事可臨時發起一些局、會、社、團,事畢即散。他們在鄉里的主要作為,就是以個人身份倡導辦理一些公共事務,如筑橋鋪路、修葺祠堂廟宇、修補水利村防設施、救濟災民貧民、興辦社學義學、調解田土財產糾紛等。
這樣,唐中葉鄉官制度廢弛以后的鄉村治理,就改由兩個并行的系統分任:屬于國家行政性質的事務由作為官府組織末梢的鄉役來運作,屬于地方“自治”性的事務由作為民間人士的士紳(以及宗族)來運作。近代以來,人們稱前者為“官治”,稱后者為“紳治”。邱捷先生的這部著作,就晚清時期的廣東“紳治”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復雜而生動的畫面,有助于我們在這方面做深入思考。
邱捷先生對杜鳳治日記的研究指出,咸同以后廣東的“士紳”群體,不僅有正途出身的科舉士人和在籍官員,還有相當一部分通過捐納取得監生(例監)“功名”和其他各種職銜的人士。這個士紳群體總體而言“好利”“不愛臉”,且往往與宗族勢力有緊密的結合。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后,清政府令各地官紳辦團練,一些地方的士紳們不僅有了自己的武裝,還乘機取得了收捐、刑罰等各種行政權力。從此,士紳們享有的一些零散且臨時的社會權力開始組織化和公權力化。杜鳳治任職廣東的同光時期,南海等州縣的鄉村普遍存在由士紳主持的“公局”,作為其首領人員的“局紳”由官府委任,在本鄉有緝捕、防衛、拘傳、初審、催征各權。這些權力的行使十分“任性”,欺壓貧弱、誣枉良善之事大量存在。對此,民眾無力制約,官府則往往有意放縱。戰亂時期,官府默許局紳處決人犯,19世紀50年代平定洪兵起義時,順德縣的“公局”拘捕了“賊匪”一萬三四千人,大部分在縣城以及各鄉處死;在非戰亂時期,公局有時也擅自殺人,清剿、拘捕盜匪時草菅人命,輕率殺死嫌疑者的事更不罕見。
這種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開啟的“紳權”組織化和惡劣化,到了20世紀初又經歷了一波發展。清末民初,國家推行“地方自治”,各地成立了(州)縣和城鎮鄉議(事)會、董事會,成立了不隸屬于縣公署而獨立運作的地方教育、財政、警察、實業局所和縣區鄉保衛團,成立了縣農會、商會、教育會等機構,所有這些機構的首領人員均為新舊士紳,“紳權”因此大興。這種地方自治當時雖然也為地方社會做了一些好事,但廣泛存在著“把持財政,抵抗稅捐,干預詞訟,妨礙行政”,“非法苛捐,冒支兼薪”,“私設法庭,非刑考訊”等濫權亂象,受到社會的詬病。“興紳權”這一口號,本是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為改變中國君主官僚專制制度而提出的,然而它付諸實行的結果,卻是劣紳勢力的惡性膨脹,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1939年,國民政府頒布“新縣制”,再次推行“地方自治”,成立“保民大會”“鄉鎮民代表會”和縣臨時參議會,選舉保長和正副鄉鎮長,議決本地公共事務。這次地方自治雖有成績,但又被一批“新士紳”和地方勢力所把持,他們操縱選舉,包收捐稅,包攬詞訟,互相傾軋甚至武裝火并,“紳治”再次破產。
鄉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清末民初,中國農村經濟衰落,民生凋敝,不少政治和文化精英都開始重視鄉村治理和建設問題。1904年,米鑒三、米迪剛父子開始在自己的家鄉河北定縣翟城推行“村治”,并不斷健全完善。1914年,孫發緒擔任定縣縣長,將翟城所實行的“村治”在全縣加以推廣,進行“模范縣”建設。1916年,孫發緒因在這方面政績突出而被任命為山西省長,將“村治”從河北引到了山西。孫發緒去職后至1920年代,閻錫山繼續了他的事業,大張旗鼓地在全省掀起“村治”運動。此后,梁漱溟、晏陽初、彭禹庭等人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繼續進行探索,尋找中國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的建設性出路。
“鄉村治理”是“鄉村建設”的核心。近代以來不少有識之士都能看到,中國傳統以鄉役為工具的“官治”和晚清以來以士紳為基干的“自治”,全都顯示出了極為嚴重的弊端,因此嘗試探索新的治理模式。閻錫山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要建立民眾自己的“活體組織”,以此來消除“官治”與“紳治”的弊病。他說:必須使人民“有施政之活體組織”才能實現具有建設性的鄉村治理,“若人民無此組織”,“政治上如同無串之錢”,則“弱受強欺,愚受智詐,寡受眾暴,除向最不愿問之衙門求救,仰最不愿仰之劣紳土棍求指點外,別無他法。云官治,乃貪官污吏之實況;云自治,亦劣紳土棍之變名”。閻錫山見到這一層,殊為不易。不過,當時中國的農民貧、弱、散、愚,素質不良,這嚴重制約了鄉村治理方面新式改革的進行,閻錫山自己在山西“村治”運動中建立的村民組織其實也只是徒具形式,并沒有發揮出他預期的積極作用。直至1949年,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問題始終也未能解決;而在此后的七十年間,人們也始終沒有停止對于這個問題進行探索。
現在人們講“時空穿越”,如果我自己能穿越回閻錫山所處的民國時代,對于中國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改革可能會持這樣一種看法:傳統的鄉役屬于政府組織末梢,但卻不被納入政府系統管理,既缺乏行政監督,也沒有民主監督,因此腐敗低效;“自治”名義下的“紳治”,其參與者、主導者以劣紳居多而正紳無幾,因此導致鄉里秩序黑暗混亂;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要想真正發揮成效而不成為貪官、劣紳控制操弄的工具,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來培養鄉村人民的思想政治素質。
邱捷先生研究杜鳳治日記的大作,內容和形式全都別具一格,相信很多治晚清社會史、法律史和政治制度史的學界同行,研讀后都會有多方面的收益和啟發。我本人更是希望能在今后對于明清州縣制度、鄉里制度的研究中參考和吸取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