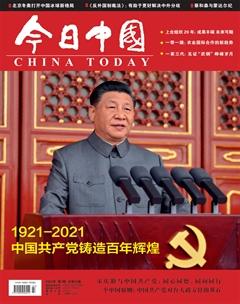李寧:為祖國醫學事業執念奮斗
王艷


20世紀80年代初,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77級大學畢業生李寧,被分配至北京朝陽醫院。在征求專業志愿時,他只寫了四個字“立志外科”,如愿分到普外科后,便開始了他的外科生涯。那年他25歲。
2017年,60歲的李寧榮獲“中國榮耀醫者外科金柳葉刀獎”。站在領獎臺上回首過往,他感慨萬千,說了這樣一段話:“我20出發、30而立、60成才、90建大業,下輩子還干外科。”
作為中國肝臟移植外科界的國手、北京地區肝移植學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在從事醫院管理工作20余年里,李寧無論在手術、學術還是管理領域,他都追求卓越,目標遠大,并且以執著的精神攻堅克難,不斷探索新知,解決更多的醫學和管理難題。
高考改變命運
1977年10月,當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得知即將恢復高考的消息時,留給他們的復習時間已不足兩個月。
這一年,中斷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引發了中國歷史的巨大變革,同時也開啟了改變那一代青年命運的大門。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但對于全國570多萬考生而言,那個冬日陽光燦爛。
1977年12月10日,北京考生在同一時刻走進了神圣的高考殿堂。北京市朝陽區新中街中學考場00001號座位的考生就是李寧。談起高考當天的情景,李寧依舊難掩興奮的余韻。
1957年10月6日,李寧出生于北京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中學教員。自幼受家庭熏陶的他,深知讀書的重要和知識的可貴,從呼家樓中心小學到北京市第八十中學,一直是品學兼優的三好學生,在初三“回潮”那年期終考試,8門功課800滿分。這個成績在那個年代也算是個學霸了吧。
后來,高考第一志愿本選擇郵電大學衛星載波專業的李寧,機緣巧合收到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1978年3月8日,李寧步入北京第二醫學院(現首都醫科大學),成為恢復高考后首屆77級大學生的一員,自此走上了醫學的道路。
“知識改變命運”,在20世紀的中國絕對是一句至理名言。李寧說:“我始終難忘恢復高考這個歷史和命運的轉折點,是大學之路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及病人的生命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當你從一片貧瘠的丘陵,懷著人生的希望和從醫治病的理想信念,步入浩瀚的知識森林時,面對書本你會產生如饑似渴的感覺,時間過得太快,以前所學的知識太少”。那個年代在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抓緊時間、拼命學習,掌握更多的知識,為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奉獻青春和熱血。
李寧回憶道,“77級是年齡差距最大的年級,我們班老大哥入學時32歲,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最小的18歲,我也剛20出頭。”但在學習面前,那是你追我趕,誰也不甘落后。尤其頭兩年,大家都是憋著一股勁,埋頭讀書,下午課后先去圖書館或階梯教室占座,晚飯后便匆匆去晚自習,十點鐘熄燈后,在被窩里用手電筒照明還要再背幾個單詞。李寧說,“最好吃的飯就是每周六早餐的油餅,那年頭肚子里沒油水,一頓飯我能吃4個饅頭,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這是我人生中最快樂、最充實的時光,真想再回到那個年代,也許我可以做得更好。”
“兩年基礎課后去臨床實習,當我第一次面對病人的時候,由衷產生了一種釋放知識的欲望,你可以對病人詢問病史、觀察他的變化、記錄病程、抽血、打針、換藥,病人病情的變化會牽動著你的心,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了節假日。一年365天,每天早晨來醫院查房,談不上什么自覺自愿,要想做個好醫生,就應該是這樣,我的老師都這樣。”李寧表示。
五年的大學生涯轉眼過去了,1982年11月,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77級畢業生舉行了畢業典禮。習仲勛副總理諄諄的教導,殷切的希望,一直回蕩在耳邊,他們唱著“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么美……光榮屬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從此步入了醫生這一崇高而神圣的殿堂。1982年12月,李寧被分配至北京朝陽醫院普外科,拿起手術刀,開始了他的外科生涯。
追求完美的愛國主義者
從醫第一年,李寧成為了一名住院醫師,24小時天天住在醫院,病房隨叫隨到,每天晚上還要定時查房,寫完病程記錄后才回宿舍。有時半夜來急診病人,還會跑去病房參加手術,他細心觀察著上級醫生的每一個動作,記錄著病人的每一點變化。
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從醫30余載,李寧在追求每臺手術精準度和成功率的同時,做手術的速度也快得驚人。做住院總醫師期間,李寧曾創造過兩項手術紀錄:闌尾切除術從開皮到結束只用了7分鐘;疝氣修補術僅用了20分鐘。每次做完手術,看到患者家屬詫異和感激的表情,李寧內心總會油然升起一股作為外科醫生的自豪感和滿足感。
1989年,33歲的李寧擔任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是當時全國大型綜合醫院中最年輕的主管醫療副院長。他說:“第一次上臺講話,我抬眼一望下面坐的都是我老師,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上。”雖然年輕,但他深知肩上的責任重大,想得最多的就是學科建設和醫院發展。
90年代初,中國在醫院管理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1994年,靠著在海外大伯的資助,李寧是第一個到美國學習醫院管理的自費生。就讀于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衛生與醫院管理專業ISP研究生班。初到美國,感覺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差距真是太大了,先進的儀器設備、百級凈化手術室、發達的信息系統、智能電子病歷、中心化學科建制、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團隊協作,更多的是理念差距。面對這一切,一股對先進知識、新技術及新組織管理方式學習借鑒的探求得到了再次升華,但學習的困難比以往更大,主要是聽英文講課有難度。自此四年間每逢暑假,他都會去美國學習一個月,兩個星期上課,兩個星期去醫院見習。每年12月還要去香港參加地區性學員研討會。那個時期,恨不得把看到、聽到的一切都記在心里,回來就實踐,邊學邊用邊改。
曾有一個暑期,李寧住在一位心胸血管外科醫生歐亞克家里,每天和他一起去出門診、查房、上手術、參觀醫院和社區,目的是要了解美國醫生是如何工作的,美國的醫療系統到底是怎么運轉的,所見所聞都讓他獲益匪淺。
李寧說:“歐亞克曾問我,是否愿意留在美國?我可以幫助你。我非常理解和感激他的善意,如果我留在美國,可能會有更高的平臺和更富裕的生活,但我那時滿腦子都是回國后的改革規劃。我對他說,美國很發達,比我們先進至少50年,但那里畢竟不是我的家,我的目標是讓中國人能過上美國人一樣的生活,我要在中國建造一家我心中夢想的醫院,美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也一樣能做到,也許會做得更好。”回憶起這段難以忘懷的經歷時,李寧不斷用手掌擦按著眼角,努力不讓眼淚流出來。
在美國學習的那段日子,所學所見所聞讓李寧獲益匪淺,也從根本上影響了他對病人和醫院的理解及管理理念的認識。在后來的醫院管理實踐中,他經歷了主管北京朝陽醫院醫療、科研、教學的副院長14年,促進了急危重病醫學、器官移植、人工假體、腔鏡與微創手術及腫瘤生物治療等新興學科飛躍式發展。調任北京佑安醫院院長、北京肝病研究所所長12年,把一個偏科、綜合實力落后的傳染病醫院,改造成全國知名的以感染、傳染及急慢性相關性疾病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集預防、醫療、科研、教學、康復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醫學中心。
在交談過程中,李寧重于戰略規劃、精于細節、執念進取、追求夢想的特質,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熱愛挑戰魅力在于卓越
長久以來,終末期肝病盡管采用中西醫各種治療方法,都無法終止和逆轉,更談不上治愈,一直被醫學界視為生命終結難以跨越的門檻。1963年,美國醫生Starzl成功實施了世界上第一例同種異體原位肝臟移植手術,患者至今健康生存。這一技術成功地打破了終末期肝病無法可醫的困境,為瀕臨死亡的病人帶來重生的希望。但肝臟移植手術也被公認為是外科手術中難度最大、風險最高的尖端科技領域。美國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腎移植難度系數為7+,而肝移植難度系數是55。中國開展肝臟移植起步于1977年,至1983年底共完成肝移植57例,1年生存率是0。1991年至1998年的第二階段,肝移植數量超過數百例,但5年生存率僅有19%,這與當時發達國家肝移植術后平均5年生存率75%的水平相差甚遠。
掌握這項尖端技術,打破這一生命禁區,一直是中國醫學界的追求夙愿。1999年,作為朝陽醫院普外科主任的李寧和另外三名同事組成攻關小組,赴澳大利亞墨爾本Austin醫院國家肝臟移植中心學習。參加的第一例肝移植手術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手術大概是夜里12點結束,第二天早上9點我們去查房,發現病床上沒有病人,正要去找護士了解,只見病人自己手提引流袋回到病房。我們上下打量著她,驚訝地問:你是昨晚肝移植的病人嗎?你現在感覺怎么樣?她說:是我啊,我現在感覺良好,剛剛在床上躺不住,就到外面遛了一圈。我們相互觀望,驚嘆不已。怎么可能呢?以往腹部大手術,第一天需臥床禁食,排氣后方能開始流食、半流食,三天后才能下床活動。而她接受肝移植手術后8小時居然能自主下床活動,新移植的肝臟會不會掉下來啊!真是不可思議!”與此同時,我們又憋了一股勁,一定要掌握這一尖端技術。回憶當時的情景,李寧激動地說道。
那段時間,李寧非常珍惜每一次參加手術的機會,觀察并記錄手術的每一個細節,以及病人每一點細微的病情變化,為后來肝臟移植手術的臨床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學成歸來,當年底李寧就與沈中陽教授合作實施了朝陽醫院第一例肝臟移植手術,這個病人至今仍然健康存活,這也是中國單次肝臟移植存活時間最長的患者之一。
20多年來,李寧帶領他的團隊完成各類肝臟移植手術1000多例次,取得了北京地區肝移植手術成功率最高、長期存活率最好的國內先進水平,成為北京地區肝移植學科帶頭人,并攻克了多個肝臟移植和肝癌領域的世界性難題。他用精湛、卓越的醫術,讓熊貓血的亞急性肝功能衰竭的女大學生成功換肝并戀愛結婚生子;經他之手縫合的800多例肝動脈和膽道無一例并發癥;為結腸癌并十二指腸、胰頭侵犯、肝轉移的晚期患者實施聯合切除加抗腫瘤基因治療,使其重獲新生,至今超過5年;為艾滋病腹膜后20斤巨大腫瘤合并腎臟侵犯患者實施聯合切除。經他雙手拯救的生命已無法數清。
帶領團隊不斷攀越高峰
中國是肝癌大國,據2020年統計報告:年新發病例41萬,年死亡病例39萬。其主要原因:一是早期診斷率低,80%患者一經確診已進入中晚期;二是肝癌對放療、化療不敏感,缺乏有效靶向藥物。
自2000年,李寧與馬丁院士合作,在國際率先開展抗實體腫瘤ADVTK基因治療基礎與臨床研究,針對超過國際“米蘭”標準中晚期肝癌實施肝移植加ADV-TK基因治療,經過兩期探索性臨床研究和Ⅱ期臨床試驗,將肝癌肝移植適應癥提高到:肝癌累積直徑<12cm,甲胎蛋白<1000μg/L,不伴有一二級大血管侵犯,5年生存率超過70%。此項成果已被寫入歐洲肝癌肝移植指南,并進入Ⅲ期臨床試驗。另一項研究顯示:<5cm的小肝癌,瘤體內注射ADV-TK基因后行肝癌局部切除再加肝臟局部血管注射基因制劑,5年生存率超過90%。其他針對腦膠質瘤、肺癌、乳腺癌、宮頸癌、胃及結直腸癌等實體腫瘤的臨床研究均取得良好的療效。未來這一成果的臨床應用與推廣將極大改善實體腫瘤病人的臨床預后。
李寧的另一項研究領域是利用多組學技術篩選乙肝相關肝癌早早期/分期診斷特異性標志物。在科技部“十一五”“十二五”重大專項研究課題和北京市科委重大疾病生物樣本庫建設計劃的支持下,李寧和他的科研團隊采用系統論的科學方法,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利用外周血免疫細胞PBMC-DNA甲基化技術,成功篩選出乙肝相關肝癌早早期特異性標志物組合,其診斷準確率幾近100%,已獲得國際國內專利。在其他方面,利用外周血采用miRNA、蛋白質及代謝組學高通量檢測技術,也已成功篩選出可精準區分慢乙肝、肝纖維化、肝硬化、肝癌早早期、早期、進展期及晚期的分期診斷特異性標志物。此項成果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將為實現肝癌精準醫療,提高肝癌早期/分期精準診斷率,提高肝癌長期生存率做出中國原創的里程碑式貢獻。
擔起大醫的使命與責任
如今李寧已年過六旬,卸任了院長職務,但作為一名外科醫生,他仍堅守在臨床醫療、科研、教學的第一線,他對醫學科技創新及醫院發展建設的使命感、責任感及對祖國醫學事業的執念追求絲毫沒有改變。
在他看來,醫生的職業是沒有年齡時限的,人對事業的追求也是無限的。“當年我站在領獎臺上手捧金柳葉刀獎杯時,坐在第一排的是四位年過九旬獲得‘金圣獎的醫學前輩,如今有兩位已年過100歲,比起他們我還是青年人。”他認為,還有許多病人等待我們去解救,還有許多已取得的成果需要我們去轉化,成為真正在臨床可以應用的方法和手段。“我說30而立到60成才走過了30年,60歲到90歲還有30年,能干許多事情,我要在90歲時完成我夢中的大業,把中國肝癌落后大國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去,所以說未來還是屬于我們的。”
這就是“789”新三屆一代人的靈魂和脊骨,他們在振興民族大業,實現祖國富強,解救人民疾苦的偉大征程中,不忘初心,抱著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懈地學習、實踐、奮斗,把有限的職業所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健康事業服務之中。
用李寧自己的話講:“為祖國醫學事業的不懈奮斗是我幸福的根本源泉。這輩子干不完,下輩子還干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