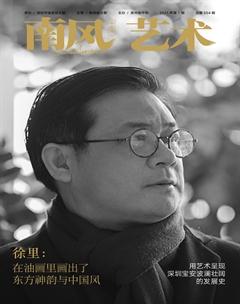自然與人為相融相合的藝術裝置探索



藝術家介紹:
Pierre Huyghe 皮埃爾·于熱是一位法國藝術家,于1962年出生于巴黎,現工作生活于紐約。他的藝術創作媒介多樣,從電影到藝術裝置,作品探索哲學思想、公共關系、生態系統等命題。
從“地域性”切入去解讀Pierre Huyghe皮埃爾·于熱的作品是不可行的,他的作品不滿足地域文化性這一條件,它們不囿限于美術館內,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
Pierre Huyghe的After A Live Ahead就選址在明斯特的一個廢舊溜冰場。這個溜冰場被他徹底改造成一個令人驚奇的作品。場內原來的看臺被保留,混凝土的溜冰地板被掀起,露出黃泥土,地面被堆砌得高低不平,低洼處還有大大小小的水池。仿佛是一個正等待勘測的古代文明遺址。當你走進現場,頭頂上傳來嗡嗡的聲響,光滑的面板從天花板上緩緩劃開,將整個地面暴露在陽光中。在這個空間內的水泥平臺上,佇立著一個可以由透明變為黑色不透光的玻璃水族箱。
整個大廳演變成一個巨大而半封閉的生態群落。各式生物如,孔雀、蜜蜂、不易察覺的微生物等被安置在大廳里。在這里,元素相互依存,并形成某種巧妙的關聯網,具有生命的生物、真實的景觀、動態與靜態混合成一個共生系統。
巨大溜冰場地面的切割方式來源于一套由阿基米德發展出來的幾何拼圖“Ostomachion”,在阿基米德的手稿中,正方形由14塊幾何形體組成。它們可以被打散與重組,也能以另一種方式拼合成正方形。Huyghe以幾何拼湊方式為依據,讓工人一點點分割著地面,不斷向下挖掘,直至地下水、粘土層與沙層。粘土被制作成了錐體聳立著,周圍圍繞著蜂群。空間內配有傳感器,不斷記錄著蜂群的運動軌跡與現場的生命跡象。所有的生命體運動將被收集,數據化處理后傳輸到一個方型的孵化器中。器皿中存活著最久的人類癌細胞,它們會根據接收到的數據產生不同的細胞分裂方式。觀眾可以通過下載一個app來觀察它們的變化過程。這些數據同樣影響著空間中心的玻璃水族箱,箱里漂浮著一只有毒的海洋蝸牛,貝殼上有織物狀的花紋,有一大一小的三角形構成。這個有機體的體積很小,很容易被觀眾忽視,但它在展覽中起著關鍵作用。藝術家掃描了貝殼的外殼,使得玻璃水箱的開啟與閉合以它的變化為準。而當水箱開或者關時,上方天花板的面板也隨之開合。
對于After A Live Ahead? 的解讀,Huyghe說:“這里是一個自主組織的系統。這里有持續的變化,成長、演化、轉變。這里沒有主從關系,它們不斷地在轉換。” “而我做的是盡量不去干預它(隨系統自主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場呈現的景象都不一樣。陽光、雨水會不斷進入空間,滋養著各生物,繼續著奇異的旅程。整體場景壯觀,但對于有著當代藝術愛好的觀眾來說,這個作品離崇高之敬仰還有一些距離。康德曾闡述:一切真正的美,是既崇高而又優美,兩者兼而有之,兩者相頡頏而光輝。“優美”與“崇高”的區別在于,“優美”給人以歡愉的感覺,而“崇高”卻使人敬畏。現場作品的文字敘述十分有限。離開了詳細的背景資料與“說明書”,要求觀眾自行腦補和演示生態系統的關聯性、物理變化、化學技術是有一定專業難度的,以致于阻擋了穿過作品視覺深入到內里探索元素間關系的嘗試。多數觀眾對作品的理解停留在視覺體驗與多媒體互動的分析與總結上,這種理解通過知性和參與性的作用,喚起了審美與互動的愉悅,卻無法喚起“崇高的情感”。
在日常社會的關系中,人類扮演著掌控者的角色,企圖用文明、技術來控制一切,使得所有的事情都變得可操控。在這個作品中,生物系統有著自己的運作方式與規律,技術被人類用作與生態系統鏈接的工具。這種自然與人為的結合產生一種對 “純自然”,“純生態”的反思:到底如何才能到達完全的,無人為因素干預的“自然”?在After A Live Ahead 中,技術給人類帶來的是app上的數據變化,界內的生態元素被數據化后作用于整個生態圈。在這個層面去理解,似乎作品并未完全達到Huyghe所談及的“不干預”,只能說在相對較少人為(此指技術)控制的環境中提供了生態系統內各元素間“真實的”互動機會。
陳思,藝術策展人、藝術評論員,畢業于墨爾本大學藝術史與策展專業。專攻十四、十五世紀文藝復興藝術、當代藝術策展實踐與學術寫作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