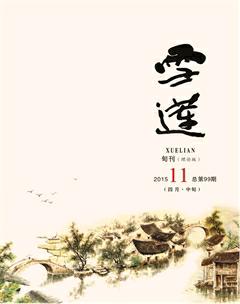淺析蕭紅散文的創作風格
周靜
【摘 ?要】二十世紀,蕭紅以其中篇小說《生死場》蜚聲中外文壇。她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還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先后集結出版了《商市街》《橋》《蕭紅散文》等散文集。她在散文創作上的成就,絲毫不遜于在小說創作上的成就。本文就蕭紅散文的創作風格,略作分析。
【關鍵詞】蕭紅;散文;創作風格
認識蕭紅或許是從《生死場》《呼蘭河傳》開始,若想熟識蕭紅,或許該從她的散文開始。她的小說常常帶有散文的風格,她的散文里又時時體現出小說的敘述方式,這也使得她的散文更具特色和魅力。
在蕭紅的散文中,我們可以看見當時的社會現實,圍繞著她的人生經歷、所見所聞,取材雖不廣泛,但她善于寫小事,能把小事說得娓娓動聽,耐人尋味。文章的著力點更多集中在描寫記敘生活或事件中的情景和過程。
作為魯迅先生的得意門生,在先生逝世后,她寫作了其散文代表作《回憶魯迅先生》,不同于其他緬懷先生的文章,她沒有寫先生一生中的重要事件,甚至沒有頌揚先生的大義和功績,而從先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寫起,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反而讓先生的形象更生動更豐滿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就連以學生反對侵略、日寇轟炸重慶為題材的《一條鐵路的完成》和《放火者》等作品,都只是把事件的過程和情景真實地再現出來,沒有振臂一呼,沒有慷慨陳詞。
她在取材和用材上的獨具匠心,使得她的散文更有特色。
縱觀蕭紅的百余篇散文,內容雖不相同,但大多數都表達出她的一種思想感情,即對美好生活的渴望與追求。從《棄兒》中的英氣十足到《后花園》中充斥的憂傷,從藝術造詣上看雖差距甚大,但她對美好生活的熱愛和向往之情卻一直都沒有變。這也使得她的散文創作風格既獨特又統一。
蕭紅一生顛沛流離,命途多舛,但她是個對生活充滿熱情的人,并始終對美好生活保有渴望并不懈追求。她對生活的熱情是從苦難的現實中萌發出來的,而不是逃避現實自顧自憐的主觀臆想。她的散文所表現出的積極意義也在于此。
《商市街》是蕭紅最為成功的散文集,全書四十一篇作品真實再現了蕭軍和蕭紅近兩年的落魄生活。寫的都是日常生活的貧窮困頓,但他們卻沒有因此喪失對生活的勇氣和信心,反而在艱難的日子里,覓得一些微乎其微的歡樂。正是基于蕭紅對生活的熱愛,才能讓這些本該傷感萬分的文字卻透出云淡風輕的灑脫。
“回來沒有睡覺之前,我們一面喝著開水,一面說:‘這回又餓不著了,又夠吃些日子。閉了燈,又滿足又安適地睡了一夜。”
餓得想拋下自尊去偷別人的“列巴圈”,蕭紅把她的兩次內心掙扎寫得入木三分,后因友人的仗義借款,他們又能挨過一些時日,在這種上頓不接下頓的窘境下,他們卻能滿足而安適地睡了一夜,足見其內心的強大和對美好生活的終將到來的信念的堅定。
“素食,有時候不食,好像傳說上要成仙的人在這地方苦修苦練,很有成績,修煉得倒是不錯了,臉也黃了,骨頭也瘦了。我的眼睛越來越擴大,他的頰骨和木塊一樣突在腮邊。這些功夫都做到了,只是還沒成仙。”
赤裸裸的饑餓,愣是被她說成了成仙前的修煉,瘦成了那樣,她覺得遺憾的只是還沒成仙。蕭紅的善良與可愛在這里一覽無余。唯有對生活保有本真的人才會如她這般熱愛生活。
熱愛生活,積極地生活,用作品去描繪現實生活,使得蕭紅的散文在創作風格上構成了一種充滿濃郁的現實生活色彩和質樸的真情實感相交融的特色。
蕭紅從走上“寫作”這條道路之初,就一直在摸索適合自己的線路,并堅持地走下去。從早期作品中顯現的粗糙淺顯,到后期作品中的成熟完美,都能很容易看出這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筆。
茅盾就曾這樣評價過蕭紅的經典作品:“《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于它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 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散文詩……”
她的散文有情節有人物有環境,你甚至很難區分這些文章到底是散文還是小說。這種小說和散文互見的形式,也算是她創作風格上的又一特色。
在蕭紅的散文作品中,我們可以通過她在題材、主題和表現手法上的特點,體會到她忠實于現實、客觀反映現實生活的創作理念和熱愛生活、率真而不失可愛的創作個性。基于此,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蕭紅的散文,也更全面地認識了蕭紅本人。
參考文獻:
[1]蕭紅.蕭紅散文名篇[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2]蕭紅.呼蘭河傳[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