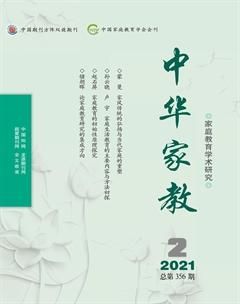物質豐裕時代家庭勞動教育的價值取向
班建武
勞動教育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只有扎根于具體的社會現實,才能充分彰顯其時代活力和育人功能。對于當下中國而言,一個突出的社會現實是,中國正日益擺脫昔日的貧困狀態而走向富裕。據報道,2019年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與此同時,中國城鄉平均恩格爾系數(即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已經下降到28.2%(其中城鎮為27.6%,農村為30.0%)。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恩格爾系數在30%及以下,就意味著那個國家的人民生活已經達到了所謂的最“富裕”水平。在這樣一種新的物質前提下,我們的勞動教育,尤其是家庭勞動教育應該有新的價值追求。
一、勞動價值觀的代際分歧
勞動價值觀突出反映的是個體對勞動意義和作用的看法。而勞動之于個體的價值和意義往往會隨著勞動形態的變遷以及社會發展歷程的變化而表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傳統社會中,勞動主要是以簡單體力勞動為其基本形態,社會物質財富相對匱乏。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對于人的壓迫性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在這種生產環境中,人們對于勞動價值和意義的認識,更多地是將其視為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謀生手段。隨著現代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勞動的復雜程度不斷增強,對人的智力因素的要求也不斷提高。與此同時,伴隨生產力不斷發展,社會物質財富也急劇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對人的壓迫性也隨之降低。這就使得在物質財富相對豐裕甚至過剩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對于勞動意義和價值的看法,與其祖父輩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當前,兩代人最重要的分歧就在于對勞動及其價值和意義的認識上的不同。比如,家長更多地是強調勞動的謀生功能,因而非常重視將孩子作為未來就業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勞動力或人力資本來培養。家長的諸多努力,比如盡可能地提高孩子的學習成績、盡可能地培養孩子多方面的才能、盡可能地幫助孩子獲得各種榮譽證書,都共同指向對孩子在教育領域中競爭力的提高,從而確保孩子將來能夠在勞動市場上“笑傲江湖”。在這種以謀生為基本價值取向的家庭教育邏輯中,孩子更多地是被當作潛在的生產要素去培養和開發,而不是被視為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去培養。這種家庭教育邏輯在過去具有非常強大的親子團結功能。也就是說,在物質匱乏的時代,將自我物化為現實生活中就業市場激烈競爭的勞動力,不斷提高個體作為勞動力的核心競爭能力,從而實現一種身份的向上流動,獲得相對富足的生活的人生訴求,特別容易在代際親子之間達成共識。之所以親子問能達成共識,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種訴求更多地建立在社會物質財富普遍匱乏、人們生活普遍貧困的基礎之上,正是社會物質的匱乏導致了“生存需求成為壓倒一切的需求”。這就為基于謀生的個體生存競爭能力的培養成為家庭教育最為看重的目標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社會物質基礎。
但是,我們也越來越發現,當下家長如果還是主要從這樣一種謀生的角度,簡單地把孩子當作未來就業市場上的潛在勞動力去培養的話,那么,這種家庭教育邏輯將會越來越遭受到孩子的內心抵制和行動反抗。曾經有媒體報道過這樣一個事件,一個初二的孩子問老師:“我們家有十幾套房子,我學會收租就夠了,為什么還要學習?”孩子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疑問,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家長灌輸給孩子的教育目標是要其成為一個能夠在就業市場上具有高度競爭力的職業人,從而保證其過上體面的生活,而這種家長眼中的體面生活基本上又是物質取向的。但對于從小就生活在富足家庭的大多數孩子而言,他們從未有過物質匱乏的生活體驗。哪怕是對于一些家庭相對貧困的家長而言,他們往往也秉持著一種“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教育理念,在物質方面幾乎傾其所有滿足孩子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孩子來說,當下的物質生活根本不是需要他們焦慮的問題。他們需要什么家長都會想方設法去滿足,尤其是對孩子物質層面需要的滿足。既然當下的物質生活已經能夠很好地滿足孩子的種種需求,那么他們為什么要再通過艱苦的學習去實現對于他們而言已經實現了的生活狀態呢?
這實際上給家庭教育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教育課題:在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勞動對于不愁吃、不愁穿的年輕一代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在物質匱乏時代,勞動具有非常明顯的謀生功能。基于勞動謀生功能的教育邏輯在對孩子進行勞動教育上具有很強的動機作用。但是,謀生的重要性對當代孩子來說已經隨著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而日益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僅僅從勞動的謀生功能的角度來思考孩子的教育問題,顯然已經失去了必要的物質前提,也失去了孩子對勞動合法性的內在認同。
實際上,勞動從來就不僅僅具有謀生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得以對象化的必要實踐,是體現人的類本質存在的重要形式。過去勞動的謀生功能之所以被凸顯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夠充分所帶來的人的物質生活的窘迫性。這也使得本應體現人的主體意志的自覺、自由的勞動變成了一種對人的壓迫的異己力量。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家長,往往帶有那個時代關于物質匱乏生活的痛苦回憶,因而天然地想讓自己的孩子不要再重蹈自己當年的痛苦。這種基于血緣的自然情感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在于,代際之間由于生活物質條件的不同,二者關于“苦”的認識存在著明顯的代際區別。對于年長一代而言,苦更多地意味著物質的匱乏。但對于年輕一代而言,苦則更多指向自我精神世界的匱乏和存在感、意義感的缺失。如果在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家長依然從其“物質之苦”來理解勞動的價值,那么這樣的勞動對于現在的孩子而言,不僅很難有吸引力,而且也極易引發親子之間在認識上的沖突。
二、新時代家庭勞動教育的價值選擇
基于謀生的單一價值取向的家庭勞動教育顯然已經不能很好地得到孩子發自內心的真正認同。這就需要家長必須自覺立足于物質豐裕時代勞動的新使命、立足于孩子成長世界的新狀態、立足于完整勞動世界的新圖景來思考家庭勞動教育的新價值,才能重新彰顯勞動教育對當代孩子的價值和意義。這就需要家長必須主動做出變革。
首先,需要家長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時代勞動的本質內涵。從形式上看,勞動毫無疑問是一種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活動。但從深層次來看,勞動更是體現人的主體性存在和意義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從馬克思主義來看:“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人化過程。人通過勞動實現了自然的人化,從而得以彰顯其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人也正是在“人化自然”這樣一種對象化實踐中真正感受到自我本質力量得以實現時的價值感和意義感。尤其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現代科技在勞動中的充分應用,社會物質財富將會不斷豐富,勞動對人的壓迫性也必將逐漸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的本體性功能將會得到充分釋放。因此,家長在與孩子談勞動時,不能像過去那樣僅僅囿于謀生這一角度,而是要引導孩子看到勞動之于其人生價值、自我實現的重要意義,讓孩子在勞動中充分感受到自我作為主體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彰顯,感受到勞動與自我的自覺、自由的類本質的內在一致性。唯有如此,勞動才能夠真正在當代孩子中樹立起內在的合法性。
其次,家長還應該主動通過勞動重塑孩子的關系性存在,從而不斷豐富孩子的精神世界。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繁重的學業和激烈的競爭使得孩子們的生活幾乎圍繞著家庭、學校、校外輔導機構這一單一的線條進行。這種生活樣態導致孩子與大千世界、蕓蕓眾生的關系不斷窄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人的豐富性的不斷喪失,從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的生命靈性的缺失、審美情趣的匱乏以及精神創造的萎靡。實際上,人的本質就其現實性而言,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生產關系。“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因此,在勞動中,既有人與人之間相互協作的合作關系,也有人與自然萬事萬物的和諧共生關系。可以說,一個人勞動的廣度和深度,將會極大地豐富其關系的多樣性,進而會提升其生命的厚度和深度。這實際上要求家長在思考家庭勞動教育的時候,不僅要考慮那些具體的生產性技能的培育,更要關注以勞動為核心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復雜關系網絡,幫助孩子通過勞動去真正走進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從而修復其與自然、社會的斷裂關系,最終恢復孩子的生命靈性。
最后,家長應從生產與消費一體化的角度來幫助孩子構建對現實勞動世界的完整認識。勞動一端指向生產,另一端則連著消費。整個勞動世界主要是圍繞著“生產一消費”這一鏈條而展開的。長期以來,我們更多地是賦予生產以積極的意義,但對消費大多持否定的態度。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將壓制自我的消費沖動看作是一種美德而予以褒獎。如果說,這種關于消費的認識在物質匱乏時代具有其現實合理性的話,那么對當前這樣一個物質豐裕的社會而言,消費就不能僅僅從消極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實際上,消費不僅僅意味對特定勞動成果和社會財富的消耗,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人的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得以維系的基本條件。前者確保了勞動力的可持續生產,而后者則確保了現代生產的動力和市場。可以說,沒有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沒有消費市場的擴大,現代生產將因缺乏必要的動力而陷入停滯。從這個角度看,消費也屬于現代生產的必要環節。此外,消費在很大程度上也賦予了生產以目的,即人們生產歸根結底不是僅僅滿足于財富的積累,而是為了更好地改善和提升人的生活質量。沒有消費的生產是很難想象的。因此,只講生產不講消費的勞動世界是不完整的。家長在面對孩子的消費時,要避免從傳統社會的道德制高點去評價和要求,即簡單地從節約、實用的角度去與孩子談消費,而是要幫助孩子從消費中理解其中所蘊含的生產意義。并且通過消費,讓孩子去洞悉其背后復雜的生產鏈條和消費關系,從而使其對勞動的理解不僅僅停留在財富生產的維度,更深入到對勞動關系以及社會整體生產關系的全面把握。
總體而言,在當前這樣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家庭勞動教育必須從過去單一的謀生價值取向轉向關乎人的存在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上來。家長最需要做的調整就在于,從自我關于物質匱乏時代的“苦”記憶當中解放出來,重新認識勞動在新時代所具有的新的意義和功能,才能更好地找到與孩子對話的基本前提。實際上,在當前這樣一個社會財富日益豐富的新時代,家庭勞動教育就不能僅僅務勞動之“實”,更要務勞動之“虛”。家庭勞動教育固然要幫助孩子具有基本的勞動能力和勞動習慣,但其重點更在于幫助孩子形成正確的勞動觀念,讓孩子在勞動中不斷豐富自我的關系性存在,從而找到自我價值確證的可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