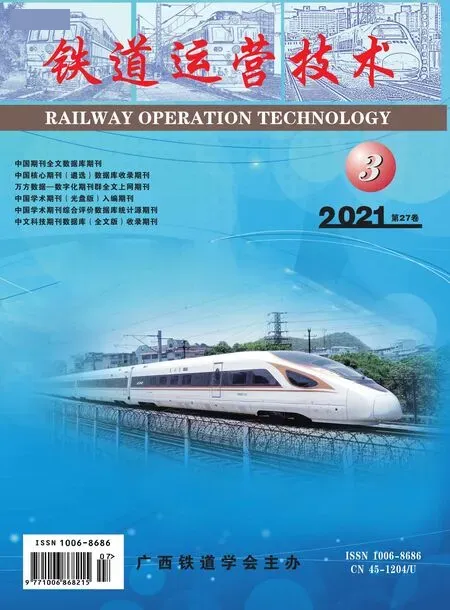地鐵車輛ATO模式下的控車方式研究
曹 斌
(上海阿爾斯通交通電氣有限公司,工程師,陜西 西安 710000)
0 研究背景
隨著國內地鐵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人們對出行工具的選擇意愿較多地集中在其能否使自己獲得舒適性上,因為,舒適性與否是乘客最直接、最具體、最迅捷的感官認知。地鐵是大中城市主要交通運輸方式之一。技術研究和實踐分析均表明,不同的地鐵車輛運用控車方式對乘客體驗、設備壽命、維修成本等的影響尤其是累積影響存在反差:合理的控車方式可以在上述方面獲得理想預期,反之,則會導致不良后果。基于此,筆者試以西安地鐵三號線ATO模式下的控車方式為例進行研究,力求找出合理的控車方式,旨在有效提高車輛乘客乘坐舒適性和制動系統的使用壽命、減少車輛閘瓦配件更換頻次和降低車輛養護維修成本。
1 現狀描述及問題分析
西安地鐵3號線運營4年多時間以來,其運維人員對于車輛制動閘瓦測量對比發現其磨損量明顯大于西安1、2號線的車輛制動閘瓦磨損量。通過調查發現其原因為車輛ATO控車方式存在一定問題所致。為有效消除所述問題,本文試以西安地鐵3號線正線運營的兩種控車方式進行數據分析,旨在為優化較為合理的的控車方式提供依據。
1.1 控車方式一數據分析通過查閱相關行車記錄和現場實測得到研究控車方式一所需的數據1和數據2,現作如下分析:
1.1.1 數據1分析 調查分析發現當車輛運營中速度為67 KM/H時,ATO先給出牽引指令信號,牽引力級位需求8%,經過100 MS,ATO直接從牽引指令信號切換至制動指令信號,制動力極位需求為8%,同時電制動進行力的輸出,由于多出一個牽引力上升過程,之后牽引力在下降,牽引電機勵磁都需要時間,因此,在電制動發揮600 MS后,為了滿足制動力需求,1車轉向架制動缸1施加壓力0.75 pa,經過200 MS后,5車轉向架制動缸1也繼續施加0.6 pa壓力,大約500 MS后撤出,基本為制動閘瓦貼合輪子后撤出。
1.1.2 數據2分析 調查分析發現當車輛運營速度為60.5 KM/H時,牽引指令,牽引力極位需求9%經過200 MS,ATO直接需求制動指令,制動力極位需求9%,同時電制動進行力的輸出,由于多出一個牽引力上升過程,之后牽引力在下降,牽引電機勵磁都需要時間,因此,在電制動發揮400 MS后,為了滿足制動力需求,5車轉向架制動缸1施加壓力0.35 pa,經過100 MS后,1車轉向架制動缸1施加0.8 pa壓力,大約500 MS后撤出。
1.2 控車方式二數據分析過查閱相關行車記錄和現場實測得到研究控車方式二所需數據1和數據2,現作如下分析:
1.2.1 數據1分析 調查分析發現當車輛運行速度為41 KM/H時,ATO需求牽引指令、極位力的需求為10%,經100 MS后直接轉至制動極位,制動力極位需求4%,此時牽引力上升需要200 MS(0-5 KN)之后牽引力需求再下降,而后電制動增加了200 MS后,由于電制動力反應時間短且小,為了滿足制動力需求,5車轉向架制動缸1施加壓力0.6帕,經過100 MS后,1車轉向架制動缸1施加0.2帕壓力,大約500 MS后撤出。
1.2.2 數據2分析 當車輛運行速度為71.5KM/H時,ATO需求牽引指令、極位力的需求為4%,而后ATO直接需求從牽引指令轉至制動指令,制動力需求8%,且持續增加,牽引力轉至制動力需要200 MS(0~5 KN),經過100 MS電制動力施加后,由于電制動力反應時間相對較短且力值較小,為了滿足制動力需求,1車轉向架制動缸1施加的壓力為0.75 pa,經過200 MS后,5車轉向架制動缸1施加0.9 pa壓力,大約500 MS后撤出。
1.3 兩種控車方式分析結論據牽引系統及設備性能實驗數據得知,當牽引力極位較小即0~5 KN時需要200 ms時間,電機勵磁及制動力上升需要時間為400 ms。
由控車方式1數據分析可以看出,都是在開始制動前先增加牽引力需求,之后再直接轉成制動指令及需求,增加了牽引力上升及下降的過程時間,進而加大了牽引力的響應時間,且制動系統不能過長時間的等待牽引(安全考慮),同時制動力也不充足,因此氣制動會瞬間補充500 MS左右,且補充壓力稍大,會造成輕微的磨損閘瓦。
從控車方式2分析可看出,此種狀況牽引力下降需要考慮車輛沖擊要求(≤0.75 M/S3),牽引系統需求按照一定力的撤出斜率減小牽引力,之后電機勵磁,按照沖擊斜率電制動力上升需要一定時間,因此也會有氣制動瞬間補充,仍為500 MS左右,同樣會導致輕微的磨損閘瓦。
經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基本結論:目前西安地鐵3號線運營線路中運用車輛控車方式1和控車方式2均會對車輛閘瓦有輕微磨損,因此,兩種控車方式都存在不合理性,需要進行優化改進,才能實現地鐵車輛運用的安全性和經濟性。
2 理論分析
2.1 車輛信號系統通訊原理西安地鐵3號線采用的是西門子信號系統,TCMS(車輛控制系統)是大連電牽研究所研制的產品,其中,兩者的通訊方式采用總線式RS485串行鏈路(如圖1所示),根據合同設定好的串行接口進行信號的互通,TCMS通過MVB網絡接收到來自RIOM(遠程輸入輸出模塊)的信號,RIOM通過RS485網絡接收到來自ATC(自動車輛控制單元)發出的指令信號,然后TCMS進行處理后轉至下方被動執行單元,例如:牽引控制系統和制動控制系統。TCMS和ATC之間通訊框圖如圖所示。

圖1 TCMS和ATC通訊圖
2.2 電氣配合理論分析西安地鐵3號線全長39 KM,共設26個站臺(其中高架站臺7個),線路中有隧道19個,從隧道出來的車輛爬坡度為30‰,其中輔助線35‰,由于坡度較大,對車輛的牽引和制動性能要求很高。西安地鐵3號線采用的是阿爾斯通牽引系統[2],車輛編組為4動車2拖車,牽引控制單元可控制牽引系統生成的電制動力,制動系統采用克諾爾公司制動系統,根據合同約定電制動力和氣制動之間要有較高的配合度,具體參數和狀態可通過實測獲得。如,在調試階段當速度達到7 KM/H時,牽引控制單元會發出電制動退出信號而后延遲200 MS,兩個系統同時根據提前設定好的斜率進行消減和增加,直至>2 KM/H左右時由氣制動完全接管,電制動完全退出(如圖2所示)。

圖2 電氣配合退出示意圖
通過分析調試階段的測試數據發現,車輛在載重到達AW2時,牽引系統電制動力可以達到完全發揮,不用增加任何氣制動,因此可以降低制動系統動作頻率及閘瓦磨損。
3 優化方案數據分析
通過上文的實際運行數據和牽引極位轉換理論分析可以看出,ATO在運行中,當牽引指令信號轉至制動指令信號前,一般會給予車輛相對很小的牽引極位需求(<8%)。根據西安3號線設定調試說明,按照AW2的牽引力計算整車輸出力為27 KN左右,對于運行車輛而言,會因整車輸出力太小不能滿足提升和保持車輛運行速度需要;此外,對于此力直接從牽引轉換至制動力需求來說,毫無意義,而且還延遲了電制動力增加的反應時間。
因此,在車輛運行時,盡量避免牽引小極位切換(<3%),同時還要注意在車輛運行時,盡可能將下一個極位轉換需求時間延長,使車輛在運行時可使剩余的牽引力全部退出后,再進行下一步動作。
經過上述分析找出問題成因后,與西門子工作人員進行會議溝通取得共識,即以進行軟件修改測試數據為依據,若測試與理論相同,可進行修改應用。根據商討方案,具體測試數據如下:
3.1 數據1當運行速度為43.8 KM/H時,ATO直接需求牽引指令、極位力的需求為1%,而后直接需求牽引指令轉制動指令,制動力需求為1%(600 MS),之后制動力需求增加,期間無任何氣制動力增加,均為牽引電制動,因為這600 MS為牽引電機勵磁及極位轉換提供了充足的時間,之后不需氣制動力補充,電制動即可正常發揮作用。
3.2 數據2當運行速度為62KM/H時,ATO直接需求牽引指令、極位力需求為0%,而后需求直接轉換至制動指令,制動力極位需求為0%,經1.1 s后直接需求增加,從中無任何氣制動補充。由于1.1 S可為牽引電機勵磁提供充足時間,并且當需要制動力時電制動力可以滿足正常發揮需要,不會造成氣制動力的補充。
3.3 測試結論通過以上2組數據采集分析可以看出,ATO控車時都是先會給出牽引指令、牽引極位需求,然后轉制動指令、制動極位需求為0%或很小(3%左右),持續一定時間(如果之前的牽引極位較小,1.5 S左右),制動指令、制動極位上升。此種狀況,在AW2及以下載荷,電制動力是能完全滿足制動力需求(80 kph~6 kph),時間僅為電制動按照沖擊斜率上升的時間,因此不需要氣制動補充,此過程不會發生車輛閘瓦磨損現象。
4 結語
本文以西安地鐵3號線車輛閘瓦易磨損為研究對象,運用現場實測與理論分析相結合方法,在找到問題成因基礎上,通過對信號系統軟件進行合理優化調整,找出了一種較為合適且較優的控車方式。經過西安地鐵運營車輛驗證本文介紹的優化方案測試結論是正確的,改進后的控車方式不僅能使旅客的乘坐舒適性有所提高,而且減少了車輛運營維護工作量,還有效降低了車輛運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