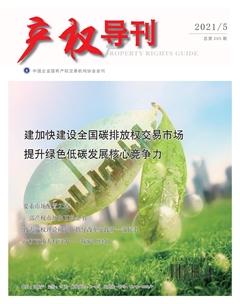境外國有資產公開交易是完善國資監管的重要內容
鄭凱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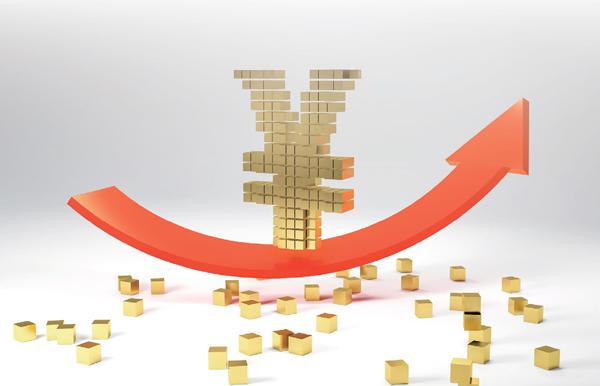
2021年1月21日,國務院國資委網站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國資發產權規〔2020〕70號,以下簡稱“《通知》”)。《通知》內容共九條,對中央企業履行境外國有產權管理主體責任、嚴格境外產權登記管理、加強個人代持境外國有產權和特殊目的公司的管理、加強境外資產評估管理及監督檢查力度等方面工作做出明確規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知》第四條強調,“境外國有產權(資產)對外轉讓、企業引入外部投資者增加資本要盡可能多方比選意向方。具備條件的,應當公開征集意向方并競價交易。”
境外中央企業,是指中央企業及其各級子企業在我國境外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依據當地法律出資設立的企業;境外中央企業國有產權,是指中央企業及其各級子企業以各種形式對境外企業出資所形成的權益。
近年來,隨著“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開展,我國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均加大了對外投資力度,國有資產對外投資總額不斷提高。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5月,僅中央企業的境外單位就達到9000多家,分布在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境外資產超過7萬億元,年創利潤1000多億元。央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合作共建項目超過3000個,已開工和計劃開工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央企項目占比超過60%,合同占比接近80%。可以想見,在“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中國企業境外投資將進一步增多,境外國有資產的體量還將進一步增大。
應該講,許多中央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加強境外國有資產監管,創造了不少好做法、好經驗,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境外國有資產監管中仍然存在一些盲點和弱點,成為國資監管的“阿喀琉斯之踵”。例如,有的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內控機制不完善,管理責任沒有落實;有的企業在境外資產運營中風險意識不強,重投資、輕管理,影響了境外國有資產的安全;加之境外機構“天高皇帝遠”,其負責人通常被賦予比境內機構負責人更大的決策權,這也使得監管難度加大,境外國有資產流失風險也相應加大。近年來,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暴露比較明顯,流失原因和流失路徑復雜多樣,一些中央企業為此付出了巨額學費。
“走出去”的中央企業絕不能成為“脫韁野馬”,國務院國資委一直非常重視境外國有資產監管工作。2011年6月和7月,國務院國資委接連發布《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國資委令第26號)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國資委令第27號,以下簡稱“《境外產權辦法》”),這兩個文件,前者側重監管的全面性,從境外出資管理、境外企業管理、境外企業重大事項管理、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等方面做出規定;后者則從最核心、最基礎的產權管理入手,對境外國企產權管理的責任主體、需要進行產權登記的情形、擬轉讓產權的評估、資金結算等做出了原則性規定,都是專門針對境外國有資產監管的最高級別規定,其后國務院國資委發布《關于加強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對央企境外產權管理的相關事宜進行了安排。到2017年,國務院國資委再次發布《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國資委令第35號),要求貫徹以管資本為主加強監管的原則,重點從“管投向、管程序、管回報、管風險”四個方面,依法建立信息對稱、權責對等、運行規范、風險控制有力的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體系。2018年5月召開的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再次明確指出,要從“投向、程序、風險、回報”四方面著力,加快完善國企境外投資監管體系,防范境外投融資、產權交易、代理擔保等過程中的利益輸送和國有資產損失。從以上規章制度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對境外國有資產的監管制度逐步完善,監管范圍愈加廣泛,監管力度正在持續增強。
本次《通知》同樣是這一態勢的延續。與10年前國資委發布的27號令中關于境外國有產權轉讓的相關規定:“中央企業及其各級子企業轉讓境外國有產權,要多方比選意向受讓方。具備條件的,應當公開征集意向受讓方并競價轉讓,或者進入中央企業國有產權轉讓交易試點機構掛牌交易”相比,本次《通知》將適用范圍從“產權轉讓”進一步拓展到了“實物資產轉讓”和“企業增資擴股”,同時強調要“盡可能”多比選意向方。這體現了《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即3號令過渡到《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辦法》即32號令的政策精神。
這里要指出的是,境外國有資產交易依然沒有要求必須進場交易,這是有其原因的。有別于境內國有資產處置已經形成了較為全面成熟的公開進場交易體系,這些境外國有資產所處的商業環境、法律環境與國內存在很大差異,且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也千差萬別,同時潛在買方不但有中國的國有與民營企業,也包括境外的買方(包括境外合資公司中的當地股東),按照目前的情況,國內從事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的機構也不可能在全球每個國家建立分支機構,這都給境外國有資產的規范高效交易造成了很大困難。
實際上,境外國有資產交易通過國內產權交易機構公開交易已經有過不少成功案例。以筆者所在的北京產權交易所為例,近五年來,北交所共完成境外國有資產交易41項,交易金額達到121.76億元,增值率達到25.76%。在這些成交項目中,主要是境外國有企業持有的境內資產,這類資產在整個境外國有資產體量中的占比并不高,為數眾多的境外國有企業持有的境外資產通過產權市場交易的案例尚不多見。
存在困難,就要解決困難。將企業國有資產納入市場化平臺公開交易,加之以中央和各地國資監管部門的嚴格監控,已經成為實現國有資產交易高效配置的最佳方式。如何將國內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的模式復制到境外國有資產,是未來國資監管需要破題的重要事項,也是國內產權交易機構努力的方向。
星光不問趕路人。我們相信,隨著國資監管體系的不斷完善,隨著中國產權市場服務功能、整體實力的不斷增強,境外國有資產依托產權市場進行公開交易有望逐步實現,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