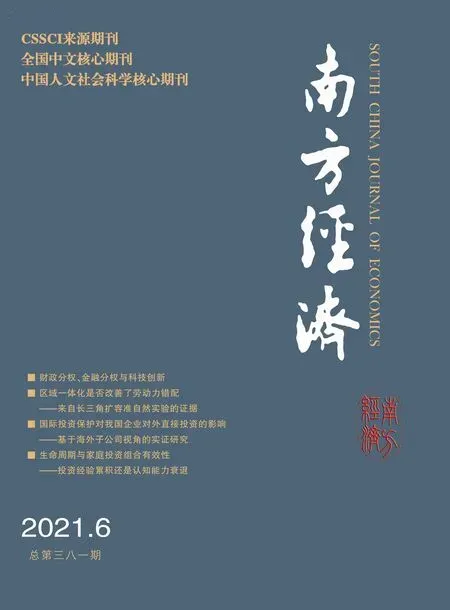基于廣義價值論的內生增長理論初探
蔡繼明 鐘一瑞 高 宏
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的中心議題,也是整個經濟學中爭議最大的部分之一。各種統計數據中,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現象,體現在一個加總的增長率上。對經濟增長的考量也是從宏觀因素開始。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總量的勞動和資本在外生的技術下通過一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加總為總產量。然后考量這兩個要素的動力學,以及對總體增長的影響。以總量的角度入手,這也是一直被詬病的地方之一。從現實來看,是每個交易主體的交換與創新形成了總體經濟增長,而不是相反。隨后新增長理論大多沿用了總量假設,只有一些模型采用同質性假設在一個多期模型中引入了個體決策,但是這樣的處理也是不徹底的。所以從總量來考察經濟增長必然會忽略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經濟增長中各個行為主體的相互關系,又比如什么樣的增長對社會是最優的。這些在傳統框架下都沒有得到滿意的回答。
本文所用的分析路徑主要通過簡單的假設,以個體這樣的微觀視角入手。所有的分析都圍繞依據比較優勢進行的交換能夠產生新增比較利益這一中心進行。在本文的模型中,交換是基礎。這一概念也在古典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斯密的絕對優勢分工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分工都強調了交換的作用。與新古典經濟學更多的設定在外生價格下的選擇不同,廣義價值論分工與交換的視角將原有的既定價格內生化,并著重考察了行為主體在交換中的互動,在此基礎上試圖解釋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回答什么樣的制度是一個好制度。
一、文獻綜述
所有增長理論的綜述幾乎都從哈羅德-多馬模型開始(Harrod,1939;Domar,1946),本文也不例外。這個模型在里昂惕夫生產函數的假設下,勞動和資本只能等比例增長,僅此一點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一般性。該模型的邏輯很簡單:儲蓄的資本通過資本產出比再次轉換為產出,于是有增長率G=s/v,這個式子是符合直觀的儲蓄的部分越多、用少的資本產出的越多,經濟增長的速度就越快的結論。在區分了實際的增長率、有保證的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后,該模型認為經濟增長的平衡是很難達到的,于是有了“刀鋒上的均衡”這種說法。
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實際應用范圍很小。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尤其是將柯布-道格拉斯函數(Cobb and Douglas,1928,以下簡稱CD函數)逐步進入到經濟分析中,新古典的增長理論發展到索洛模型(Solow,1957),其思想與穆勒(2013)的并沒有什么不同,只是技術、資本和勞動的組合形式在新函數下賦予了更多的經濟學含義。與哈羅德-多馬模型相比,索洛模型最顯著的變化是引入了技術,其產出方程為:
Y=AKαL1-α
(1)
兩邊取對數全微分,可以得到簡單的增長方程:
(2)
其中上標的點表示增長率,在式(2)中,總產出增長率取決于技術、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并且依據其在CD函數中的份額獲得在增長中不同的權重。因為技術不容易被測度,所以將經濟增長中除去勞動和資本的部分算作是技術對增長的影響,被稱之為全要素增長率。關于這個概念的經驗研究直到今天都是一個熱點,本文這里對此不做進一步的展開,而是介紹這個式子更一般的形式,這一形式用隱函數給出,表明了三者間可能的各種關系,如下:
Y=F(A,K,L)
(3)
對式(3)用泰勒展開,有:
(4)
將式(4)用CD函數代入并除以Y便是式(2)類似的形式。問題是式(2)是通過全微分得到的,而這又依賴于省略了式(4)中二階項以后的無窮小,也就是只考慮了式(4)等式右邊的前三項。對于理論研究這樣處理并無不妥,但是具體到計量分析,誤差的衰減速度很多時候并不能快到放棄后面的高階項。所以在用總的增長率減去資本和勞動的貢獻后,得到的不是技術的貢獻,而是技術、資本和勞動的多階互動加上技術影響結果。在現實經濟中,這三者顯然是互相影響的,甚至很多情況下是強影響。我們不能設定模型這三個變量相互獨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有的不少研究對這個問題的計量都沒有很好地擬合真實狀況,也造成了不同方法、不同數據估計下的誤差很大。
索洛模型的另一擴展是對穩態的考察,在將這個函數寫成人均形式后,新的投資等于:
dk=sf(k)-(n+g+δ)k
(5)
這里,生產函數f是一個滿足稻田條件(Inada Condition)的式子,這樣的處理既符合一般意義上的邊際遞減,也能確保與后一項相交從而保證解的存在。正是因為這樣的假設,使得存在一個穩態條件,在這個穩態中,人均資本、消費不會再變動,實現經濟增長只能依靠外在的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不僅如此,在引入動態時間后,索洛模型可以很容易地分析受到沖擊后達到穩態的時間,并引出兩國收入狀況的收斂情況。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貢獻和問題一樣大。在這個模型中將符合常識的認知用數學表達了出來,得到了諸如提高儲蓄有利于提高處于穩態時的人均收入等一系列結論。不過,在收益遞減的假設下,這個模型一定會收斂于內生增長率為0的穩態。外在的儲蓄率和技術的提高會形成新的穩態,并改變原有狀態下的位置和福利,但又會使得經濟向著新的穩態前行,經濟增長的動力重歸于0。索洛模型只能將長期增長歸咎于外生的技術,卻又沒能解釋為什么技術會上升,與經濟增長的相互影響是什么。新增長理論正是彌補了這一點,在收益遞增假設下重新考察經濟增長的規律。
整個新增長理論的中心就是尋找和論述遞增效應。新增長理論的開端是從Arrow(1962)提出“干中學”概念算起。他提到一個重要概念,“隨著時間的增加,知識會不斷增長”。這句話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解讀:首先知識是有積累效應的,也就是一種遞增的存在;其次,在Arrow(1962)的模型中,這一效應是外生給定的,或者說,這是個不完整的內生增長模型。“干中學”的意義在于,即使不用專門投入一部分人搞研發,在原有的生產過程中,仍然可以實現知識的積累從而提高效率。不過這也存在一定疑義:單一生產過程中的知識積累對增長效應的強度和持續性如何?如果很高的話就不用再單獨搞研發了,而這顯然不是現實世界的情況。所以后面的內生增長模型幾乎都把研發單獨列出來,用一部分資源進行具有遞增效應的專業化研發。
20多年后,Romer(1986)通過假定技術和知識的外溢發展了一個真正內生化的增長模型。其思想很簡單,通過現實中的一些遞增案例,并將其模型化。最終證明了在長期無限期界的增長中,均衡是存在的。Romer模型是新增長理論的開山之作,第一次建立了一個內生化的遞增模型,從而實現長期增長。以后的新增長理論,幾乎都是按照這個思路來的,區別只是尋找的遞增媒介不同以及數學方法上的高低。
Romer之后,新增長理論的另一個代表Lucas以人力資本視角來看待長期增長。最早提出人力資本非遞減效應的是Uzawa (1965)的模型。這個模型通過線性生產技術的假定,實現了長期持續增長。Lucas(1988)在新古典范式下,拓展了Uzawa所做的工作,先考察實物資本再到人力資本,借助其遞增效應實現了長期增長,其人力資本的積累方式由學校教育和干中學獲得。Glomm and Ravikumar(1992)在異質性個體的假設下,使用OLG模型分析了學校教育這一人力資本投資的作用,考察了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結論當然不出意外——公共教育更能縮減收入差距。
在Lucas之后,對人力資本的研究空前繁榮,涌現了一大批新成果。不過與Lucas(1993)模型用人力資本來描述遞增,其實質是將知識等非實體遞增效應固定在實體的依托之上相比,這些研究并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Young(1991)將干中學和規模經濟放在一起考察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國際貿易趕超發達國家。不過這一趕超仍然要以大家熟悉的條件為前提,即勞動力的豐富形成了更高的學習效應以及更強的規模效應。隨后,Young(1993)又將創新活動與干中學融合在了一起,思路是干中學可以獲得低成本的收益,因為不需要額外投入,這樣所產生的剩余可以為昂貴的創新活動提供支持,反過來創新又促進了干中學。關于R&D的外部性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備受經濟學家關注。除了Comin(2004)認為R&D外部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非常小之外,Melo and Robinson (1992)考察了出口導向型國家生產率和外部性的關系,結論是加入外部性后,能比傳統的新古典模型更好擬合數據。Pessoa(2010)則發現了R&D外部性對經濟增長的國別差異,也就是這種外部性的大小在不同的國家顯著不同,還有更根本的因素影響著經濟增長,研發和知識擴散的外部性大小取決于對產權的保護。Helpman(1993)認為知識產權保護阻礙了創新。這個模型仍然將經濟分為創新的北方國家和追隨的南方國家,并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效應對南方國家福利的影響更為明顯。
在傳統內生增長模型外,還有一條從產品質量升級來看待經濟增長的路徑,被稱之為“產品質量階梯”。Stokey(1988)最早闡述了這種思想,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但在一個動態一般均衡中,會伴隨著低質量商品的退出和高質量商品的進入。隨后,Aghion and Howitt(1992)建立了一個完全不同于過往的經濟增長模型,他們模型化了熊彼特關于創造性毀滅的思想,并指出了這種力量可以構成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他們的三部門模型中,中間品部門的創新促使最終品產出更有效率,同時中間品部門的競爭又會使得新的技術進步否定了原有技術帶來的利益,這就是模型中的創造性毀滅。隨后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1991b)推進了這個方向的研究。
另外,國內在對增長問題的經驗研究中,一個特點是將增長與具體經濟現象相聯系,包括了環境污染,人口密度以及官員流動方式等等(王立新、劉松柏,2017;孫攀等,2019;楊本建、張立龍,2019;陳紹儉等,2019)。這類研究以小見大,通過不同的計量方法試圖找尋具體現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
以內生增長模型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至今仍占據著主流,因為其解釋了原有理論所不能解釋的東西:為什么經濟可以長期持續增長。知識和研發的確具有遞增效應,只是這種遞增效應的強度和持續性是值得商榷的,不能試圖通過簡單地假定這種遞增效應一定大于1而獲得長期增長效應。內生增長理論最大的問題在于,如果要經濟持續增長,那么必須使經濟具有遞增效應,而遞增效應又會讓增長出現爆炸性趨勢,這與長期歷史事實是不相符的。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增長都是緩慢的,這意味著以遞增的視角來看待增長有一定的瑕疵。
一些經驗研究也否定了知識和研發的遞增效應。Jones(1995a,1995b)用不同的數據和方法都否定了這種遞增性。而對于人力資本的測度就更難了,在不同計量模型假設下,所得結論差異非常之大。這就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我們將長期增長建立在一個如此依賴于還沒有被完全證實的假設下是否恰當,長期經濟增長能否有一個更簡單、直觀符合邏輯的理論,這也是本文所要做的工作。
二、廣義價值論簡介
廣義價值論是蔡繼明教授(1985,1988,1999a,1999b,2010)1985年以來依據比較優勢原理創立的一種新的價值理論。這種價值理論根據交換的本質是實現各自的比較優勢,在交換中確定各種商品的價值,將機會成本作為核心變量納入到價值的分析框架中,通過比較利益率相等這個引力方程解出均衡狀態下的價值。比較利益率在廣義價值論中占有核心地位,其被定義為交換所帶來的新增收益與原有收益的比值。在廣義價值中,如果自身生產對方商品的機會成本過高,將會在交換中處于不利的地位,降低自己所生產商品的價值。這樣的道理是簡單的,因為自身生產商品的門檻很低,而轉換生產對方商品的門檻很高,那么自身商品的價值必然不高。
每個交易主體以不參加這項交易的效用(或勞動時間)為基準,依據比較優勢原理的分工,參加交易后會提高效用(或節約勞動時間)。這樣,參加交易的雙方相對于不參加狀態所獲得的同等的效用改進幅度就成為公平交易的標準,依此確定的商品交換比例即均衡交換比例,由這種均衡交換比例所決定的分配關系也自然是一種公平的分配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均衡交換價值的形成和相對比較利益的均等分配是按照同一個原則同時決定的。廣義價值論以一個全新的視角論述了價值決定和價值分配的完整過程,給出了一個既簡單清晰又符合直觀的邏輯。因為價值本質上是經濟主體在交換過程中的一種交換比例,這個比例本身也必然隨著分配比例的改變而變化,把價值決定和價值分配人為分開的兩分法不可能勾勒出反映財富創造和分配全過程的完整畫面。
廣義價值論正是在李嘉圖原有比較優勢原理的基礎上,將原僅適用于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原理應用到一般分工理論研究,將其忽略的分配問題納入到價值決定模型,并以比較利益率均等為中心重新論述了價值決定的一系列原理,形成了一個更具解釋力的全新價值理論。比較利益率均等原理在廣義價值論中占有中心的地位,該原理自從廣義價值論最初文獻(蔡繼明,1985)以來,伴隨著廣義價值論的發展有了不同的表現形式。下面對廣義價值論的介紹將從這一等式開始。
所謂比較利益就是生產者通過分工交換而得到的收益(效用),高于自給自足時的收益(效用)或高于其所讓渡的產品機會成本的差額。比較利益是分工交換(包括國內和國際分工交換)產生的原因。下面以兩部門(或兩個國家)經濟模型為例加以說明。
用自給自足和分工交換的效用來表示:
(6)

用分工交換中付出的機會成本來表示:
(7)

用分工交換節省下的勞動時間來表示:
(8)
其中,t11和t21分別表示部門1和部門2生產產品1 的成本,t12和t22分別表示部門1和部門2各自生產產品2的成本,x1和x2表示產品1和產品2的交換系數。式(8)是廣義價值論最初的式子,也是最經典的,其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將增加的利益歸為所節約的勞動時間。
從式(6)~式(8)可以看到,廣義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交易主體依據自身比較優勢進行分工,產生了新增比較利益,再依據比較利益率相等原則進行分配和確定價值。比較利益率相等表明了這樣一種關系,公允價值依據自身的成本和機會成本確定。對方生產自己商品的機會成本越大,自己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就越高,也就獲得了一個更高的溢價,在價值分配中占有更有利的地位。這也很好地說明了現實中的高技術、難以被復制產品的高價格,不僅僅是其生產成本高,更重要的是這份不可替代性從機會成本角度應該給出高溢價。
根據比較利益率均等原則即式(8)推出均衡交換比例:
(9)

在求出均衡交換比例后,再將單位商品的價值根據部門比較生產力的高低換算為兩部門原來投入的勞動量。由式(9)可推導出單位商品的價值:
(10)
由單位商品價值式(10)可推導出部門單位平均勞動創造的價值量:
(11)
式(11)表明,單位平均勞動創造的價值量與綜合生產力系數正相關:
如果CP1/2>1,單位平均勞動創造的價值大于勞動耗費;
如果CP1/2<1,單位平均勞動創造的價值小于勞動耗費;
如果CP1/2=1,單位平均勞動創造的價值等于勞動耗費;
也就是說,只有當CP1/2=1時,不同部門(不同國家)等量勞動才創造等量價值,不同產品的交換比例才等于各自耗費的勞動比例。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強調了價值的實現,投入的多少并不意味著在價值形成中就能全部表現出來。馬克思將其形容為“商品的驚險一躍”。在廣義價值論中,價值是在交換中實現的,是一種徹底的社會化價值。
由單位商品價值式(10)可進一步推導出部門內個別勞動創造的價值量:
(12)

式(12)表明,部門內單位個別勞動創造的價值量與其個別勞動生產力和部門綜合生產力正相關。
由部門平均勞動創造的價值量式(11)可推導出部門總勞動創造的價值量:
(13)
式(13)表明,部門總勞動創造的總價值量與綜合生產力系數正相關:
如果CP1/2>1,部門總勞動創造的價值大于總勞動耗費;
如果CP1/2<1,部門總勞動創造的價值小于總勞動耗費;
如果CP1/2=1,部門總勞動創造的價值等于總勞動耗費;
也就是說,綜合生產力水平高的部門(或國家),1小時勞動產品可以換取綜合生產力水平低的部門(或國家)耗費多個小時生產的勞動產品,如中美之間1億件襯衣與1架波音777之間的交換。根據“比較利益率均等”原則,參與國際貿易的各方各自獲得的比較利益與各自付出的機會成本之比必須都是相等的。根據這一原則決定的貿易利益的分配是公平的。
三、增長模型設定
描述增長有多種路徑,比如,新古典增長理論主要是考察勞動和資本投入的總量函數的擴大,新增長理論同樣以這一視角,無非加入了一個新的遞增部門。這種處理方式的好處是契合了經濟增長這一宏觀現象,同時將考察的重點放在各個總體變量的動態過程上。然而在這樣的總體框架中,我們無法得到相關個體的有用信息,更不可能分析這些個體的互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后來的RCK模型加入了個人跨期選擇,并分析了此時的消費和資本積累的動態路徑。不過這類模型僅僅考慮了單個個體在一定約束下的選擇,其相關變量的動態路徑更多的是在既定參數下的數學游戲。在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考量中,不同的角度會帶來不一樣的結論,但是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如何在長期維持一個不為0的增長率。
本文主要以間接效用代表的實際收入為依據論證增長問題,這是一個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可以論證在交換中兩個行為主體的互動及一系列經濟變量的關系。這樣做的好處是體現了分析從個體到總體的自然路徑,同時可以看到個體行為(比如掠奪了過多的收益等)對總體經濟增長的影響。而在建模方法上,本文延續了李亞鵬(2010)所做的工作。
本文認為經濟增長的本源是分工交換產生的經濟剩余即比較利益,而部分比較利益用于技術創新并進一步內生化分工則產生更多的比較利益,由此便可以實現經濟永續增長,其中不需要任何中介變量。李嘉圖語境下的一個簡單的數值例子就是:A、B兩個國家生產x、y兩種產品所花費的時間分別是(6, 3)和(1, 2)個小時,即國家B在兩種產品上都有絕對優勢,在斯密框架下分工是不會存在的。而依據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A、B兩個國家應該分別專業化生產y和x兩種商品,如果兩個國家原有時間稟賦分別為9個小時和3個小時,分工前生產了全社會總計2個x和2個y產品。在分工后,國家A的9個小時可以生產出3個y,國家B的3個小時也可以生產出3個x,與原來相比各自多生產出來一個。這多出來的剩余產品即分工交換帶來的比較利益,也就是經濟增長的實質。這樣的經濟增長是客觀的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增長的成果即比較利益該怎么分配?如果確定了比較利益的公平分配,再將所得的比較利益的一部分投入到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的開發,便可進一步促使分工交換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的內生性持續增長。
(一) 基本模型
追逐剩余是分工的意義,這一剩余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李嘉圖式的外在異質性剩余,這構成分工的基礎;其次是斯密范式的剩余,即在分工的過程中,將原有剩余繼續投入研發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本節先給出增長的基本模型,然后在后兩節按照技術不變和技術可變兩種情況加以考慮。
模型中有1、2兩個行為主體,產品1和產品2兩種商品,各自的初始勞動稟賦分別為T1,T2,而各自生產兩種商品的勞動時間為(t11,t12),(t21,t22)。本小節中討論的是長期問題,我們使用線性效用函數(1)這里使用線性效用函數是為了簡單直觀,而本文從分工角度對于增長問題的分析對于CD函數和CES函數都是適用的,所得到的條件也類似。這些結論也都已經成型,只是因為篇幅沒有在本文中列出。,為:
Ui=αixi1+βixi2
(14)
為了描述異質性,我們假設各自在序號商品上有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描述為:
(15)
因為生產效率q是勞動時間的倒數,式(15)也可以變為:
(16)
式(16)便是廣義價值論中相對生產力系數,也是分工交換產生剩余的根源。根據本文的異質性假設,每一個交易主體盡管在與自身序號一致的商品序號上有比較優勢,但是卻更偏好于另一種商品(2)這樣的假設初看有點讓人疑惑,行為主體為什么會偏好于自身比較劣勢的產品?但是細想之后,會發現其實這是對長期分工很好的描述。因為從長期看大多數時候,商品生產者都不是自己所生產商品的消費者(或者至少只消費這種商品極少一部分,在建模中可以忽略),而是用自身生產的商品來換取別人的商品,這正是商品經濟的本質。當然,這種完全替代所要的時間非常之長,更多的是一種理論意義的描述。而在中短期因為不完全替代,我們也能考慮行為主體自己留用一部分所生產商品的情況,并討論了中短期和長期的異同。同樣因為篇幅,這些擴展不在本文中列出。。所以,其自給自足的效用(實際收入)為:
(17)
而如果產生分工,則行為主體可以各自生產其比較優勢的產品,并相互交換,此時的實際收入為:
(18)
下面推導式(18)中的交換比例R2/1。從式(17)和式(18)中,根據比較利益率相等原則有:
(19)
將式(19)帶入到式(18),可得分工后的效用(實際收入):
(20)
用參與分工后的收益除以自給自足狀態下的收益便是分工收益增加的比例。這與楊小凱的分工理論不同,這里真正抓住了比較優勢分工的要義。式(20)除以式(17),有:
(21)
式(21)便是相對生產力系數的開平方,根據其參與分工的比較優勢條件,在式(21)中,最后一項根號中的值是大于1的。因為我們假設了交易主體1,2分別在產品1,2上具有比較優勢。式(21)根號中的值即相對生產力系數是大于1的。這一式子也反映了廣義價值論的要義,即參與分工交換的各方利益增加的比例相等。在分工后,各自的利益增加量為:
(22)
式(22)是廣義價值論框架下分工交換各方的利益增加量,即由于分工交換形成的剩余,只要分工交換持續進行,這個剩余就會不斷產生,并可以通過單純量的積累促進社會福利增長。同時,這一剩余還可以用于技術研發,提高生產效率,從而不僅能促進原有分工模式的進一步增長,而且由于處理剩余的方式不同,研發的性質不同,還會對分工方向產生影響。
不論分工方式如何,只要交換存在,就會不斷產生剩余。而在有了剩余后,更多的技術進步才成為可能,促使了經濟更快速的增長。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人類社會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增長速度都較慢,而只在工業革命之后,才出現指數增長的情況。上式還有更深刻的經濟學含義,分工的意義在于互相分取利益。一個交易主體的創新會對其合作伙伴產生正的溢價,式(22)中的q11和q22均進入到對方利益增加的函數中。這是因為廣義價值論將分工和分配納入到同一個體系中,由此揭示了比較優勢原理的全部奧秘。簡單地說,一方技術進步會產生一個收益,但是這個技術進步是在與對方交易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沒有分工與交換,自身也不會產生比較優勢。這樣,對方理應獲得一部分收益。傳統理論——無論是古典經濟學的斯密、李嘉圖,還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楊小凱,從來沒有如此深入地揭示出比較利益產生和分配的機理,而恰恰是這一機理才是我們理解內生增長理論奧秘的關鍵。
(二)技術不變下的增長
我們首先分析技術不變條件下的增長,論證即使不考慮任何的遞增效應,長期增長仍然能夠實現,意味著在技術不發生變化時,每一次基于比較優勢的分工交易都會產生一個剩余。式(21)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首先對比馬克思社會總資本的簡單再生產情況。簡單再生產描述的是生產規模在原有基礎上保持不變的再生產過程,類似的過程也出現在斯拉法沒有剩余的生產體系中。而在廣義價值論中,交換是為了獲得新增比較利益,并且在每一次的交換后形成了一個新的剩余。這個剩余不僅能補貼原有的耗費,還有余量。也就是說在每一次交換后,都能比既定條件下增加收益。而這是在技術不變情況下實現的,不依賴于其他條件。這一增加由如下途徑實現,在原有條件下因為新的剩余產生,使得人們可以用這一剩余內在的改善生活和教育,這又會促進勞動強度的提高從而形成了總有效勞動的積累。
(23)
依據比較優勢的定義,式(23)根號下相對生產力系數大于1,中括號里的值也大于1。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勞動資源稟賦會不斷增加從而導致實際收入不斷上升(3)這一數值變化比新增長理論直接假定規模收益遞增要小的多。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各行各業在成本和機會成本間還沒有太大的差異,或者說相對生產力差異很小,哪怕我們將相對生產力值設定為1.3,儲蓄率為8%(事實上,在生產力不發達剩余本身就很少的時候,這一儲蓄率假定已經很高了),也要經過100次交換才能實現總產品的三倍增加,加入交易成本,速度還會更慢。廣義價值論所描述的增長更符合長期歷史事實,在相當長的階段中,增長都是緩慢的。。除此之外,新增剩余還可以刺激人口的進一步增加,從而形成新的行業,這也就是外延的擴大再生產。新的行業必然會與原行業進行交換,可以在更廣闊的范圍中去尋找更低的機會成本從而繼續促進增長。這一思路擬合了經濟發展中部門越來越多的趨勢。
廣義價值論從一個新的維度重新論述了增長問題。這樣的增長源于分工對福利的促進,即使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也可以實現永續增長。這樣的經濟增長并不受技術的遞增或遞減效應所控制,而是源于交換帶來的收益。從現實來看,技術一直具有遞增效應的假設是值得商榷的,尤其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人類社會早期更是不可能具有遞增性的。而在廣義價值論框架下,交換可以帶來持續的額外利益,經濟是可以獲得永續增長的。
(三)加入研發的經濟增長
技術進步來源于投入和研發,從根本上講,進行技術創新要以一定的剩余為基礎,因為當期的投入并不能立即產生收益,就像在斯拉法維持生存的生產體系中,如果隨便抽出一部分資源進行研發,那么原有整個體系便會崩潰。
在廣義價值論的增長模型中,交換產生的新增利益對增長有雙重作用。首先是這一部分新增利益可以作為投入研發的初始資金,因為這部分資金并不會影響原有的生產體系;其次,在研發的遞增效應減弱并進入遞減階段時,仍然可以通過交換獲得比較利益,從而抵消遞減效應實現長期增長。
以行為主體1為例,將分工收益的一部分投入到技術進步中,有:
(24)
其中f11代表了技術研發函數,s11代表比較利益中投入產品1上的份額。分析式(24)可知,只要相對生產力不等于1,也就是比較優勢存在,q11就會不斷上漲,并且這種上漲是持續的,因為行為主體1發展自身比較優勢產品不改變分工方向,增長有一種加速效應。同時,行為主體1將剩余用于發展自身比較劣勢產品在一定的區間也能促進這種產品效率的提升,因為隨著q12增大,只要根號下的相對生產力系數還大于1,就可以保證上式為正。與其他理論顯著不同的是,在廣義價值論中,我們找到了發展一國比較劣勢產業的依據。這一依據不僅論證了比較劣勢產業增長的可持續性,也豐富了我們從福利角度看待比較劣勢產業。(4)分工所產生剩余的存在,使得有了發展比較劣勢產業的可能。因為剩余本身獨立于原有生產體系,便有自由的處置權。就像現在中國發展大飛機,未來的市場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這并不影響現階段的投入研發。當然,能否形成新的比較優勢還要看這部分投入對分工方向的影響,這也是下一節將討論的問題。以上關于行為主體1所說的,同樣適用于行為主體2。
下面將技術的隱函數用一個顯函數給出,以便進一步分析技術進步對生產力提高的影響,其基本思路是通過A(·)b這個顯函數將剩余即比較利益轉化為技術增長的目標函數。現今所有的新增長理論都將假定b值不小于1,以便在長期獲得一個持續增長效應。本節也首先控制這種效應,即假設b等于1。這樣做有兩個好處:其一,能夠得到一個簡單的顯函數,便于進行后面的推導,因為本節中的剩余從根本上說也劃歸為了技術,這樣的處理有著天然的同質性;其二,控制住了技術的遞增或者遞減效應,在一個報酬不變的非加速環境中來考量廣義價值論的增長,能夠反映主流經濟學界對于增長問題的核心關注點。代入有:
(25)
其中Aij將偏好和儲蓄率這兩個外生變量合二為一轉化為技術的相關參數,以使我們聚焦于模型本身,并分析將交換產生的剩余分別投入到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商品的技術研發上的增長效果。分析式(25)可以看到,行為主體1將剩余用于比較優勢產品的技術創新可以使得生產效率持續提高,因為q11的上升會提高相對生產力系數,而研發比較劣勢產品在一定范圍內也可以保證其技術水平上升。
為了考察技術在長期的增長率,我們將式(25)變形為:
(26)
式(26)就是技術在長期可能的增長率(5)這里想解釋一下為什么對于增長我們更關注的指標是增長率而不是增長量。因為隨著時間推移,技術不斷提高能夠帶來更多的實際產量,從而提升國民福利。但到了一定階段這一存量會非常大,那么從量上再提高一點以式(25)來看是有意義的,但是對于如此豐富的存量,提高的一點意義便很小了。而從增長率的角度來看卻不同,即使存量實際收入很高,只要能保持一定的增長率,哪怕這一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一,從長期看仍然有豐富的經濟學含義,對現實也更有意義。,而如果我們加上時間,將每一次分工所得收益即式(23)加入到增長速度中,有:
(27)
在廣義價值論中,因為分工交換帶來了額外收益,并且這一收益并不取決于技術是否遞增,所以在每次交換后可以將這樣的額外收益投入到新的技術創新中去。從式(27)可以看到,即使隨著生產力q11的不斷增大,表現在增長式子中分母中的q11增大,但是在交換中獲得的收益Gt也在隨著時間不斷增加。這樣,就對分子有一個抵消的作用,從而保證了生產比較優勢產品的技術在長期仍然可以有大于0的增長率。而在式(27)中,多期累積利益的加入也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即相對生產力大于1時)提高比較劣勢產業的增長率。
事實上,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都只考慮了諸如q11或者q12單方面的變動。而無論是行為主體1還是行為主體2,只要將每次獲得的剩余合理投入到兩種產品的創新中,就可以保證這兩個式子都在長期大于0,也就是比較優勢產品和比較劣勢產品都可以獲得永續增長。同時,對于同一個經濟系統來說,一個行為主體對比較優勢產品的技術創新,會給對方的增長率帶來正的外部性。
比較在分工之前的狀態,因為效用函數的完全替代,此時行為主體1只生產商品2,而行為主體2只生產商品1,其產量分別為:
(28)
在式(28)中加上效用函數便是未分工系統中的實際收入,因為只能自給自足,所以如果要進行技術創新,必須從原有的里面取出一部分來。以行為主體1為例,此時的實際收入為β1T1q12,與前面的轉換函數一樣,則技術創新的動態方程為:
(29)
增長理論關注的是技術是否具有遞增性,即b能否在長期大于1:如果b>1,式(29)在長期可以獲得持續正的增長率從而不斷的提高實際收入;而當b=1時,經濟只能以一個初期既定的增長率增長下去。特別是在技術不具有遞增效應,此時b<1,會導致式(29)在長期趨近于0,技術的長期增長不可持續,而實際收入也必然會陷入停滯。主流經濟學關于增長所有的討論都是在b≥1的假定基礎上進行的。也就是文獻綜述部分所說的,先假設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礎上來論述經濟增長的各種效應,區別只是模型數學方法的高低。
而廣義價值論框架下的增長,抓住了分工交換帶來新增比較利益這一經濟增長的實質。我們首先在式(25)中控制了技術的遞增性,使其等于1。這樣加入了分工利益后便可以得到經濟持續增長。換句話說,如果技術呈現遞減效應,也就是在b<1時,也可以對沖掉b<1時的影響,仍然實現長期增長率為正。當然,廣義價值論也不否定技術創新的作用,只是強調在分工下,技術的遞增性并不構成增長的條件,并且分工也放大了技術帶來的收益。
(四)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和意義
因為有了技術進步,從而對原有價格體系產生了新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內生化了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正如前面所說的,比較優勢原理本身就不是一個外生理論,產生這樣的誤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比較優勢原理的最初創立者李嘉圖當時只考慮了外生的情況,同時20世紀初的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影響非常大。廣義價值論既考慮了初始態的外生異質性,又將這一異質性差異投入到新的研發中,使得兩個行為主體相對地位產生新的變化,從而完整地表述了一個動態化的比較優勢理論。在這一框架下,異質性不再固定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工與研發中不斷動態變化。我們以相對生產力系數來解讀這一過程,有:
(30)

這也為現階段中國發展比較劣勢產業提供了理論依據,主要表現為三點:首先,發展比較劣勢產業可以直接改善貿易條件,提高本國的福利,這一特點在前面單個行為主體的福利表達式中都得以體現;其次,發展比較劣勢產業在中短期和長期都是可持續的,并且也能對總體福利產生正影響;最后,經濟正是在你追我趕中不斷提升迭代,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在競爭中一次又一次的逆轉,技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形成了長期經濟增長并提高了所有參與者的福利水平。
廣義價值論回到了分工交換的本源上,從分工交換產生利益到公平地分配這一利益,引出了經濟增長的動態路徑。市場中各個交易者為了獲得更高的福利,將分工交換新增利益的一部分用于比較優勢產品和比較劣勢產品的技術創新,提高其生產率:前者能產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自己和交易者的福利,后者在提高自身福利的時候會有損對方福利,這樣又對整個分工產生了影響,形成了新的分工模式和新增比較利益。由此循環往復,經濟增長便在一個更簡單的框架中得以實現。當然,這里并不是排斥規模收益遞增,而是將內生增長一般化:如果不需要遞增就可以在交換中實現長期增長,那么加入遞增之后,這樣的速度便會更快。馬克思也曾把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因素歸納為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等五個因素(馬克思,1972)。其中“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顯然指的就是與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相對應的社會分工,也就是廣義價值論以及本文所討論的一般意義上的分工交換,而“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則與規模經濟有關。廣義價值論將社會分工的細化和深化、規模收益遞增和不變、比較優勢的強化和比較劣勢的弱化等所有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力并進而提高比較生產力的因素均納入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并闡明了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提高,都可通過分工交換表現為比較利益的增加,并根據比較利益率均等原則實現了公平的分配。
近年來發生的中美貿易爭端,撇開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不說,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于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并沒有對貿易的內在機理給出一個邏輯自洽的完整描述,尤其是忽略了機會成本的影響。薩繆爾森(Samuelson, 2004)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按照廣義價值論,相對生產力系數的逆轉是一個自然過程,并且從長期來看,這一逆轉并不會損害美方福利,中美仍然可以依據比較利益率均等原則公平地分享技術進步之后新增的福利。廣義價值論為解決這一爭端提供了一個更為科學的思路。
四、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什么樣的增長是最有效率、最公平的?對這一問題一直沒有一個被普遍認同的標準。主流經濟學在論述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更多地是著眼于保護產權的角度,而沒有涉及應該如何分配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各種產權在交易中理應獲得的公允份額。新增長理論和新古典增長理論因為廣泛使用總量生產函數,更不可能揭示公平與效率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無論是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資本的黃金率還是新增長理論中資本的動態路徑,抑或是大道理論,都沒有解釋經濟增長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本節將論述為什么基于比較利益率均等原則的分配對于經濟增長是最優的。
對制度的經濟學分析可以追溯到康芒斯(2013),科斯(Coase,1937,1960)從交易成本的角度界定了產權,認為當交易成本為0時,初始的產權配置不影響整個經濟的效率,總能實現帕累托最優。盡管科斯沒有將其理論稱為制度經濟學,但是交易成本卻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范疇。諾思(2014)則將產權和社會制度均視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阿西莫格魯(Acemoglu et al., 2001,2002,2005)。因為所處時代的差異,與前三位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不同,阿西莫格魯的研究廣泛使用現代經濟學工具,尤其他的經驗研究本身就是應用計量的典范,這也為制度經濟學的規范化和傳播提供了便利。
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主要的一條路徑是沿著產權展開的。諾斯和托馬斯(North and Thomas,1973)認為產權保護對中世紀的貿易興起具有重要作用,并考察了西歐各個國家的績效,提出交易費用對產權制度變革的影響具有臨界效應。Knack and Feefer(1995)的經驗研究證明了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正相關。Aron (2000) 從長期產權和投資的關系切入,論證了產權對于資本市場以及長期增長的重要性。Acemoglu et al. (2001) 完整地論述了產權的建立以及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績效。在這個模型中,他們以病死率為工具變量考察殖民者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制度,以此證明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內在邏輯是外生疾病影響較大的地方(如非洲等熱帶國家)殖民者傾向于短期掠奪,所以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這又反過來影響了長期經濟績效;而較宜居的地區殖民者為了長期利益愿意建立一個更有效的產權制度,所以這些國家(如澳大利亞)能夠取得較高的國民收入。隨后,Acemoglu et al. (2002) 沿著類似的思路分析了殖民地的“制度逆轉”,在原來富有的地區采用掠奪性制度,而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地方建立有利于進一步增長的制度。而Acemoglu et al. (2005) 從大西洋貿易利益分配的角度,論述了商人階層與君主階層的對抗,最終演化出不同的制度。而新的制度變革又促使了經濟往不同的方向發展。據此,他們試圖解釋西歐國家發展的差異。
保護產權,就保護了財產權和收益權,這才能讓持有者有動力將這部分資源繼續投入到生產中從而促使可能的進一步增長。這是以往經濟學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主要范式,幾乎所有的經驗研究也從不同角度論證了這一點。不過這種思路仍然遺留了一個重要問題,各個行為主體在交易中依據自己產權所應獲得的收益是多少,如何分配這一新增收益。同時,原有理論只論證了產權激勵的影響,沒有論證不公平交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這無疑是重要的。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考慮界定和保護產權的重要性,還要回答一個基礎性問題:什么樣的制度是好制度。本文認為,一個好制度應該是保護了各個行為主體的公平交易,使得其所獲與其貢獻對等。
與傳統制度經濟學的切入點不同,本節試圖用增長的基本模型來探討好制度的屬性,這里更多地是從制度的本源入手,分析一種制度在交換中應該如何維護交易者雙方的利益。
交易者根據自己的絕對成本與機會成本形成交換比例,如果一方交易者依據固有優勢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對社會總體福利的影響是什么。回答這一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掠奪為什么是不可持續的,而最終的均衡會自發地回到比較利益率相等。
假設行為主體1生產兩種商品的絕對優勢都更高,并以此在交易中占據更優的地位,獲得更高的比較利益率,模型化為:
(31)
其中,θ大于1,表明行為主體1獲得了更大的不均等利益。解式(31)有:
(32)
觀察新的交換比例,當θ等于1時,也就是公平交換的情況與原來求得的交換比例相等。在得到了新的交換比例R′后,我們可以代入到交換后的效用函數中去,再將公平交易和不公平交易的收益做減法,則公平交易和非公平交易的社會總福利為:
(33)
(34)
式(33)減去式(34)就是兩種情況下福利的變化,式(35)表明了公平交易的福利與偏離比較利益率均等之后的福利的大小:
(35)

五、總結
本文在廣義價值論的框架下從分工的視角分析了長期增長問題。因為基于異質性的交換能夠產生一個客觀收益,這一收益便構成了長期增長的來源。同時,也是因為這一多出來的收益,才使得進行研發等活動有了最初的積累。在長期,無論是比較優勢產品還是比較劣勢產品都可以獲得一個不為0的增長率。
在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下滑壓力增大的背景下,我國提出“雙循環”的發展格局。從本文來看,促進交換、破除壁壘就會帶來一個廣泛意義上的增長。而“雙循環”正是將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統一起來,力求在國內外尋找可能的更低的機會成本并與之交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制度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瓊斯、羅默(2009)也提到了這點。制度規定了利益的分配,以及這個分配如何影響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現有的研究沒有很好的說明這一問題。分配本身就是廣義價值論題中應有之義,構建一個新的制度模型具有比其他理論天然的優勢。本文做了一些嘗試,但還有很多方向值得進一步挖掘。如果能量化制度,應該會有一些更能解釋政治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新洞見,這也是廣義價值論以后應該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另外,怎樣運用最新的計量方法,對廣義價值論所提結論進行經驗檢驗也是未來努力的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