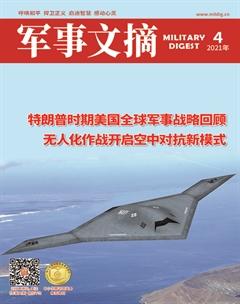智能目標識別在未來軍事作戰中的應用與思考
翟佳 郭單 李元 董毅
軍事技術決定戰爭形態。人工智能作為最重要的顛覆性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日趨廣泛深入,成為引領世界新軍事革命的主要因素,未來必將改寫戰爭規則,催生智能化戰爭。智能目標識別,作為一項面向探測預警、情報偵察、態勢感知、精確制導等多個軍事應用領域的關鍵使能技術,以人工智能為技術手段,能夠解決戰場自動目標識別的關鍵問題,是打贏未來智能化戰爭的重要手段之一。
智能目標識別橫空出世,勢不可擋
“一旦新技術在既有技術體系堤壩上打開一個缺口,洶涌潮水的到來就不會太遠。”這句話用來形容智能目標識別再合適不過。
2012年,以深度學習為核心的智能目標識別在學術界名聲大噪,這一切緣于當年的ILSVRC評測。ILSVRC是近年來機器視覺領域最受追捧也最具權威的學術競賽之一,代表了以圖像、視頻為數據源的目標識別、定位、檢測等機器視覺領域的最高水平。在這之前,最好的Top5算法分類錯誤率在25%以上,而2012年AlexNet首次在比賽中使用了深層卷積網絡的智能目標識別方法,錯誤率僅為16%。之后,每年都有新的好成績出現,目前最優的Top5分類錯誤率均在5%以下,已超出了人類的識別水平。
2018年,一篇源自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新聞稿,將具有智能目標識別的遠程反艦導彈(LRASM)推到風口浪尖。該新聞稿稱:“德克薩斯州戴斯空軍基地第337試驗中隊的B-1B在加利福尼亞州穆古角的海上發射了LRASM,成功擊中了海上目標并實現測試目標。”這其中,智能目標識別貢獻了巨大力量。

AlexNet模型框架
LRASM是美國海軍與美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正在研發的新一代反艦巡航導彈,可為美國海軍提供進行遠程目標打擊的先進反水面作戰能力。高度智能化的目標識別能力,使得LRASM飛抵目標區域之后,能夠根據識別算法對區域內探測到的多個不同信號進行分類,逐步縮小不確定區域,最終實現復雜戰場環境下的艦艇目標識別,并根據目標幾何特征對特定目標點進行打擊,形成高度自主的作戰能力。
智能目標識別制勝的內在機理
在信息化戰爭中,動態海量數據已超出人腦處理能力的極限,智能目標識別的出現有著天然存在的迫切需求,但內在的作用機理才是其表現突出的制勝關鍵。
智能目標識別是采用人工智能技術途徑,通過接收、探測目標與環境數據,進行有效的特征提取和樣本積累,經過充分學習以實現對未知目標的認知與辨識,從而判定目標類別、真假和屬性等信息。區別于其他目標識別方法,智能目標識別具有自主學習、智能推理、在線升級等特點。
智能目標識別衍生于自動目標識別(ATR)技術理論體系,伴隨著人工智能的演進,逐漸呈現出獨有的特點。自動目標識別技術的發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經歷了近50年的發展歷程,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自動目標識別算法。縱觀自動目標識別領域的發展,始終在致力于提高自動目標識別系統的自適應和學習能力。早期的系統以模式識別為主,其后發展了基于模型和基于知識的識別系統,又將人工神經網絡、支持向量機等機器學習技術應用于自動目標識別領域。2006年,伴隨著大數據技術、高性能計算資源的發展,以深度學習為核心的智能目標識別終于應運而生,并在圖像、語音、語言識別等領域獲得了成功的應用,成為解決自動目標識別問題的一種有效途徑。

LRASM打擊體系示意圖
以深度學習為核心的智能目標識別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原因在于其實現了人工智能技術從“計算”到“學習”的轉變。此前,人工智能算法大都基于已知規律或確切邏輯關系建立數學模型,建立后即可運用,其核心是計算,智能實現就是按規則演算。這些算法雖然準確高效,但它們只能按照既有程序進行計算,無法應對超出程序設定的變化,是封閉的靜態系統。深度學習則不同,它由多層模擬的神經元網絡組成,建立后不能直接使用,必須先進行大量訓練,在訓練中不斷提高,進而變得越來越“聰明”,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通過海量數據的訓練,神經元網絡逐層遞進并提取出物理世界的各種特征,發現其模式、結構、規律,不斷“進化”出更高的智能水平,其核心是學習。經深度學習形成的人工智能,一些方面甚至會超越人類。

深度學習的機理
隨著現代戰場在空間上的拓展,復雜多樣的戰場探測器遍布陸、海、空、外層空間和電磁網絡空間,智能目標識別所適用的探測數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通過對點信號級、序列信號級、圖像級、運動軌跡級、融合數據級等探測數據的判定,得到目標類別、真假和屬性等信息,在偵察預警、情報分析、精確制導、電子認知等軍事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偵察預警方面,美國DARPA實施的對抗環境下的目標識別與自適應(TRACE)項目力求開發一種準確、實時、低功耗的雷達目標識別系統,有效降低了密集作戰環境中誘餌和背景等對目標識別系統有效性的影響;在情報分析方面,密蘇里大學使用智能目標識別技術分析微型圖像,搜索識別我國東南沿海防空導彈陣地,在準確率與人工目視基本相當的情況下,識別效率提高了81倍;在精確制導方面,美國的“心眼”項目聚焦自動接收并解讀真實場景影像,可實現快速自動識別潛在威脅,為目標打擊提供依據;在電子認知方面,美國行為學習自適應電子戰和自適應雷達對抗項目均重點研究了如何將智能目標識別應用于雷達電子對抗過程,以便于可以快速識別出敵方新的、未知的無線電威脅。
智能目標識別是打贏
未來戰爭的關鍵一環
算法是人工智能技術的核心,掌握更強算法的一方可快速準確預測戰場態勢,創造出最優戰法,實現“未戰先勝”。智能目標識別作為一項面向探測預警、情報偵察、態勢感知、精確制導等多個軍事應用領域的關鍵使能技術,是打贏戰爭智能化進程中算法戰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方面,智能目標識別是奪取學習優勢、認知優勢、決策優勢的關鍵。一是能夠通過知識積累和優化,精準提取目標特征規律,縮短個體“學習曲線”;二是能夠及時有效處理海量情報數據,促使數據處理水平快速增長,有效解決“信息迷霧”;三是具備自適應能力,可為指揮決策提供強有力支撐。
另一方面,智能目標識別是適應作戰空間拓展、作戰時間壓縮的關鍵。在現代戰場,作戰空間拓展到陸、海、空、外層空間和電磁網絡空間,其遍布的各種傳感器產生的情報偵察與監視預警信息呈爆炸式增長,導致戰場信息收集不及時、有效信息產出時效性低、反饋失誤等嚴重問題。同時,無人機蜂群等新式智能化武器裝備與新型作戰樣式的提出,對指揮員決策的時效性、準確性、靈敏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智能目標識別可將人從生理極限中解放出來,基于自主學習、智能推理、在線升級等技術優勢,綜合不同數據來源,提升數據處理和數據挖掘效率,縮短觀察、判斷、決策、行動(OODA)環的反應時間,減少戰場態勢感知的不確定性,在智能決策、指揮協同、情報分析以及電磁網絡攻防等關鍵作戰領域發揮作用。
迎接智能目標識別
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未來戰爭的智能目標識別發展趨勢,既是重大挑戰,更是難得機遇。近年來,美國等國積極探索智能目標識別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認知域等戰爭空間中的創新運用,我方若想謀求建立新高地的軍事優勢,必須冷靜、客觀、全面地分析智能目標識別的適用邊界、科學問題和技術短板,既推動理論創新,也避免盲從追趕;既大力發展推進智能目標識別研究,也積極探索非對稱反制戰法和力量手段。
智能目標識別絕非萬能。一是脆弱性。智能目標識別優良的表現,并不意味著其完美無瑕、毫無漏洞。以圖像智能目標識別為例,當攻擊者利用智能目標識別算法模型的漏洞,在裝備目標上加裝特定偽裝圖案后,便可對衛星、無人飛行器和各類智能裝備背后所依賴的軍事圖像識別系統進行攻擊,使其無法正常識別視頻圖像內容。為應對新形勢,一方面需要利用智能目標識別技術研發新型軍事裝備;另一方面要了解對手可能采用的智能對抗技術和裝備,并尋找其中的算法漏洞,研發相應的防御和反制措施,使智能目標識別在攻與防的環境中不斷發展。

智能對抗案例
二是透明性。智能目標識別模型的復雜性為其帶來了非凡預測能力,然而若其提取的深層特征不直觀,無法理解算法決策過程,難以分辨某個具體行動背后的邏輯,就會導致識別風險不可控,無法準確估計識別算法的適應性。
2016年10月,DARPA發布“可解釋的人工智能”項目(XAI)的廣泛機構公告,其目標是建立一套新的或改進的機器學習技術,生成可解釋的模型,結合有效的解釋技術,使最終用戶能夠理解、一定程度上信任并有效管理未來的人工智能系統。通過該項目,新的機器學習系統將能解釋自身邏輯原理,描述自身的優、缺點,并解釋未來的行為表現。
智能目標識別實戰化之路坎坷艱辛。目前,智能目標識別還不適于強雜波的、擁擠的、復雜的、快速變化的軍事應用場景。以美國為代表的軍事強國早在40年前就期望實現精確制導系統的智能化,但目前大多數導彈系統并沒達到智能目標識別的預期目標,這包含智能目標識別在數據、算法、理論方法等層面遇到的應用瓶頸和科學問題。

DARPA 的XAI項目總體框架
一是數據的充分性、有效性難以保證。數據的充分性、有效性將直接影響智能目標識別的性能。然而在實際作戰中,戰場環境的復雜性、目標特性的不確定性和對抗條件導致的信息不完全性,將會帶來目標特征的不可重復性、復雜多變的雜波背景環境、低對比度、遠距離、存在偽裝、遮掩與干擾、外界場景的多變性(不同的地理區域、戰場條件和氣象條件)等問題。當提供的是稀疏、不完全、分布不均、質量不足的數據集時,許多智能算法將無法展現良好性能。
二是現有算法的局限性亟待突破。現有的許多商用智能目標識別算法的一個重要限制,是它們對訓練數據集的批處理。采用批處理時,需要一次得到所有的訓練數據,使學習算法構建一個可運行在實際應用場景中的模型。當積累數據的體量無法達到訓練要求時,就需要深度網絡實現在線學習與現場訓練。然而,如何設計穩健的在線學習方法,仍然是目前軍事應用中的棘手問題。同時,針對復雜戰場環境下無法獲取數量充足、分布全面、質量優秀的樣例數據的實際問題,需要將無監督、半監督、有監督方法相結合,借鑒先驗知識和關鍵特征,降低對數據的依賴,探索對噪聲不敏感,并能采用稀疏標注或者完全沒有標注的數據集的學習方法。
三是智能目標識別缺乏理論支撐。由于缺乏科學理論的支撐,沒有建立信息論測度來確定智能目標識別系統的性能邊界,難以理解和預測智能目標識別系統的性能。同時,軍用領域的智能目標識別缺少對試驗測試領域的研究,特別是試驗、驗證、測試、評估、鑒定的核心技術體系,及基本支撐理論、綜合試驗環境、評估指標體系等關鍵基礎性問題尚未有實質性突破,尚無法回答智能目標識別在軍事應用領域的準確性、可用性、有效性。
責任編輯:葛??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