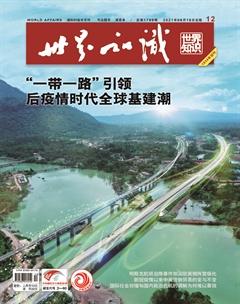法國社會已深陷“撕裂癥”
慕陽子

2021年5月19日,法國警察團體在首都巴黎舉行集會,要求議會通過加強保護警員權益法案。
4月底以來,法國部分退役、現役軍人在極右翼媒體《現實價值》先后發表兩封聯名信,指責政府政策,引發全法輿論嘩然。該事件是當下法國社會“撕裂癥”的新表現。近年來,法國社會亂象頻出,恐襲、暴力事件、抗議、罷工、游行此起彼伏,背后是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的時空背景下內部各種利益、思潮、代際之間的撕裂與對抗。這一過程爆發出強勁的沖擊力,也給法國執政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法國社會亂象不斷
2017年,馬克龍當選總統后,曾立志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彌合國內經濟社會裂痕,恢復國家信心,帶領法國和歐洲“重回世界舞臺”。幾年下來,法國社會內部矛盾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愈發尖銳。
反改革抗議此起彼伏。馬克龍上臺四年多來,針對勞動力市場、鐵路、公務員、教育、稅收、失業金、退休制度等各領域推出結構性改革,導致社會各群體抗議不斷,其中“黃馬甲”運動和反退休制度改革聲勢最大。2018年11月起,法駕車人通過網絡自發串聯發起“黃馬甲”運動,抗議馬克龍政府為實現綠色轉型承諾而增收燃油稅的計劃。該運動以身著黃背心為標志,以公路環形路口為聚集地,以周六為固定抗議日,動員人數最高時達30萬。在激進分子煽動下,該運動暴力程度一度不斷升級,在城市中心焚車、搶砸店鋪、襲警等混亂場景持續上演,造成法國自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最大的社會動蕩。2019年12月起,法公交部門呼吁啟動“無限期罷工”抗議馬克龍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各行業積極響應,動員人數最高時達150萬人。這也是法國近25年來公交部門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罷工,幾乎使法國陷入癱瘓。
宗教極端主義威脅上升。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族裔聚居區頻現違法行為和群體性暴力事件。近年來,“郊區暴力”升級為“血腥恐襲”,《查理周刊》系列恐襲(2015年)造成17人死亡,巴塔克蘭音樂廳系列恐襲(2015年)造成130人死亡,尼斯恐襲(2016年)造成86人死亡,2020年10月發生的“巴黎教師斬首案”和“尼斯圣母大教堂恐襲案”再次震撼全法。與此同時,部分穆斯林社區近年來“伊斯蘭化”趨勢加劇,法國的青少年穆斯林居民極端化傾向尤其明顯,引發社會廣泛憂慮。
安全政策“左右為難”。法近兩屆政府均將“安全”視為優先事宜,出臺增加安全預算、增雇警察和憲兵、完善安全立法等政策。2020年以來,馬克龍政府重點推動兩項安全領域新法,分別為“加強共和國原則法”和“整體安全法”,旨在從源頭遏制宗教極端主義,強化法國世俗價值觀;加強對警察、憲兵等執法者的保護,提升執法效率與能力。然而,上述法律措施卻面臨被左右政治勢力共同聲討的窘境。部分左翼認為,該法案與法國自由、平等、人權等傳統價值觀嚴重相悖,指責其“對少數族裔群體進行鎮壓”“侵犯言論自由”“使法治國家淪為警察國家”等。部分右翼政治勢力則認為措施過于溫和,無法有效改善不斷惡化的治安環境。
環保議題成為新的社會矛盾點。20世紀60年代,法政府為開發西部地區,計劃在大西洋盧瓦爾省的蘭德斯圣母鎮修建大型機場。該計劃使各黨派、各地區、各經濟和政治力量間爭吵了50多年,最終在2018年由馬克龍裁決放棄建設,其間造成的損失難以計數。裁決之后,全法的環保人士在該地區安營扎寨,進行各種環保生活試驗,試圖組建無政府社會。政府不得已出動2000余警力強行驅逐,才結束這場鬧劇。2021年5月,法國一項關于氣候問題的法案在國民議會進行了三個星期、總共110多小時的辯論后才最終通過,創下了第五共和國的最長記錄。當議會多數派歡呼該法將給馬克龍的總統任期“打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時,大量左派議員卻認為,面對迫在眉睫的氣候問題,該法案的措施“遠遠不夠”,法案甚至引發極端環保分子抗議示威。
“法蘭西群島”
法國著名社會分析人士杰羅姆·富爾凱曾在《法蘭西群島:一個四分五裂的多元化國家的誕生》一書中提出,法蘭西作為一個整體民族已不復存在,法蘭西共和國也不再是法國《憲法》所規定和描述的那樣“完整且不可分割”。他還提到,過去法國人心目中的法國是一個“天主教加共和思想加法蘭西高盧白種人的國度”。今天,法國社會價值理念的基石已土崩瓦解,法國社會儼然已成為了一個“由不同種族和文化組成的群島”。

2021年5月5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夫人布麗吉特出席法蘭西帝國皇帝拿破侖一世逝世200周年紀念儀式。
觀察這個日益“群島化”的社會,人口結構變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法國國家統計局2021年數據顯示,2006年至2017年增加的人口中,移民占比44%,幾乎與人口自然增長持平。統計局2017年數據顯示,法國本土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數為1.8,馬格里布地區(埃及以東的北非地區)移民女性為3.5,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女性為2.9。隨著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人口占比的持續上升(當前約為8%~10%),“文明沖突”也隨之更加尖銳,圍繞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移民與治安等問題的爭議不斷升級,成為法國社會分歧的最大引爆點。
在經濟生活領域,法國社會則存在“精英法國”與“邊緣法國”兩個平行世界。全球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法國中產階級規模萎縮,金融資本加速集中,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法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5%最富有法國人資產占法國所有家庭凈資產的三分之一,1%最富有的人擁有16%的財富;1996~2016年,10%最富有人群平均月收入增長近1000歐元,而10%最窮人口月收入僅增長約100歐元。“黃馬甲”運動抗議的內容就不只限于反對增收燃油稅,還針對法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加劇等不平等現象。法國蒙田研究所2019年3月發表的一項關于“黃馬甲”運動的研究發現,在一萬名受訪者中,絕大多數將自身購買力下降列為參加抗議活動的主要動機。人們將怒火集中在被視為“精英代言人”的馬克龍個人身上,“馬克龍想到世界末日,而我們擔心月末”成了示威者的流行口號。
法國社會學家托里斯托夫·吉洛伊在《邊緣法國》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巴黎等大城市環城鐵路沿線小鎮的白人是如何在一夜之間成為“少數派”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威廉·德羅茲迪亞克指出,“黃馬甲”運動在工人階級聚集的郊區和荒蕪的農村地區扎根,尤其是在“真空對角線”,即從東北部的阿登地區到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脈之間廣袤的“法國中部”地區。這一地區人口密度較低,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絕大部分民眾自認為被全球化拋棄。
在法國,正如在整個西方世界正發生的,傳統左右政治格局已無法回應日益撕裂化、碎片化的社會現實,新的政治分野正在逐漸形成:一邊更加強調全球合作,以應對人類面臨的氣候變化、貧富差別挑戰,主張新的自主、平等、協作、可持續發展的生活;另一邊強調民族認同、國家主權,認可傳統價值與生活方式,重視集體與個人安全,強調文化與地理邊界等。在兩股政治思潮之下,各種思想支流在法國社會相互交匯、激蕩。
疫情進一步撕裂法國社會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與“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蒂埃里·馬勒雷在《后疫情時代大重構》一書中指出,疫情加劇了社會不平等,讓社會弱勢群體不成比例地暴露在健康與經濟風險中。不平等加劇的一個嚴重后果是造成社會動蕩,“當人們失去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時,他們就會訴諸暴力”。作為疫情重災區,法國一年多以來疫情起伏不定,在進行三次大規模封城背景下,即使政府在財政方面做出大量努力,依然無法彌補經濟與就業所受的重創,導致社會低收入群體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與此同時,法國軍隊和警察面臨巨大的抗疫、維穩壓力,其不滿情緒同樣在累積。2021年4月以來法國部分退、現役軍人在極右翼媒體《現實價值》先后發表兩封聯名信,指責政府在本國領土上向極端主義“讓步”,致使“軍人在海外白白流血犧牲、警察成為社會沖突的替罪羊、中學老師被斬首”,警告法國有陷入“內戰”的危險,聲稱“愿意支持那些考慮國家存亡的政策”。這兩封信在法國政壇引起強烈震動,甚至被一些聲音視作“軍事政變的苗頭”。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黨魁勒龐積極向這些軍人們拋出橄欖枝,邀請他們加入其“愛國運動”。
面對愈發撕裂的民意,馬克龍在大選前最后一年的核心任務就是以一種更平衡的方式重塑國家認同,粘合破碎的法國社會,防止發生新一輪大規模社會動蕩。目前來看,馬克龍在社會經濟領域有意向左翼政策回調,批判現行資本主義模式缺陷,承諾更加關注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強化國家的保障作用;改革精英教育與公務員體制,發動一場“反階級固化”革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但承諾在轉型過程中“照顧弱勢群體”。在社會安全領域則向右翼保守政策傾斜,抨擊激進左翼思潮,打擊“伊斯蘭分離主義”,推出反恐新法,與風頭日盛的極右勢力展開一場“地盤爭奪戰”。